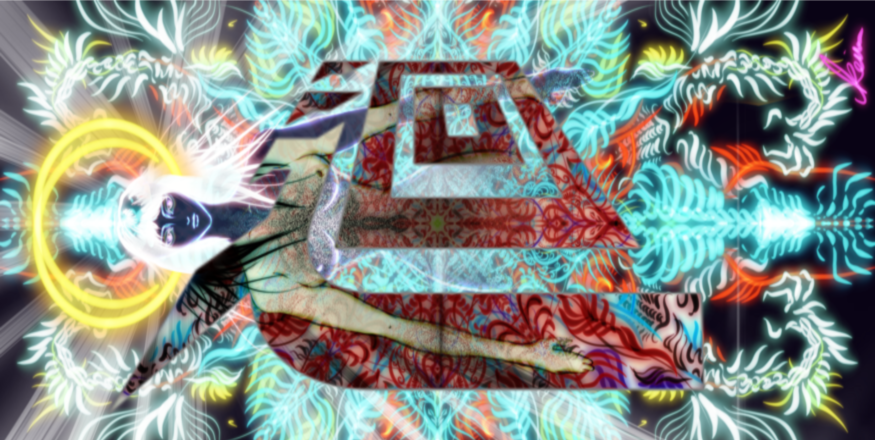我就像大部份的人一樣,在成長的過程之中,小時候所謂的「夢想」就是在四季更迭的必然之下,隨著日曆的消損不斷地變得單薄。
八歲時我在學校的勞作課上畫了一幅畫,內容是某個我所夢到的遙遠星球上的動物跟風景,因為是夢,所以我知道那不是地球,那是個在星海深處的異星,有點像是地球,但顏色不一樣,地表有著人造的遺跡,文明存在過的代謝物,但曾住在那邊的人不知消失去哪裡了…‥
因為是夢,所以這些類似背景設定的事我都理所當然般地知道,高聳的失去顏色的巨大建築如同方正的鐘乳石,雖然沒有了智慧生命,但也更顯得生意盎然,各種各樣不曾在圖鑑或電視上看過的奇妙動物就在被植被覆蓋的城市廢墟中散發著強大的生命力,有背上長著翅膀的雷龍、脖子很長的豬、十隻腳的雞、長著烏賊觸腳的黃色熱帶魚、果實是紅色嘴唇的椰子樹與蕊是眼珠的玫瑰花,所有的生物都和樂融融地在三顆綠色的月亮下生活著。現在看來那也許是張筆觸幼稚,用色與構圖跟比例皆嚴重失衡的畫,但就那個年紀而言卻是幅令老師驚豔的作品,講話嗓音尖細語調刻薄鼻頭上有顆大黑痣的女老師不但難得誇讚了總是因為遲繳作業,成績也頗糟糕被打被捏是家常便飯的我,放學時還特地送我到校門口跟母親說我極有藝術天賦呢。
真的是使我受寵若驚,畢竟那位長得像是巫婆的老師常常都像是隻確認著地盤的狗一定要在我身上留下幾個瘀青。但也因此我在她那厚得將眼睛縮小一倍的鏡片後所看到的炙熱目光與情緒高昂而更顯得音調刺耳的褒揚話語中得到了自己生平的第一個確切的夢想─「畫家」。
直到有一天我瞭解到對於繪畫自己終究只是比一般人好大約百分之十左右罷了,這百分之十大概就是我在紙上畫了隻貓跟狗,你可以明確地分辨出來左邊的是狗右邊的是貓的程度,這種細微如塵的才氣跟所謂的天賦完全是兩條平行線。花了不少錢送我到畫室學習直到小學畢業的母親應該比我更早瞭解到兒子的資質終究只能讓人看出狗與貓的不同,絕無可能成為第二個達利、梵谷、畢卡索、徐悲鴻等名家……但她什麼都沒說,直到我自己有所醒悟。
在父親離開我們之前,母親總是什麼都不說。
十三歲時我迷上了倪匡的小說,那是父親所收藏的,一整套包括了衛斯理、原振俠及羅開的故事就零亂地擺在他積著灰塵的書櫃裡,我那時候為倪匡筆下絢爛的冒險與各種超自然力量及玄妙的外星人描述深深得瘋狂著迷,到現在我還記得第一次讀《肢離人》的心情,那字裡行間對於漂浮在半空中的手敲打著窗戶玻璃的敘述實在是太真實太有畫面了,讀完的那晚我躺在床上盯著拉上窗簾的玻璃窗戶無法成眠。
然而……我之所以會對那些超自然事物著迷,那個下著雨的傍晚的奇妙體驗可說是個更明確的濫觴,雖然事後回想那件事說實在要解釋的話也可以有許多合理的解釋……不過我認為我看到的應該是祖父的鬼魂。我的直覺非常肯定地這樣告訴我。
畢竟,那個場所應該就是那種有著跟另一個世界磁場相通的場所,所謂的靈異景點。
20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mw1LWe3SYq
20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J8EjO5uq5x
在我十五歲,也就是國中畢業的那個暑假我試著寫下了一篇小說。
並沒有什麼靈光一閃或天啟之類的,我想只是因為除了自慰外根本無處宣洩心中那股為賦新辭強說愁的思春期青少年特有的苦悶與哀愁之稚拙心靈對神秘又遙遠的愛情投射自然而然產生的鏡花水月幻想。
也可能是因為那段時間我翻譯著祖父的手記觸發了我內心寫作的衝動。
我用文字構建了一個我與那個叫做旬的女孩子之間發生的苦澀之中帶著黑色幽默之愛情故事,脫胎於現實,完美於虛構。
在寫完後訂下了〈鼠〉這個標題,然後投到了縣政府辦的一個不大不小的文學獎,此時暑假已經過了三分之二了。結果〈鼠〉居然出乎意料的得到了個評審獎,獎金雖然不多但對於學生來說也是筆超乎想像的大數目了,接到主辦單位的通知時我剛過完十六歲生日,高一上學期才開始不過兩個月。封印在抽屜之物應該早已化為白骨,甚至可能成灰了。我猜,我之所以會寫下著這篇小說除了前述的原因外,多少也是跟自身對老鼠的心理陰影有關吧!
我本來並不討厭老鼠這種小動物,甚至覺得牠們還滿可愛,全身灰色的毛與大而無辜的黑亮眼睛及肉色的耳朵,還有細長的暗粉紅色尾巴,都一再撩動著年幼的我對於這種小型哺乳類的興趣,也偷偷瞞著極度討厭老鼠的母親在抽屜養過一隻小白鼠,只是白化的老鼠如同兔子紅艷的眼睛總是缺少了正常老鼠黑膽石般晶亮雙眼那種惹人憐愛的特質。
小白鼠是在夜市攤販抽獎抽到的,我把牠取名叫「嗶啵」。
由於母親厭惡老鼠,所以當我知道自己抽到了隻白老鼠時心情完全高興不起來,我本來中意的是被擺在竹籠中羽翼未豐的灰藍色小鸚哥……
國二時那段不快回憶在我從老闆手中接過裝在紙盒裡蠕動著的白色幼鼠時襲上心頭……
那是個陰天,放學的我在家門口外的水泥柱角落發現了片黏著三隻灰色小老鼠的黏鼠板被放在一袋裝著果皮之類廚餘的垃圾袋旁,母親在家裡每個角落暗處都放著許多黏鼠板。黏鼠板上只剩下一隻老鼠還活著,其餘兩隻皆已因過度掙扎毛皮撕裂地軟癱著,不知是血還是糞的乾涸褐色斑點散落四周。
我蹲下來看著唯一活著的小老鼠,牠也抬起頭發出虛弱地吱吱聲以黯淡混濁的小眼睛看著我。
「救命……」
牠似乎這麼對我哀求,我撿起了落在腳邊的小樹枝想將它從黏呼呼地膠上掰下來,但是並沒有想像中容易,於是我有些煩躁地加強力道,最後牠雖然脫離了黏鼠板,卻留了一部分的皮在上面,淡粉色的腳爪與尾巴因膠沾黏成一團,側身冒血地像隻蟲在水泥地上顫抖。那樣的場面讓我反胃而驚恐。
吱吱吱吱吱吱吱吱……
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
奄奄一息的幼鼠發出了淒厲的叫聲,四肢無法動彈的牠拼命扭動殘破的身體向我的腳邊靠過來,用深黑的眼睛望著我並在深灰色的粗糙水泥地面拖曳出血痕……
我呆立了兩秒後立即快步衝回家裡,但關上門後我仍然聽得到幼鼠的叫聲,理應被隔絕於門外的哀鳴如黏鼠板上的膠緊緊附在我耳窩裡。
我所做的事情當晚便被母親發現,她高分貝神經質怒叫責罵我,盤問著為什麼要將抓到的老鼠用下來。「因為很可憐……」我低喃著。聽到我這麼說的母親突然靜默了,她的臉像是被按下暫停鍵的電視畫僵硬不動,只剩下歪斜蒼白的唇微微抖著,睜得老大的雙眼內倒映著我低著頭雙肩萎靡垂下身影的黑色瞳孔跟幼鼠那雙看不到眼白深洞似的小眼睛重疊在一起。
時間的連續性在當下被奇妙地撕裂成了分散的斷面,接下來的畫面在記憶中像是被蒙太奇手法剪輯過一樣只有快速的凌亂不連續片段配合著母親憤怒的話語重複不斷無從逃脫。
啪─
臉頰傳來的聲響伴隨了熱辣的刺痛。
「很可憐?」
啪─
「你知不知道老鼠身上有多少細菌?」
啪─
「那東西有多髒有多噁心已經不是可不可憐的問題了!」
啪─
眼前的景象因為淚水而搖晃了起來,嗡嗡地耳鳴與不停爬上雙頰的熱辣感使我聽不清楚母親的話語,雖然想轉身逃跑但雙腳卻被釘死在地上無法動彈。我咬著牙,決定不為所動。
「告訴你多少次!」
啪─
「吃飯前也不洗手!」
啪啪─
「為什麼這麼不聽話!」
啪啪啪─
引起耳鳴的一聲聲啪、啪、啪與母親響徹雲霄的怒罵聲及幼鼠的吱吱叫鳴在我腦中融合成了個巨大的漩渦。
父親則背對地坐在一旁的沙發上沉默以對。
20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kytssCxK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