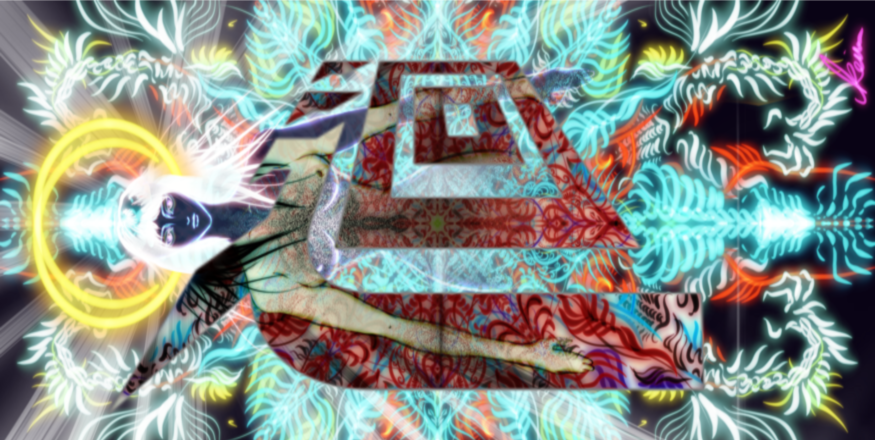以旁觀者的視點看著的「我」感到下腹部有陣眩惑的涼意襲來。
排山倒海的歡呼聲與鬧鐘的鈴聲在睡夢與清醒的渾沌邊界重疊並互相排斥卻又渴望融合。
我醒了過來,陽光從百葉窗的縫隙照了進來,被切割成橫條狀的光以等距間隔排列在我的身上。
按掉瘋狂大叫的鬧鐘後,我發覺自己的內褲裡濕濕的,於是將手伸進去,沾染在指尖上的是少量黏膩的半透明白濁液體,我把手指湊到鼻子聞,液體散發著類似漂白水的味道。
當下我意識到了自己的身體已經產生了不可逆的變化,罪惡感在我明白那液體所代表的意義時沒來由地爆發。羞恥、慚愧、悲哀等情緒也湧進了我體內,自己卻不明白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情緒反應。
我無言地呆坐在床上看著條狀的光,昨晚夢境的細節仍鉅細靡遺地印在腦海中,平常做的夢在醒來後總像是朝露在陽光的照射下隨即蒸發消失,但昨晚夢裡場景的一切;諸如光度、色澤、擺設、流程、對白等即使在紫外線的作用下還是深刻地烙印在記憶裡彷彿一部在電視上偶然轉到卻留下深刻印象的戲劇片段。
「阿愆,起床了沒?」門外傳來母親的呼喚,我咕噥了幾聲回答她。
然後起身將內褲脫了下來摺疊成極小的方形,再拿衛生紙將兩腿間擦乾淨,接著把內褲與衛生紙團放進置於床頭的書店塑膠袋。
就在我換上印著就讀的校名的制服時,地板上的某個東西吸引了我的目光,我彎下腰想看清楚到底是什麼。
乍看之下我還以為是隻蚯蚓,是條蟲般細小的粉紅色物體,呈現S狀躺在書桌桌腳的前方。
啊!
這是……
我看向被鎖起來的抽屜,睡前還掛在那裡的半截尾巴已失去了蹤影,我用手大力拍打了抽屜,但過了幾分鐘裡面依然什麼動靜都沒有。有道如不小心被紅筆畫過的血跡留在原本尾巴垂掛的地方。
門外又傳來了母親的呼喚,我撿起斷尾放入了裝著髒掉的內褲與衛生紙的袋子,接著又猛然想起了抽屜的鑰匙,於是我也把鑰匙放進袋子裡再將袋子打個死結綁起來塞到書包。
出門後我騎著腳踏車繞了路騎往學校的反方向。我將書包中的袋子丟到了貫穿這城市的河裡,袋子在水中載浮載沉往海的方向流去,我就這麼在被車潮霸佔的橋上聽著此起彼落的喇叭聲看著水流中逐漸遠去的袋子。
早晨清新的空氣與將河面照得亮眼的陽光讓我有種難以形容的愉悅,看了一眼去年生日父親送的CASIO手錶,上課是遲到定了,但我卻不擔心,遲到也沒關係,因為我有個感覺,一切的一切都變好了,沒什麼需要擔心的。
6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DvcsVmsmSY
6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mGQa1NgZf4
父親在市區開了一家叫「The Happy Prince」的餐酒館,主要是賣咖啡跟比利時啤酒,餐點的部分則有義大利麵、漢堡與手工蛋糕。店內的裝潢以鄉村風格為主,牆上貼滿了老電影的海報與父親跟母親在他家鄉時的生活照。父親溫吞的性格感覺起來似乎沒什麼經營才能,但店的生意非常的好,我周末有空都會去幫忙,只是母親似乎不太樂意我這麼做,她沒有積極表現出反對的態度,但有些時候她看我的眼光總是像探照燈般讓我覺得隱藏在內心的真正想法會完全暴露在她面前。
在我還沒上幼稚園的年紀,父親總是看著我的眼睛用語尾上揚腔調微妙的國語說我有雙跟他父親顏色相似卻左右相反的眼睛,看起來就像快樂王子。
他還會說自己則是燕子。
那媽媽呢?我這麼問。
蘆葦吧!他說。
後來在瞭解這篇王爾德寫的童話故事內容後,我一度認為父親是不是討厭我,不然為什麼會把這個悲慘的角色套在我身上呢?
在擁有基本閱讀能力後,我在父親的書房一遍遍地翻著標了注音的《快樂王子》,卻怎麼也無法喜歡上這個故事。
不過也許這只是單純因為我的眼睛使他有這樣的聯想。我兩邊的眼睛顏色並不相同,左眼跟來自台灣的母親一樣是接近黑色的深褐色,右眼則遺傳了父親的西洋血統呈現淡藍色,看起來就像故事中將鑲在兩眼之一的藍寶石送給飢餓劇作家而少隻眼睛的快樂王子一樣。
我人生第一次夢遺後莫約過了半年,升上國中的我幾乎忘了嗶波,只有在偶爾翻找東西時順手想拉開鎖住的抽屜時才會想到牠,還有在某些睡不安穩的夜裡,半夢半醒間時不時還會若有似無地聽到細微的刮搔聲由抽屜內傳來,當然,我知道那是幻聽。
在陰暗抽屜裡的大概只是具少了半截尾巴的齧齒類白骨吧,像是個被深埋在地層的古老化石般被時間所遺忘。我毫不猶豫地這麼認為,並為此感到安心。
但有時候許多事實總是跟想像有著落差。
那是個下著細雨的星期一,也是父親的店休日。我回到家時父親正坐在客廳,電視頻道轉在HBO他膝頭上還放了本書,他翻著書,光彩躍動的電視畫面倒映在他的眼鏡鏡片上。放假時他總是窩在家裡,不是睡覺就是看電視讀書聽音樂。
「回來啦?今天怎麼這麼晚?」
落水狗般的我將書包一丟便走進浴室沖個熱水澡,對父親的話置若罔聞,從昨晚開始這個世界對我而言驀地變得朦朧混濁無法看清自身與其之距離。
由蓮蓬頭奔騰而出的熱水滑過了身體表面,但熱氣卻無法驅趕走剛剛在後山的經歷所凝結在體內的寒意,而生殖器上殘留的甘美刺痛感卻輕易地被水所帶走流入無光的下水道中,我身體還再無法抑制地發著抖。
短短不到二十四小時的時間,我所看到的、感受到的、體驗到的一切就像是個雜揉著梵谷與莫內及達利還有畢卡索的風格所描繪而出的光怪陸離無從理解詭異莫名卻又美麗動人引人嚮往的地獄和天堂穿插交錯的畸形美景。
6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VfWGKAJiZI
你啊跟我是一樣的喔,是蝙蝠,有翅膀卻不是鳥類,長得像老鼠卻也不是獸類,什麼都像卻也什麼都不是。
6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v0b6Tlg5iu
不到一個小時前,那個叫做松本旬女孩在我耳邊對我的低喃依舊迴盪在我耳邊重複,嘩啦啦的水聲怎麼也淹蓋不去。我的陰莖上含殘留著被她握著的觸感。
6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2GZxOWUU0Y
洗完澡後我換上居家服及乾淨的內褲走到客廳坐到了父親旁邊。
「Alma今天要加班,晚餐就我們先吃吧,餓了嗎?」父親說,他的國語現在聽起來算是非常字正腔圓了,但還是掩不住微妙上揚的語調及錯置平仄的口音。
父親對我提起母親時通常都是直接叫她的英文名字,而不是「你媽」、「你母親」之類的,我常覺得這種用法充滿略微刻意的疏離感。
我冷然地點了點頭,看著電視螢幕,畫面中正在上演著某部活屍電影。在這個時候面對父親,我的內心沒來由得有一股羞愧,我無法掌握這股情緒的由來,但我能隱藏,以冷淡的膜將之包圍,吞噬,放到情緒的內側。
對於我的態度似乎毫無所覺的父親起身到廚房準備晚餐,我拿起了沙發上他剛才正在看的書,是《老人與海》的中英文對照版。
老舊的書頁被我翻動著,舊書特有的氣息混和著少許的霉味騷動著我的鼻腔,書頁間附上不少精美細緻的插畫,我看著最末頁躺在沙灘上尖銳長嘴被纏繞著麻繩,除了頭部外全身只剩下骨頭的馬林魚及站在其遺骸旁指指點點的一對男女,試著閱讀著插圖下方那行英文字。
雖然父親來自英語系國家,但從我有記憶以來便很少聽到他說母文,而我雖然遺傳了他蒼白的膚色、輪廓還有一隻藍色的眼睛,但英文成績卻有點糟糕。
插圖下的英文單字排列在我看來就像是難解的密碼,眼底的那些字逐漸扭曲變形,我的眼皮也逐漸的沉重了起來,隱約聽到電視中被行動遲緩的活死人追逐的女主角發出了烏鴉般粗啞的高分貝尖叫。烏鴉……我想起了昨夜的白色烏鴉的叫聲……
就在我即將墜入睡眠迷宮最深處的那一刻;意識如冰塊漸漸消融越飄越遠但神智依舊不願放手如飢餓的螞蝗緊緊吸附在腦海深處的迷濛半夢半醒時分中,插圖中那對男女在落葉紛飛般的英文字母中動了起來,由黑色線條構成的男女與背景、魚屍都被繪上了色彩與陰影,濤聲裡日落的橘紅海岸中搖曳的棕櫚樹下男人蹲到了馬林魚的旁邊以哀憐的表情撫摸著它失去了皮膚肌肉內臟裝飾的白亮骨骼,女人則爬出了框架站到了我面前。
我拼命地集中渙散凋零的意識看向眼前的女人那張我熟悉無比魂牽夢縈的容貌。
旬……
我呼喚著她,卻不確定自己有沒有發出聲音。
女人對著我露出笑容,左邊的臉頰浮現了小小的酒窩。
「嘿,記得不能跟別人說喔,我想你這麼聰明應該知道吧!」
她說,並將身體靠在我身上,我聞到了淡淡的玫瑰香氣。
我用力地點了點頭,喉嚨瞬間又乾又熱好似有團熾熱烈火在食道中燃燒……
然後當她靠近我時,我越過她看到了被方框圍住的插圖內男人與魚骨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父親赤裸著身體對我微笑著,他們下體腫脹的巨大陽具使我產生相形見拙的自卑感。
正當旬要拉開我的拉鍊時……睡眠的深度忽然被擴大加強成具體的黑暗將我吞了進去,我墮入了無邊無盡的黑色睡眠迷宮深處,無底的黑暗中我又聽到了抽屜內的刮搔聲,刮搔聲漸進的加大,然後化為地鳴般的雷電,強烈的電光中有個男人,那個男人用他的眼睛看著我……那雙眼睛讓我沒來由地害怕……為什麼……他的眼睛……
我在沙發上像死了般昏睡了將近半小時,父親似乎花了不少工夫才叫醒我。
晚餐是佐上自製紅醬加了許多波菜與德式臘腸的西班牙蛋餅,也是父親最愛吃的食物,除了西班牙蛋餅外還有貝殼麵沙拉與南瓜湯,我與父親將食物端到了客廳,配著電視吃著。
我用叉子將混在西班牙蛋餅中的洋香菜碎末仔仔細細挑了出來堆在盤子的邊緣,父親看著我露出了苦笑。
兩個人吃著晚餐有一搭沒一搭的說著話,我壓抑著內心的複雜思緒盡量平和地讓對話進行著,但大部分的時候我們之間共有的只有叉子與湯匙刮過瓷盤上的空洞聲響。
對於我所營造出的漠然態度終於有所感受的父親似乎有些徬徨卻又無從找到癥結點來切入,看著那樣的他我的心中升起了虛浮的優越感。
吃完飯後父親開了罐海尼根大口喝著,白色的皮膚立刻泛紅,我則喝著可樂,HBO播完B級活屍電影後開始播放反差感十足的老舊歌舞片,我們無視桌上的杯盤狼藉看起了電影,電影演完時已經八點多了。
「我收就好了,你去休息吧!」
父親將空盤疊在一起關上電視後這麼說。
我看也不看他地點點頭往樓上走,腳才剛踏上階梯就聽到了廚房傳來父親的驚呼聲,我轉過身往廚房走去,看到父親的背影站在流理檯前,晚餐的杯盤歪歪斜斜地堆在流理檯旁。
「怎麼了?」
窗外的雨勢似乎隨著夜的深度而有轉強的趨勢,滴滴答答的雨聲充斥著一切,我走向背對著我低頭盯著地板的父親,耳朵聽到了奇妙的聲響。
有個東西正從流理台下方的縫隙爬出來,牠的步調緩慢且失衡,因為其後腳及下腹部被絆住了,牠拖著被牽制的身軀極力想逃脫。
是隻正拖著黏鼠板長約三十公分的巨大老鼠,盯著牠的父親眼中充滿畏懼。
這鼠的毛色偏淡帶著奇妙的花紋,牠已經有三分之二從縫隙中竄了出來,爪子在地上刮著,長度與牠身長相當的黏鼠板看似撐不了多久,牠完全無視俯視著的兩個人類拼命地在我們的影子中扭動著,縱使它的體型龐大,但下半身被強力黏膠糾纏再加上黏鼠板的重量使它像是個受了重傷在壕溝中苟延殘喘的士兵。
「哇,超大!」我忍不住後退了一步,牠爪子摩擦地板的聲音實在是太噁心了。
「對啊,根本是鼠王了嘛!」
「晚點媽看到應該會很高興,大豐收。」
「但牠快逃脫囉,等她回來就來不及了,如果Alma知道我們讓這東西溜走我們就死定了。」
「那怎麼辦?」
皺著眉苦著臉的父親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地上的老鼠,眉間的皺紋在暖色系燈光中拉出了深刻幾何線條的暗色陰影。
老鼠終於只剩下五分之一的身體還留在縫隙裡,牠張開嘴發出了難聽叫聲,長長的暗黃門牙若隱若現使之看起來更加詭異恐怖,沾滿黃色黏膠的右後腳這時已經脫離了黏鼠板在半空中扭動。
「沒辦法,我們必須馬上幹掉牠。」
父親吸了口氣後說,表情非常悲壯,我知道他也非常厭惡老鼠,與母親不同的是,他的恐懼是更加生理式而神經質地,並非如母親積極的面對加以消滅而是消極逃避視若無睹避而遠之。
他大概是想藉此在我或母親面前展示些尊嚴之類的,但從他哀戚的臉上我可以看出他內心的天人交戰。
我揣摩著他的心態不屑地說:「怎麼幹掉牠?」
聽到我不耐地這麼說,父親眉間的陰影更濃了。
然後他似乎想到什麼,走到了瓦斯爐旁放置雜物的抽屜裡翻找,似乎刻意故作輕鬆嘴裡還吹著口哨,忘了在哪裡聽過的輕巧略帶懸疑感的旋律在雨聲與老鼠的騷動聲中飄揚……是《胡桃鉗》的《糖梅仙子之舞》。
父親所蒐藏的大量古典樂唱片中有許多張都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我有時候也會拿來聽。
父親走了回來,手上拿著他做烤布蕾時用的瓦斯噴燈。
「用燒的應該可以吧?」父親說。
「你確定?」
我想像高溫的藍色火焰舔舐著老鼠毛的光景,感到有些悚然,對於屠殺鼠輩的方法我毫無概念……父親應該跟我差不多,母親倒是終結這類害蟲的行家。
該用水、用火、用毒、用刀?我想最高指導原則是能確實將之生命終結都可以吧!所以用噴燈應該並沒有什麼不行,說不定還具有殺菌效果。
流線狀的藍焰由噴燈的出火口射了出來還搭配著嘶嘶聲,蹲著的父親將火焰往老鼠的頭部靠去,他握著噴燈的手關節泛白顫抖著。
火焰親吻了老鼠的頭部,牠發出淒厲的慘叫,聽起來有些類似嬰兒的哭聲,捲曲的毛與起泡的皮肉化成了黑色的煙產生了嗆鼻的怪味,強烈的痛苦使老鼠發狂地扭動著,牠拖著黏鼠板一下前進一下後退原地打轉看起來既可笑又恐怖。
父親在動手不到十秒後便被眼前變形的鼠頭、四散的怪味與恐怖的叫聲逼得停手放棄,但我卻感到那十秒像是被壓縮扭曲成無限的恆常般無止盡。
老鼠的頭部冒著煙,焦黑的皮下顯現出紅色的血肉,小小的火苗還徘徊在牠的兩頰,外凸的眼球變地白濁看起像是外星怪物,慘烈的叫聲漸漸地降低成了微弱的呻吟。父親不知所措地站到我旁邊噴燈仍被緊握在他手中。
面貌悲慘的老鼠用前爪奮力地前進著,牠的身體終於完全從流理台下爬了出來,黏鼠板在地板摩擦發出喀拉喀拉的聲響。
然後……
我發現這隻老鼠的尾巴長度只有正常的一半,而它偏淡的毛色之所以佈滿不均的斑點花紋應該是因為在暗無天日的下水道中與垃圾汙水裡討生活不可避免的沾染髒污造成的,牠的原本毛色極有可能是無瑕的白色,雖然剛才沒注意,但我想那雙被烈焰舔舐過蛋白質凝結而白濁的眼睛本來也是如寶石般的豔紅。
不可能吧……
收縮的喉嚨傳來了強烈酸味,我覺得想吐。
老鼠以盲目的雙眼看向我,牠的慘叫聽起來像是在大笑。
6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dDl0EyJxgB
6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tUdb65aEc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