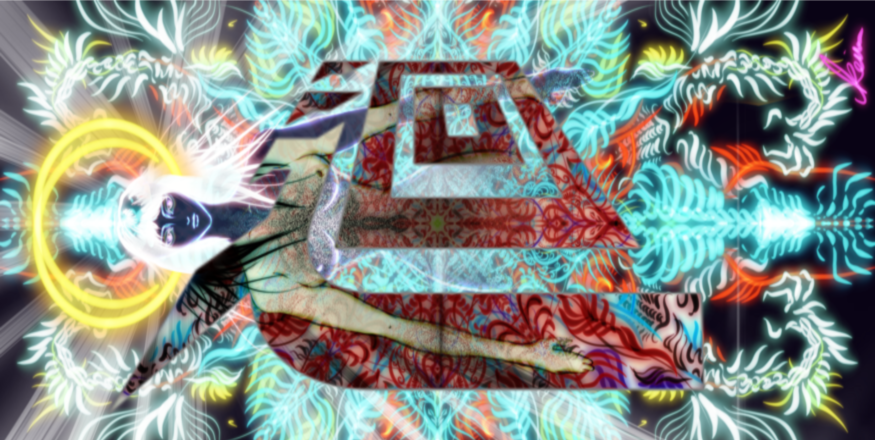你啊跟我是一樣的喔,是蝙蝠,有翅膀卻不是鳥類,長得像老鼠卻也不是獸類,什麼都像卻也什麼都不是。
6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YKE5NHOrGl
旬曾這麼對著我說。
旬啊她姓松本,父親是日本人,母親是台灣人,七歲前因為父親工作的關係住在利物浦,後來回到日本跟母親在大阪定居過一陣子,父母在她國中時離婚,她便與母親搬回台灣。
她正就讀大學二年級,主修哲學,每周有五天固定在「The Happy Prince」打工,主要是負責外場,但依情況會在廚房及吧檯內幫忙。她有一個男朋友叫阿雄,是「The Happy Prince」的專職內場。也許是因為總是理著三分頭及那漫爬在四肢玲瑯滿目筆觸張狂顏色艷麗的刺青,外型給人的感覺總有幾分流氓氣息使人卻步帶著難以親近的印象,言語也毫不掩飾地透露著極左派的風格,但說真的,實際互動下來,他其實是個滿好相處,心地善良的大哥。
6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IJSAlHn1oK
6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Md6cKAdF38
第一次見到她是在某個初秋的周日午後,那天我與旺仔看完了電影,電影的劇情跟想像中的不一樣,遠本在電視上看了預告我以為是有著酷炫武打場面的刺激動作片,預告裡的主角都戴著墨鏡穿著皮衣用著慢動作開著槍,但進戲院看了以後才發現實際上這是一部科幻片,內容完全出乎我意料,講的是在未來電腦統治了世界,人類的身體被當作電池來用,意識是活在虛擬實境的故事,旺仔也跟我一樣,我們都沒想到會看到這樣一部內容超出想像的作品,會不會這個世界真的就像電影裡演的,都是假的呢?
出了戲院我跟旺仔還意猶未盡地在路邊對電影的內容聊了大概半個小時,可惜他得去補習,總覺得聊得不夠盡興,他就先走了。
而有點失落的我也不知要去哪裡晃就想說到父親的店吃點東西好了,於是便騎著腳踏車到店裡。
推開了貼著名不見經傳地下樂團海報的木門時門上鈴鐺照例發出清脆的聲響,由於正好是不上不下的離峰時間,店裡還沒有客人,不知那裡聽過的英文歌正在空蕩的空間中飄著。
「歡迎光臨。」
一個陌生的溫柔嗓音親切地傳來,隨之是個穿著胸口畫了個大大反戰符號白T恤的女孩子一手拿著托盤走到了我面前。
「你好,一位嗎?」
她剪了個露耳的鮑柏頭,髮色染成了偏淡的亞麻色,耳朵上掛著金色的圓形耳環,齊眉的瀏海下是雙鳳眼,高挺的鼻子及粉色的唇配上那雙眼睛構成了亮麗的長相,上揚的嘴角與左邊淺淺的酒窩形狀美好得閃閃發亮。
我的心臟瞬間便被那光亮俘獲。
也許是見呆立在門口的我遲遲沒有反應,她再次喊了聲你好,並再次詢問我是否為一個人。
我想說些什麼,但砰砰狂跳的心臟使我喉嚨乾澀發不出任何聲音,視線不自覺得盯著那反戰的符號,啊,不能這樣看著對方的胸部啊,她會不會覺得我很奇怪?
「是我兒子啦,你看完電影啦。」
就在我僵在原地不知所措時父親從廚房走了出來並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對我伸出了援手。
「這是小旬,新來的服務生,是阿雄的女朋友喔。」
廳玩了父親的話,旬向我露出了不同層面的微笑,她瞇著眼看了看我又看向父親,然後說:「哇,你們長得好像喔。」
我坐在吧檯的角落吃著略早的晚餐,加了雙份起司與花生醬的漢堡,父親坐在我旁邊微笑著看我用可樂將漢堡三兩下吞到胃裡,然後熱切地問著我對今天看的電影有什麼心得,他想找母親去看那部片,但由於母親最近升了職很忙,兩人的時間總是對不到,所以從上映至今已經過了三個禮拜了父親還沒看過這部從上映前他便萬分期待的片子。
我心不在焉地跟父親避重就輕地敘述著電影的情節,因為他說他很好奇劇情,但又不想知道太詳細,這種矛盾不是不能理解,而我更多的注意力同時是不時偷瞄著在吧檯另一端與阿雄談笑生風的旬。
視線角落中窗戶透進的黯淡夕陽下,旬的側影在我心裡漸漸地擴大,她後方的牆上貼了張老舊的電影海報,海報中一對男女騎著台藍色復古的機車,穿著紅裙的女主角摟著男主角笑得極為開心,背景是羅馬競技場。
後來我便開始主動要求在課後到父親的店裡打工,父親非常的高興,因為他之前也帶我到店裡幫忙過,沒幾次我就拒絕再去。現在他笑著說:「你長大了呢!」他可能認為這是兒子成長所產生的貼心表現,對於他這樣的想法我略感到狼狽,但他怎麼想其實我也控制不了,而且如果他能因此感到開心或滿足,也沒什麼不好。
背著光的側影,反戰的符號,她的笑容,旬的身影不但擴大,還幾乎佔滿了我的所有心中的空隙。
我想把握住能看到她的所有機會。
6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KQRWQDXVar
6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ywXfYGsnmY
對於幾乎沒有任何經驗的我,旬很仔細並認真的教導我關於外場服務生所該具備的基礎知識,水杯該如何擺放、桌巾與餐紙的位置、點餐時如何引導客人對高單價的餐點或限定的飲品產生興趣、輕鬆的收桌整理法等等的。她總是親暱地叫我小愆,而我則是結結巴巴地叫她旬姊。
我總是抓不到跟她對話的節拍,忍不住想看她,又怕被她察覺我的視線,我知道自己跟阿雄相比之下就是個毛頭小子,她可能還覺得我難教,連話都講不好。
還好時間有時就是最好的助力。
幾個禮拜後我終於逐漸地上手,上水,點餐,送單,上餐,收桌以及清潔等等流程已經抓到了訣竅,父親也給了我份不錯的打工薪水,最重要的是我已經可以自然地跟旬聊天說笑了。
我們會在吧檯角落偷偷的觀察客人並發揮想像賦予他們一些有趣的故事,大部分都是由我開頭,然後她再接續。
譬如我說:「你看,第五桌的那對男女,兩個人臉都臭得跟大便一樣,是在談分手吧?」
「不是喔,你看那個男的看起來至少四十歲了,頭都禿了,女的看起來卻才二十多左右,應該是小三,她正因為男方遲遲不肯跟太太離婚而生氣吧?而男的西裝筆挺的,想必是個高階主管,頭禿成這樣應該是因為壓力大再加上領導能力不足的關係,而且胃潰瘍很嚴重所以辦公桌抽屜塞滿了胃乳,他當初只想玩玩,沒想到惹禍上身,女方強烈的佔有慾跟忌妒心害他每天都要多喝兩包胃乳,今天他本來是想談分手的,沒想到女方居然威脅他要告訴他太太還跟他攤牌說自己懷孕了。」
「這也太八點檔了吧?」我說。
「對啊,太老套了。」有時候阿雄也會插上兩句。
阿雄說:「應該是客人跟小姐在談價格吧,男的開三千五要玩全套,女的卻怎麼也不願意,三千五只能技能保養喔,由於價格談不攏所以才會鬧得這麼僵!」
我有時真羨慕能把那些沒營養的下流話順暢說出口還能逗得旬發笑的阿雄。
「喂!你們給我差不多一點!」父親有時候也會這麼制止我們。
雖然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的累積堆疊,但這段時光真的很快樂。
我真的以為什麼都不會改變。
時間就只會以這樣的形式沉澱,固化,一天重複著一天,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
但世事的改變及它轉彎的弧度大多都在人無法察覺的瞬間,然後改變開始後便是個不可逆的。
6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tCjamPqq0b
6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H0bqur4CB4
基本上平常日我都是下課騎著腳踏車就到店裡,趕上餐期,然後九點下班回家用功課或看書,由其他三個人進行收尾的整理工作。
那是個吹著南風的夜晚,跟季節不太搭的潮濕暖風吹了整天毫無止息的跡象,整個晚上店裡都冷冷清清沒有什麼客人,於是父親便讓我提早八點就走。
回到家門口我才發現放著家門鎖匙跟錢包的背包不知怎麼著地忘在店裡了,按了電鈴,母親似乎還沒回家,於是我只好再回去一趟。
我回到店裡時鐵門已關了起來,不過父親的機車還停在門口,我拍了幾下鐵門,但裡面卻沒有任何動靜。
於是我繞到了後方的防火巷打算從後門進去,那是條黑臭陰濕的巷子,地上滿是可能樓上住戶或被風捲來的垃圾,排水管、盜接的電視線、外露的鋼筋張牙舞爪地盤踞在長著霉斑與青苔的水泥牆上。
我走到店的後門,左方裝了鐵欄杆的毛玻璃小窗半開著透出昏黃的光,那是廚房的氣窗,由於明天公休,父親他們這時應該正在裡面做每星期一次的大掃除,我推了後門,鋁製的門聞風不動。
呱…呱…
一陣不怎麼悅耳的尖銳叫聲響起,我嚇了一跳,有隻鳥停在我左上方的鐵架,一開始我以為是白鷺鷥,但當牠再度發出呱呱叫聲我才發覺那是隻烏鴉,或看起來像烏鴉的某種鳥,因為其通體都是白色的,也可能是白化的烏鴉,記得不久前新聞上好像報導過動物出現大量白化的現象,我自認自己對於動物的辨認能力不算差,那應該就是一隻白化的烏鴉,牠正以暗紅的眼睛看向我。
正當我準備拍門叫喚父親時聽到門後傳來奇怪的聲音,隔著門那聲音有些模糊,像是女人呻吟的聲音,混亂中以規律的節奏在適當的間隔中起伏著。
我並非沒聽過這種聲音,應該說我會透過耳機聽著這種聲音自慰。我將耳朵貼在冰涼的門板聽著那斷斷續續的呻吟,藉由聽覺的刺激心裡無法抑制地衍生出了許多千奇百怪的幻想,接著那些幻想與旬的身影交融,眾多的,旬特有的親切微笑的臉孔與男女交融的身體幻象重疊變成了炫目的圖案……我身體內部的某個部分好像因此崩塌產生了個空洞……南風吹過洞內發出了共鳴,嗡嗡的共鳴聲聽起來像是殘酷的耳語。
不行!
我搖著頭甩掉那些奇怪的意淫,那扇裝著鐵欄透著光的氣窗映入了眼簾。
躡手躡腳走到窗戶墊著腳透過半開的窗口我往裡面窺探。
首先闖入視線的是廚房的不鏽鋼平台,坐落在廚房中央的不鏽鋼平台平時主要是用來揉麵糰或處理食材的,但現在平躺於那上面的卻是旬近乎赤裸白得跟麵團顏色相近的身體,豐腴的乳房半露在黑色的胸罩外,她曲著腳,腳掌靠在平台邊緣,黑色的蕾絲內褲掛在腳掌上。她表情恍惚,半開的嘴發出愉悅的哀鳴。
有個裸著上半身的男人將頭埋在她敞開的雙腿間,雖然看不到男人的頭,但他手臂上的天使刺青與蒼白的膚色無疑是父親。
而阿雄正站在角落,他也脫去所有衣物只穿了件內褲,刺龍繡鳳的黝黑皮膚因緊繃的肌肉看起來更有威脅性,他叼著根褐色的菸滿臉陶醉的吸著,淡藍色的煙霧飄在空中散發著濃烈的氣味,連在室外的我都聞得到。
我就著黃濁卻又飽和的燈光憋著不發出聲息看著眼前脫離了我認知的超現實光景。那空間之中的低飽和光彩頓時因為其中的事物變得亮眼而絢爛。
那畫面是:左上方阿雄的臉沒入了暗影中,只有在吸吐間亮起的菸頭紅光閃爍在他的眼中,右下角看不見頭部的父親細瘦的身體彎著,肋骨在開始泛紅的皮膚上畫出了條條灰色淡影,畫面的中央斜躺著的旬咬起了下唇,她挺起了身體雙腳扭動著,倒映在不鏽鋼平台中她的倒影像是透過細膩點描法所勾勒出其真實本質的迷離鏡像,慢慢夾緊的雙腿使掛在她腳掌的內褲掉到了地上,接著她忘情地用手指輕捏著自己的乳尖,胸罩已然脫離了原本存在之處。
我注視著那對美麗、堅挺、白皙滑嫩的乳房,感到了心臟的失序狂跳、喉頭乾渴、全身發熱,由頭頂奔流的血液皆往雙腿間匯集。
《維納斯的誕生》。
這幅在美術課本上看過的文藝復興名畫沒來由地浮出腦海並與眼前的光景重疊結合再一起。
之前,我一直並不覺得那幅畫中的維納斯美麗,毫無疑問,那是一幅經典名作,畫得精緻細膩,那枚飄浮在波浪之上開啟的貝殼,以及由其中生出的美神所構成的符號也成了一種文化象徵影響著後世,但就我看來,那畫中的維納斯總缺乏了某種力道,那種橫空出世,雜揉神祕與美麗,包含了世俗與神性的絕世的張揚。
而這一刻,眼前的景象卻讓我突然想起了這幅老師不斷讚揚的畫,而我突然也好像在當下認知到了自身的短淺,以及不足的審美,《維納斯的誕生》的美之所以能傳世必然有道理,而我現在目賭的就是屬於我的維納斯之誕生,誕生是美好又殘酷的一件事,因為只要任何東西以物質的方式誕生,那便必不可免地往死亡墮落。
瞬間,塞滿於室內濃密的光度突然微妙的黯淡了幾秒,因為兩旁的人物開始像是彩排過般的順暢地走起位,光影也隨之晃動,那光影彷彿是液態的般悠悠蕩蕩。
父親從旬的下腹抬起了頭,嘴上沾著透明液體反射著光,臉上帶著我不曾看過的表情,兩隻眼睛的瞳孔迷離而失焦,隨著父親抬起了頭,旬的雙腿反射性般地慢慢合攏,阿雄走向父親,父親則往阿雄的方向移動並接過了其遞來的菸,兩個人互換了位置,阿雄有些粗暴的撐開了旬的腿並將頭埋了進去,他將頭埋入了那白皙的雙腿之間,雖然看不到,但我也知道他正伸出舌頭舔舐著那我想像不出是什麼樣滋味的……雙眼依然迷離的父親吸著菸站到旬的臉龐邊,他吞吐著煙霧,期間還比起眼露出滿足的享受神情,他拉開了拉鍊掏出淡色尺寸巨大的生殖器,旬如同看剪餌食的魚般慢慢張嘴叼住了那還未完全硬挺的器官,然後吸吮了起來。她吸吮的節拍逐漸與阿雄擺動的頭慢慢地同步。
看著他們,我忽然感到了無以復加的悲哀與深刻強烈的羨慕,不論平時我跟他們相處得如何,終究無法真正進入他們那個我難解又遙遠的世界,對他們來說我只是個小孩,這扇窗所依附的牆分隔出的內與外就是我跟他們的關係缺乏深度的隱喻之實體化的狀態。
事後我再度回想起來,總覺得那幅異常難解而情慾橫流的悖德畫面是如此地美好,流著日不落帝國後裔血統卻在此落地生根的父親、日本人與閩南人混血的旬、總是戲稱自己是白浪花;有著外省與原住民之血的阿雄,雖然只是原始地以身體連結著,卻不可否認地他們是在某種自我意志與共識下將彼此交融在一起。
終於,阿雄也抬起頭爬起身,他壓在旬的身上並挺起了腰進入了旬的體內,出乎我意料的,阿雄也伸出舌頭跟著旬一起舔著父親的屌,父親就像是回應般,伸出手撫摸著阿雄的頭。
而我也伸出了手撫摸著胯下,我無法抑制的勃起,被隔絕在外只能透過窗戶窺探的我拉開了拉鍊掏出充血而發漲得難受的生殖器開始自瀆。
我目不轉睛躲在暗處偷看他們一邊打著手槍,不知何時旬已轉過頭望向我這邊,我冷不防地對上了她的視線,她漆黑的瞳孔猛地揪住了我,同時嘴角掛上意味深長的微笑。
被發現了嗎?我緊張地想著,卻沒有停下動作。
就在旬的視線注視下,我瞬間無聲地射精了。
6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oOM9o8iw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