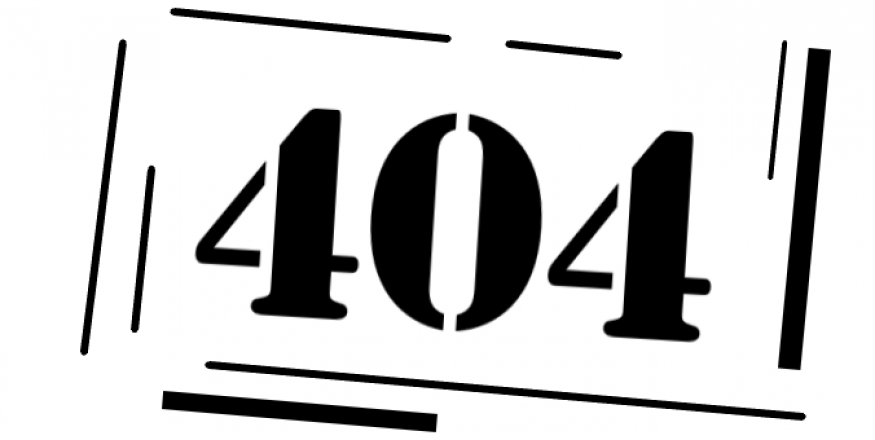蟬鳴鬧耳,夏日炎炎,縱使時間尚早,氣溫仍毫不留情的攀上三十度,大有一股要把學校烤融的氣勢,身處教室的學生一面盼著鐘聲響起,校方解開冷氣的限制,又可惜難得這麼清閒的早自習匆匆離去,上午第一節又正好是催眠的數學課。
還在經歷高中生每日起床後靈魂拷問的風紀選擇怠忽職守,決定在找到生活的意義前暫時停止去考慮被老師了無新意的訓話和口水糊一臉的後果,半夢半醒之間隨手翻著面前的講義,時不時瞟一眼窗外,檢查有沒有教官經過,再戴起耳機,自以為隱蔽的開起小差。
坐在左側靠窗的班長被基友煩到不行,轉身翻了個白眼,無可奈何的把數學卷和英文講義拍到他臉上,成功做了一回傻逼同桌的神仙再生父母救世主。
倒數第二排的女孩子像做賊似的往閨蜜手裡遞東西,在對方如釋重負的眼神裡嫣然一笑,桃粉色的唇膏閃著水潤的光澤,引來另一個女生驚豔的目光,三人嘰嘰喳喳的開始聊大熱天化妝有多麻煩和附近飲料店的夏季新品,正在討論班際籃球賽的其中一位男生一言難盡的看了下他們,眼裡的嫌棄多到快溢出來,接著驚恐的往後一縮,避免這群注意到他換新球鞋的損友趁其不備踩他一腳。
20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fOxgsrYO6Z
同學間的竊竊私語,趕作業時快速的書寫聲,低著頭偷吃早餐時塑膠袋悉悉嗖搜的聲音,斷斷續續的翻頁聲,老舊的吊扇因為許久不經潤滑而發出的嘎茲聲……
牆上的鐘滴滴答答的走,窗外是行色匆匆的上班族,早餐店熱氣蒸騰,趕路的駕駛著急的按著喇叭催促慢悠悠的行人,眾多商家拉開鐵門,城市的繁華熱鬧逐漸步上正軌。
這大概是準陽市最普通的夏日,晴空萬里,炎熱、聒噪,城市車水馬龍,五月十四日的早晨不過是日曆上所有被草草撕去的日常之一,伴隨著世界規律的運轉,人們按部就班的站上自己的崗位,按照平凡的劇本生活。
上班、下班,上學、放學,電視轉播著眼花撩亂的新聞,社會安定卻又不安全,燒殺擄虐跟禮義廉恥,正義與道德,法律和犯罪,社會新聞的頭版永遠不缺熱度,關於良好教養、優秀品格的路人爆料也占據了不小的版面,一切處於一個微妙的平衡中,不好不壞,某種程度上而言不該算平靜安穩,可又應該如此。
或者說一切本該如此。
直到上午七點五十二分又四十七秒,世界的劇本開始脫綱演出,魔法跟科學手拉手,一時興起和人類開了個玩笑。
最起碼當那棵難以言喻的詭異植物從學校操場破土而出並開始瘋長時,雲璟高中的所有教職人員跟在校生都希望這只是場逼真的整人節目。
然而現實總是不盡人意,漆黑醜陋的參天巨木中央化成一位慘叫的女人模樣,像遭受火刑的巫女,五官因怨恨而扭曲,細細聽彷彿有女人歇斯底里的尖嘯環繞,枝幹上長出猙獰的藤蔓,如海怪的觸手般在半空中亂竄,隆起的根部粉碎了操場,傾倒的籃球架在擠壓下應聲斷裂,脆弱的不似鋼筋鐵架,而是一觸及碎的玻璃……,被波及的建築和生物殘骸與血液,無處不在昭示這個宛若災難片的場景是真實存在的。
20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9DzefA9Opz
「啊啊啊啊啊———」,尖銳的叫聲充斥著校園,和崩塌聲交織成絕望。
高一七班的教室裡一片混亂,混亂的桌椅在整棟樓的劇烈的搖晃下甩尾飄移,天花板上的吊扇歪斜著,破損的一邊僅依靠幾條電線保持平衡,講台上方的日光燈砸向地面,燈管碎片濺了前排同學一身,第二列右側的日光燈斷了一邊架子,勉強靠另一根燈架支撐,坐在下方的同學有幸逃過一劫,後排坐在班級圖書區附近的同學卻沒那麼幸運,被傾倒的書櫃壓個正著,女孩在抽搐幾下後便沒了動靜,不知是死是活,幾本散落的圖書浸在血裡,觸目驚心,教室門前還有一灘刺目的血跡,濃烈的鐵銹味在不大的教室內擴散開來,淒厲的哭喊聲衝撞著耳膜,擾亂著人們的心神。
就在幾分鐘前,同學們還不以為意的瞎起鬨,慫恿膽大的人去一探究竟,一群玩得比較瘋的男生彼此推搡笑罵著,最後由承受不住激將法的人雀屏中選,罵罵咧咧的壯著膽子,拿起手機走出門去錄影。
他並不知道自己將要為熱血上頭的行為付出多少代價。
他們都不知道。
領頭的男生前腳剛踏出教室,後腳就被巨大的藤蔓貫穿了身軀,嬉鬧的表情僵在臉上,轉變成了不可置信的驚恐。
藤蔓瞬息間從他的胸口抽出,腥紅的血液沒了異物阻擋,像噴泉一樣湧出,站在他後方的同學呆滯在原地還沒來的及躲開,血液濺上白淨的制服,緩緩向下流淌,染紅嶄新的球鞋,溫熱的液體滑過臉頰,雙目無意識的瞪大,僵直著身體,眼睜睜看著受傷的男生被下一道襲來的藤蔓捲走,連帶的還有眼前的一大塊走廊。
他往後重心不穩的跌坐在地,看著一地的鮮血和幾塊被攪得不成模樣的臟器,才後知後覺的感到恐懼,噁心的感覺不受控的湧上,他別過身哭著發瘋似的嘔吐。
到底是青少年,平常表現的再跩再熊,也改變不了他們只是群不曾涉險的學生的事實,溫室裡的花朵沒見識過所謂人間煉獄,生平接觸過最接近此刻的場景可能是在電影院裡看的4D恐怖片,可那也不過是假的道具布景而已。
朝夕相處的同學就這麼突然的死在眼前,而自己甚至是慫恿他去送死的一員,心理防線的崩潰只需要一瞬間。
所有人驚叫著在教室內抱頭逃竄,無法冷靜,也無暇顧忌四周情況,只能依照本能掙扎求生。
而此時,在班級後排角落的位子卻顯得格格不入,像是自成一個不受干擾的方形空間,和現實所有混亂擦肩而過,隔絕了嘈雜的聲音跟人群的視線,保持著災難發生前的平靜常態,連桌椅都沒移動半吋。坐在這個位子上的人正閒適的趴在桌上補眠,任憑校園走向毀滅也無動於衷,在角落兀自巍然不動,充斥著恍若困在箱中的默劇演員般的荒謬感,而直到現在他才悠悠轉醒。
路君遷只感覺有股電流隨著血液從心臟蔓延至四肢,弄得他渾身發麻,又隱約感受到震耳的噪音和壓抑的空氣,掙扎了片刻後不情不願地坐直身體,煩躁的揉了一把亂糟糟上翹的黑髮,一抬頭,印入眼簾的便是看起來像像颱風過境還發生了命案的教室跟暴動的同學,然後他的目光轉向窗外,一條條極似異形的巨大黑色藤蔓在半空中揮舞,大腦嗡的一聲瞬間空白,他深吸一口氣,安詳的閉上雙眼。
假的,都是假的,一定是我醒來的方式不對,那玩意兒絕對不是詭蔓,我他媽是在現實世界,不是無限流世界的坑人遊戲場。
三秒後路君遷再次睜眼,看著分毫不差的場景,心想我操他媽的世界。
遊戲場的生物為什麼會來到現實?這是世界崩壞嗎?傳送出錯?還是隨機捉幾個衰鬼去闖關已經不夠它玩了,打算搞批大的?怎樣,無限流和現實擊個掌,給人類一個大大的surprise?
有病啊,不至於吧。
打斷路君遷腦內風暴的是扛著衝鋒槍破窗而入的金髮少年,白色的大衣在風中飄揚,教室左側外並沒有後走廊,窗外只有近二十公尺的高空,天曉得他是怎麼飛過來的。
季簫踩著窗框探身進教室內,絲毫不管被自己嚇到心梗的一眾學弟妹們,他制服外罩著一件不倫不類的醫師袍,但提著槍的樣子不像個醫生,比較像黑手黨幹部出街。
「路君遷,外找。」季簫懶洋洋的喊道,口吻跟今天天氣真好一樣,如果不是他從行為舉止到裝扮都像個恐怖份子,教室內的人都差點產生外面的一切只是幻覺而已的錯覺。
「喲,你班傷亡慘重啊。」他漫不經心的垂著眸,心裡默數了一遍班裡的倖存者,視線越過門口飛濺的血跡,聚焦在被書櫃壓著的學妹,凝重的皺了皺眉,而後朝路君遷語焉不詳的提醒,「技能能用,去頂樓。」
「你確定?」路君遷有點詫異的問。
季簫的衝鋒槍和醫師袍還能說是恰好和詭蔓一起掉落的道具,可能本來是他們要被傳送去這趟副本的,只是中途出了差錯,遊戲場的裝備和生物一起被扔來了現實,傳送失誤或是座標定錯……之類的,可如果連異能都能夠使用,那就事關整個世界法則的改變,這樣情況就比他想像的還要糟糕許多。
他捻了下指腹,又想到那股熟悉的電流,好似連指尖都在發顫。
回復路君遷的是季簫肯定的眼神,他跳下窗戶,無視建築物的晃動,踩著滿地的狼藉,穩當的走向圖書區,半跪下身,接著徒手搬開有兩公尺高的實木書櫃,把壓在學妹身上的書扔到一旁,伸手摸向她的脖頸,探了探脈搏,確認還有微弱的跳動後,握住她的手腕,一道金色的光芒化成柔軟的綢緞,一端繫在季簫的手腕上,一端向外延伸,纏繞上對方的小臂,再一路向全身包覆,隨後全數沒入她的身體,奇異的金色紋路散發著柔和的光芒,短暫的浮現在了皮膚上,轉瞬即逝。
剛才還處在瀕死狀態的女孩驟然睜開雙眼,身上已不見任何一處傷口,只有地上大量的血跡證明了她剛走過一趟鬼門關的事實。
「我、我、我還活、活著,我,不對,我沒死,我……咳咳咳——」被救活的同學猛的坐起,語無倫次的胡言亂語著。
一片寂靜。
眾人的表情混雜著震撼和不可置信,教室外尖叫、斥罵、推擠奔跑聲依舊,教室內的人說不上是鎮靜還是更混亂了,面前這個有過幾面之緣的學長,用著不知名的力量,輕易的,拉回一個將死之人的生命。
從突如其來的怪物開始,一切的常識和規律似乎都被顛覆,世界觀被打亂重組,未來的走向偏離正軌,從前平淡的生活,彷若黃梁一夢。
而身處漩渦中心的季簫完全不打算為任何人解惑,旁若無人的起身站好,繞過倒地的課桌椅,一把拉住路君遷往教室外拖,徒留眾人在原地徬徨。
***
教學樓外的走廊大多被掃蕩的殘破不堪,兩人踩著外圍僅存的磚瓦,閃過胡亂飛舞的藤蔓,輕盈的在破敗的樓道中奔跑,一系列動作堪稱飛簷走壁。
在這種一失足成千古恨、慢半拍等於粉身碎骨的情況下,路君遷正一邊跑一邊胡思亂想。
詭蔓屬於新手遊戲場的boss,根基不可移動,且具有標準攻擊範圍,醜是醜了點,但反正多看兩眼也不會瞎,時間一到就能解脫了,基本是讓新人苟過一場,拿個及格分和一點經驗值,不作死就能活的良心局,不過現在世界組成的情況不明,它會不會在固定時間內消失還很難說。
幸運的是,這株詭蔓的攻擊範圍,正好介於四棟教學樓之間——路君遷第一次慶幸學校把中央的行政大樓給拆了,不然場面一定很精彩——撐死也不過是把前走廊打爆、震碎幾扇窗,而且詭蔓降臨時正好是早修期間……
路君遷撇了撇嘴,估摸著全校師生的存活率應該有個八成,但在操場上運動的、在學校地下桌球室、停車場的、走廊上行走的、恰好不在教室的和作大死跑出教室圍觀的……大概都死絕了。
他們停在有晴樓和西洲樓之間的旋轉樓梯上,也就是學校的東南角,這個名裡帶西卻是南樓的機歪設計源自雲璟高中的初任校長,一個往詩裡隨便摘字的取名鬼才。
東樓叫有晴樓,「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的那個有晴,取個友情的諧音。
西樓叫輕塵樓,取自「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諧音清晨,代表黎明的到來,但只要是個人都知道,太陽他媽是東昇西落的。
南樓叫西洲樓,來自「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堅持不懈的在學生失去方向感的時候用川堂上夢想啟航的標語發出嘲笑,夢在西洲,但你不在,你在南風中凌亂。
北樓叫上寒樓,源於「木落雁南渡,北風江上寒」,被第一任校長硬安了個高處不勝寒的名頭,一聽就知道是在扯淡。
很難說究竟有多少個小可憐在考進來前抱持著中二且不切實際的幻想,然後還來不及圓一把狂帥酷霸跩的武俠夢,就被殘忍的現實擊倒在地——這個取自方位卻分不出方位的名字根本就沒有存在的意義!!!!
不管這棟樓叫什麼狗屁名字,能通上頂樓的樓都是好樓,季簫熟練的撬開樓梯間的柵欄門,把神遊天際的路君遷粗暴的推上頂樓,一點也沒有理會有晴樓崇高的友情理念的意思。
頂樓已經聚集了四位看起來就不太正常、在教導主任的記警告行為面前瘋狂踩雷的學生,在校園悲慘的災情下,相當沒心沒肺的玩著UNO,儼然一副拯救世界與我無關的鹹魚心態,得虧他們每個人在遊戲場裡都是令人聞風喪膽的大魔王,一點大佬風範都沒有。
「終於來了?你們也太慢了吧,半路被詭蔓嚇著了是嗎?需不需要哥哥我安慰一下?」夏言商端著那張禍國殃民的臉假抱怨、真調戲的開口,及肩的黑髮鬆散的紮成馬尾,左眼眼角有顆不明顯的淚痣,不笑的時候總帶點無辜的意味在,在一些考驗心機和欺詐的副本裡堪稱無往不利,本人也勢必把藍顏禍水四個字發揮的淋漓盡致。
一旁和他長相別無二致的夏言霜打出一張加四,蓬鬆的短髮襯著她有些輕飄飄的質感,像仲夏夜的精靈,她慢條斯理的推了下用來裝逼的無度數金絲邊眼鏡,涼涼的接話:「如果是讓他來安慰的話,建議多準備盒保險套以防萬一……喔,不是,是百分之百用的上。」,嗯,開口就是老司機了,差點忘了這貨走的是斯文敗類路線,失策。
「差薛寒……,他沒來學校嗎?」季簫直接無視這對犯病的雙胞胎及臉上寫滿鄙夷的路君遷,向團隊的總指揮問道。
「嗯,我已經通知過了,他大概十分鐘後到。言霜有用幻術掩蓋我們,但只限這個頂樓。」藍鈴百無聊賴的把手上的牌放到一邊,棕色的波浪捲髮隨意的散落腰際,慣用的髮圈已經不知所蹤,她單手支著頭看向路君遷,「試試看你的異能,查一下政府和國際動向,看各國的超自然現象研究處有沒有動作,順便把目前每個出現的無限流產物記錄下來,確認它的規律性……如果它有的話。」
藍鈴不客氣地要求道,語氣中帶有一絲篤信,似乎毫不質疑路君遷有能力辦到這樣的事。
沒有路君遷侵入不了的網域,沒有。
路君遷半倚著欄杆,朝藍鈴擺擺手,示意自己聽到了,接著闔上眼眸,仔細去調動浮動的能量。
黑暗在崩解、重組,靈魂失重漂流,失去對時間與空間的認知,迷失在無序中。
把人的一生格式化,是不是只夠放進一枚硬碟裡?
數道半透明的黑色面板像螢幕一般在半空中圍繞著他展開,在睜眼的一剎那,異能被法則容納,無數銀色的代碼從他眼前的面板鋪張開來,閃爍著傾洪而下,印入眼眸的字符宛如劃開黑夜的流星,帶來一種近似於本能的,靈魂的顫慄。
他能感覺到,異能不再是因為遊戲而被附加於玩家的獎勵,它變成融於血骨、銘刻在生命上的印記。
路君遷深吸一口氣,克制住近乎窒息的亢奮,伸手觸碰面板,隨著指令的輸入,全世界所有被網路捕捉到的異常動向毫無保留的向他展現,又在他的操作下轉換成一套完整的情報檔案。
「無限流產物的足跡幾乎遍佈世界,目前看來沒有一定規律性,各國的超自然研究處都陸續開始行動了,至於異常的原因,嘖,他們還不一定有我們清楚……,我再把詳細列表傳給你。」他把面板隱藏起來,整個人已經歸於平靜,相當無所謂的靠著年久失修的圍欄,任由脆弱的生鏽欄杆支撐自己的重量,漫無目的的思考著異常發生的原因。
異能已經不受遊戲場控制了,那可能是融入了現實的世界法則,比起任何一方崩壞,更像是合併,抑或是世界間地位晉升的角逐導致的互相吞併壯大?
一夕之間屠殺這麼多人類,看著也不像什麼和平友好交流啊,也不排除是無限流世界突然腦抽就是了,雖然機率微乎其微,但也不是沒可能嘛,反派搞事見怪不怪。
「有需要去把這玩意兒幹掉嗎?」季簫手癢的捏了下槍柄,居高臨下的俯視著詭蔓。
操場已經被毀的不成樣子,詭蔓的根基盤根錯節的延伸,毫無立足之地可言,靠近地面的藤蔓伸出了類似昆蟲的口器,鑽過四肢百骸,將那些運氣不好的衰鬼捲起碾碎後狼吞虎嚥的吸收著血液,再扯開頭蓋骨吸食腦髓,剩下血肉模糊的殘骸被蠕動的根部蓋過,成為下一輪的養料,校園裡的尖叫聲少了,多的是噁心的嘔吐聲和撕心裂肺的哭聲。
拉瓦席被斬首後眨了十一次眼睛,證明人經歷重傷後不會立即死亡。
而這是遊戲場,死亡是最奢侈的解脫,又有幾個人能享受這樣的優待呢?。
「可能暫時不行,藍鈴想試探一下政府那邊的深淺。」,坐在藍鈴身旁安靜洗牌的陸子說歪著頭朝季簫靦腆的笑了笑,暖棕色的眼睛彎成一彎新月,身上帶著小動物般的乖巧無害的氣質,乾淨的像童話書裡的陽光。
很難想像這樣的人能在遊戲場中活下去。
季簫盯著他沉默了片刻,終於按耐不住蠢蠢欲動的心,伸手揉了一把陸子說的頭髮,感覺成功被治癒。
對於這群有事沒事就被拉進遊戲過副本、日常被辣眼睛辣腦子的高中生們的心理健康,陸子說小同學的無償獻身功不可沒。
「啊,有人過來支援了。」路君遷展開面板,透過監視器的視角全方位展現學校四周的景象,一組大約十二人的武裝部隊正在輕塵樓的大門口外待命,而在一眾訓練有素的軍人裡,兩個穿著職業套裝的人影格外顯眼,也格外的鬆懈。
「他們兩個是『玩家』。」藍鈴指出,「這個女生我有遇過,代號叫滿月,我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她穿得像個中二病魔法少女,拿著咒語書在副本裡飛天遁地。」
藍鈴永遠忘不掉她穿著那身死亡芭比粉的蓬蓬裙跟帶金色蕾絲的白色厚底馬靴,騎著一隻飛天獨角獸在中世紀副本裡閃耀登場時,教徒npc那個懷疑人生的眼神。
巴不得人家把你燒掉是吧?
可是那是獨角獸欸!(大聲逼逼gif.)
最後是藍鈴以一己之力帶飛全場拿下勝利,但這個遊戲還沒開始就昭告天下快來殺我的行為實在太過令人印象深刻,給當年初出茅廬的藍鈴造成了重大心理創傷,至今仍難以忘懷。
第一次見到比她玩得還自暴自棄的人。
直到她結識了薛寒跟季簫,遊戲場高級擺爛玩家,一個高攻高防人形自走外掛、能動手絕不走劇情的暴力分子,和一個把治療異能用成新型折磨手段、拎著重軍火日天日地的奶媽。
好好的副本都被這兩個天煞孤星玩成pvp戰鬥遊戲,屬於建一座迷宮給他解謎,他當場拆牆直線前進到終點的那種遊戲體驗破壞者。
一種物理意義上的自爆自汽。
屏幕裡的月光擺弄了一下繽紛的髮飾,帶著花彩雀鶯輕盈活潑的夢幻感,一邊哼著輕快的小曲,一邊蓄勢待發的召喚出魔法書,她身旁的男子拿著對講機,神色嚴肅的向另一端的人匯報現場狀況,監視器呈現的畫面稍顯模糊,他們只能勉強從口形辨識出幾個明顯的語詞,但真正的麻煩不在這裡。
離學校兩條街以外的一條無人小巷內,照不到光的角落陰影攢動,黑暗像浪潮般湧起,一抹人影出現在其中,眨眼間又隨著所有異相消失不見,小巷內再次歸於平靜。
那是薛寒。
ns 15.158.61.48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