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溫塵輕輕地呻吟一聲,是將要醒來的徵兆。但在睜眼之前,頭就先疼了起來,他恍然意識到自己是宿醉了,好像還作了什麼奇怪的夢,可醒來之後就不記得了。
他仍閉著眼,想要稍微賴床一會,可身下的觸感卻又奇異的柔軟,並不像官宅的床鋪。
這時,忽有一隻手伸了過來,輕輕地揉了揉他的太陽穴,一個不該出現在這裡的聲音驀然從他的身側響起:「醒了,身體還有其他不適嗎?」
溫塵聽見這聲音時如遭雷擊,渾身都僵了。他立刻睜開眼,果真看見景帝睡在自己身旁,而這裡根本不是他的官宅,分明是天子的寢殿。
他第一個念頭是自己是否酒後失態了,才冒犯了景帝,正惶恐地要起身下床謝罪。可他不過才稍微動了動,身後的隱祕之處竟傳來疼痛感,讓他悶哼一聲又倒了回去。
景帝溫和的眉眼隨即露出擔憂:「是傷到了嗎?朕看看。」
這句話能傳達出的意思太多了。
姜元臻並不遮掩,將某個事實在他面前赤裸裸地揭開。溫塵的臉色驟然變得慘白,竟躲過了景帝伸過來的手,強撐著身子下床,什麼話都不肯說,只伏在地上行了一個跪拜之禮。他身上只著單衣,身形削瘦,又強忍著不適,可偏偏將這禮行得十分標準,骨子裡十分倔強。
溫塵是在明明白白地告訴他,他們是君臣,身分有別,縱然私下交談甚歡,也絕不是可以混為一談的事。
無論昨晚是不是酒後亂性,他是否真的御前失儀了,景帝若沒有那個意思,根本就不可能會變成現在這樣。溫塵縱然內心驚怒不已,可他確實是有文人傲骨的,既不肯在這時失態,又得顧及景帝顏面。畢竟這不是他一個人的皇帝,而是天下人的皇帝。
姜元臻見他如此堅決的模樣,心想果然如此,只是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溫塵聰慧又敏銳,恐怕已經把事情經過想個通透了,想要騙他是行不通的,只會把他越推越遠。姜元臻這時只能實話實說:「是朕授意的。」
溫塵單薄的身子一抖,驚愕地抬起頭來,但隨即又俯低下去。
「溫卿,不管你信不信,你都是朕的良藥。」姜元臻又是一嘆,言詞真摯,「朕也絕沒有欺辱你的意思。」
姜元臻簡短幾句話就將事情說過一遍,包括他無意間發現兩人只要有肌膚上的碰觸,即使當日天氣再糟糕,他竟也不會發病,甚至這病弱之症還有好轉的現象。昨晚那樣的纏綿已足夠成為證據了,否則以他這樣的病軀,原本能不能做到最後都是未知數。
溫塵每聽一句,臉上的血色就褪一分。他總算明白景帝為何總是在大雨時叫他過來了,原來……原來是這樣。
他明明很清楚彼此的身分有別,皇帝利用臣子也是應該的,可心裡又莫名抽痛起來。
「溫卿,朕確實愧對於你。但朕也並非完全無意──」
溫塵聽這開頭就感覺不妙,恐怕景帝會說些什麼他不能承受的話,突兀地打斷道:「陛下!請陛下慎言。」
姜元臻停了停,卻還是繼續說了下去:「縱然前面說的聽起來像是藉口,你酒醉沒了印象,或許也不相信。但昨晚,確實是我情不自禁。」
姜元臻並未用屬於皇帝的稱呼,而是以一個男子的身分說出這句話。
只一句話,就讓溫塵方寸大亂。他跪拜的身子顫抖起來,更顯得單薄瘦弱,像是無法支撐一樣。對於昨晚的事他確實什麼都記不清了,只餘今早醒來的驚怒與疼痛而已。他現下更是混亂不已,加上腰腿痠軟,幾乎要跪不住,可還是倔強地撐著:「臣惶恐,臣懇請告退……」
姜元臻知道再說下去,溫塵就要長跪不起了。他也不願意逼得太緊了,放軟了語調:「去吧。」
溫塵又行了一禮,起身時站得不穩,像是隨時都要跌倒一樣。
姜元臻何嘗不想親自去扶他,但恐怕自己的靠近只會讓溫塵更加驚恐而已,便想喚曹裕進來幫忙,可又被溫塵給阻止了。
溫塵昨晚褪下的官服就妥善地放在一旁,用薰香去了布料上的酒味,還摺疊得整整齊齊,彷彿諷刺地彰顯著昨晚的聖寵。他精神有些恍惚,沒注意到觀音玉珮就放在最上方,匆匆忙忙地想要穿衣離去,順手一扯,那玉珮竟就直接摔落在地,四分五裂了。
溫塵頓了一頓,像是回神了,但終究是沒撿起來。
姜元臻見到此景,竟莫名有一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悲涼感。他又賜給了溫塵另一塊隨身玉珮,溫塵不敢不接,卻連一眼也不敢多看,謝過之後就匆匆離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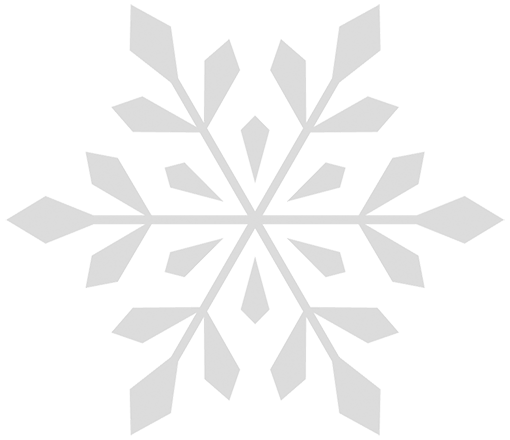
而藏在龍池裡的妖魔終於有了動靜,墨極追蹤數十日終於有了成果,也連忙召集眾人前來。
除了馥顏師徒幾人與清靈門弟子外,守護龍池的瑾璃也在場。但因事關重大,更意外牽扯到容華的恩人,於是墨極也派人邀請炎冥與容華前來。只是時間到了,兩人卻遲遲未到。
馥顏冷哼一聲,似有不滿:「恐怕有人嘴上說著要改過向善,其實根本就只是做做樣子吧。」
墨極聞言並沒有什麼表示,只是問了身後的弟子是否確實把消息傳達給兩人了。
那名弟子神色毫無異常,卻有些心虛,但唯恐師尊怪他辦事不力,只表示已轉達了,卻沒說出是託人轉達的。實際上,他在去的路上遇見潛冉,因還要趕著去其他地方,又見潛冉有空,便把這件事交給他了。他先前與萬靈殿的弟子毫無交情,也不知那魔頭與萬靈殿的糾紛,只因兩人的年紀相當,再加上潛冉年少得名,沒有什麼架子,路上便多聊了幾句,就這麼熟識起來了。
如今師尊問起,那弟子才偷偷地看了潛冉一眼,見潛冉似乎沒什麼反應,心想只是傳個話而已,或許並不嚴重吧。
墨極聞言便沒有再問:「既然如此,我們就開始吧。」
墨極雖有追蹤祕術,但也要妖魔活動的時候才可以偵測得到。昨夜他已窺得妖魔的一部分,便口述出來:「這妖物身軀細長,通體黃棕,身上有鱗,周身有黑霧繚繞,看不清真面目,但似有控霧之能,加之那霧氣有毒,能使龍鱗潰爛。一旦它隱身在霧氣之中,我便追蹤不到了。」
此類妖魔的特徵並不難猜,瑾璃便道:「難道是蛇妖?還是蛟龍?」
墨極卻搖了搖頭:「就算是蛟龍也該畏懼真龍三分,更不用說是吸食龍氣了。我擔心……會是最棘手的螣蛇。」
騰蛇傳說是上古神獸,足以與龍媲美,但也有好壞之分,若臨世時現凶兆,便是災害的代表。這類上古妖魔最難對付的地方不在於力量有多強大,而在於螣蛇是噩夢驚恐的代表,見之易生心魔。心性堅定者或許不受影響,但凡人或心性易受動搖者,就易被引誘控制。若出現在凡間,就容易引其極大的災禍,例如暴動、戰爭等殺戮,又或者螣蛇善水司火,也會引起洪災、火災。
「雖不知為何出現會在龍池裡,但顯然真龍也想將牠困在池底,避免牠出去害人,才至今都沒有重大災害發生。或許螣蛇是為了脫困,才意欲吞噬真龍壯大自己,但長久下去,對景帝的性命會有危害。所幸──」墨極說到這裡時竟頓了頓。
馥顏不由得問道:「發生什麼事了嗎?」
真龍是天子的化形,一舉一動皆是景帝的意志。雖然他未親眼看見,但觀那龍昨晚徜徉游水的姿態,也能知景帝正在與人翻雲覆雨。恰巧溫塵元神出竅,他才見到那名人類的模樣,竟是容華的恩人。
墨極又道:「我算溫塵此人命格,體質極為特殊,因血肉能增長修為,世世皆受妖魔所害。這一世若非容華仙君保命,他早該命殞在岐山。」
馥顏聞言冷諷一聲:「那人真是亂來,擅自救那魔頭本就不該,現下又亂了天道。」
「也不能這麼說。」墨極又道,「如果溫塵沒有活到現在,景帝就真的沒救了。能滋養妖魔的血肉,對真龍也是極有好處的。」
總而言之,景帝若是無故枉死,那才真是天下大亂了。不知道該說是歪打正著,還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數。
馥顏不再說話了,但顯然不以為意。
而站在她身後的潛冉卻是握緊手心,指甲刺入肉裡,低垂的目光越發冰冷。被他猜中了,這也是他故意沒有將消息告訴那兩人的原因。螣蛇一出,血王藤的危害彷彿就被大家拋在腦後了。現下聽墨極之言,竟還有與那魔頭合作之意。潛冉是萬萬不能讓此事發生的,他絕不能讓那魔頭有翻身的機會,否則卓瑤上仙的事不曉得什麼時候就會曝光,萬靈殿也會跟著染上汙名,仙門榮光不再……
墨極召集大家過來,除了告知妖魔的危險性之外,也是希望大家一起合力布下結界,防範於未然。京城人口眾多,一旦螣蛇突破束縛,雙方大打出手的話,恐會造成無辜的百姓受害。再加上既已猜到妖魔的原身,就更不能像先前那晚一樣,讓那些帶有惡念的金藍色泡泡流入百姓之中。一旦噩夢生成,就難以擺脫螣蛇的控制了。
馥顏雖然心直口快,卻是嫉惡如仇,對於此事自然不會推託。
而等到清靈門的人都走了之後,潛冉才走上前,一臉沉重的樣子道:「師尊,有一事我不知該不該說。但現在不說的話,之後恐怕就遲了……」
潛冉很少會有這種猶豫不決的樣子,再加上先前未能保護好弟子,她這個師尊心裡有愧:「何事?你說說看。」
潛冉看了師尊一眼,而後彷彿下定決心一樣:「其實那天我遇上了要去通報消息的清靈門弟子,見他忙碌,我才答應幫他轉達消息,但是……」
馥顏聞言隨即皺了眉頭:「你去找那魔頭了?是他又對你做什麼了?」
「不是。可是……」潛冉露出了古怪的神色,說道,「弟子先前總覺得他們兩人怪怪的,明明一個是魔頭,一個是仙君,可偏偏又時常膩在一起。換做是其他人,湊在一起不大打出手都是好的了。而那容華仙君又生得……生得這般出眾。他們的行為舉止又處處透露著古怪……」
馥顏細細回想,確實也覺得有點不對勁,可她還是聽不出潛冉想表達什麼意思,便直問了:「潛冉,你究竟想說什麼?」
「那日我去找他們,聽見房門裡傳出一些奇怪的聲音。那魔頭與那仙君似乎……」
「怎麼了?」
潛冉竟跪了下來,直言道:「是在做苟合之事。」
「你說什麼?!」馥顏聞言震驚極了,雖說不是沒有先例,但仙魔苟合可是違逆天道之事。馥顏的神色也沉重下來:「你可確認清楚了?」
潛冉見師尊似乎信了,又惶恐道:「弟子不敢撒謊。弟子……弟子先前在路上就已察覺不對勁,那魔頭對那仙君的態度似乎十分親暱,有幾次……有幾次甚至還看見那魔頭的身上有些曖昧的痕跡,但弟子當時只是猜想,不敢隨意汙衊仙君清白。直到這次,才終於確定下來……」
潛冉這番話正是暗示他們苟合已久,恐怕自源城那時開始,又或者更早的時候就……
馥顏久久沒有說話,眉頭擰得很深,似乎也在回想那魔頭的舉動。兩人若不是這種苟且的關係,那人又為什麼要袒護那魔頭。原來是早就墮落了,要替那魔頭與自己掩蓋種種惡行。她恍然大悟道:「難怪……」
「師尊。」潛冉又在這時候認罪道,「弟子不敢在墨極掌門面前提起這件事,也是擔心……」
馥顏聞言又是冷哼一聲,說出了潛冉不敢說的話:「為師也看得出來,墨極是有意偏袒他們。清靈門一向公正,沒想到墨極也會有糊塗的時候。」
「那……」
「不用擔心。只要讓墨極看到證據,相信他就不會再袒護那魔頭了。」
「是。」潛冉低頭恭敬道,唇角卻牽起一抹冷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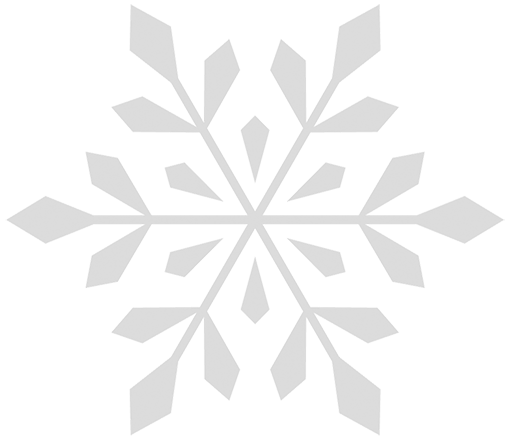
而在朝堂上,姜元臻已好幾日沒有看到溫塵的身影了。他用目光詢問一旁的曹裕,曹裕這才上前小聲道:「溫大人今日也告假。」
姜元臻露出苦笑道:「想來是不願看到朕。」
曹裕原也是這麼想,但又覺得溫塵不像是會逃避之人,便把聽到的如實說出:「聽說是病了。」
姜元臻皺了眉頭:「傳喚太醫了嗎?」
曹裕搖了搖頭,卻只看著景帝不說話。以溫塵的性子,受了屈辱,又傷在那種不可告人的地方,自是不願讓人知道的。
姜元臻看明白曹裕的意思了,男子與女子不同,他也是頭一次,未做到善後之責,那日又見溫塵跪在冰冷的地上許久:「是朕疏忽了。」
這時眾臣已齊齊上前朝拜,姜元臻便不再多說,可在議事的時候卻有些分心了。
下朝之後,曹裕見景帝仍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樣,便主動提議道:「陛下要是擔心的話,老奴親自帶嘴嚴的太醫去看看吧。」
「好。」姜元臻想了想,又道,「他若不願看病的話……就別讓太醫知道了。」
曹裕明白景帝的意思了:「是。」
隨後曹裕換了衣服,立即帶著一名醫術高明的太醫出宮去了。
溫塵確實是抱病在家,喝了藥卻始終不見好,急得小翠又到處請大夫,還以為在源城那時水土不服的毛病又犯了。可這一次溫塵卻不讓她聲張,甚至也不願向大夫說明病因,於是這病總也不見起色,就這麼拖了好幾日。他知道多日未上朝,同僚恐怕會對他有什麼意見,認為他是仗著景帝寵愛就目中無人了……可他勤奮苦讀,憑藉自己的實力高中狀元,沒想到卻發生那樣荒唐的事,讓他突然間就感到茫然了。
這時小翠急匆匆地進來,說宮中來人了。
溫塵臉色一白,但很快又鎮定下來,披上了外衣之後,才開門待客。
曹裕是孤身帶著太醫前來的,並未張揚,這讓溫塵放鬆不少,可還是頻頻地朝曹裕的身後看,稍微透露出不安與緊張。
曹裕見狀無聲地嘆了口氣,小聲道:「陛下沒有來。」
溫塵這才真正放鬆下來,可又莫名地感到有些自己也說不上來的失落。面對曹裕,他的心情還是複雜的,態度也比以往還要疏離。雖然知道曹裕也是聽令行事,可他也清楚景帝私下裡是親信這個內侍的,曹裕若是開口勸諫過,景帝也是會聽進幾分的。
太醫並不知道原由,只是正常地看病把脈,一提到病因,溫塵頓時就感到渾身不自在,但果然不肯多說,隨便找個受寒的理由含混過去了。
曹裕站在一旁也沒有多說,只有小翠因憂心溫塵的病,提了一句在源城水土不服的事。
曹裕面上不動聲色,卻默默地記下了。
而宮中的太醫醫術還是比較精湛的,觀察溫塵的神色,不到鬱結於心的程度,但近日情緒恐有大起大落,便在藥中開了安神的方子。
而後曹裕藉口有事要跟溫塵談,小翠便先請太醫出了院子,獨留兩人交談。
溫塵還以為是景帝傳了什麼話,不由得又緊張起來。沒想到曹裕只是遞了一罐藥膏過來,是抹在傷處用的。
溫塵一見到那東西,臉色又白了起來。
曹裕道:「放心,這是我向其他太醫要的。不會有人知道這件事。」
溫塵一頓,這才收了下來。
曹裕雖是內侍,但跟在景帝身邊多年,在宮中也算是有不小的威望,私下自然不必以奴才相稱:「我知道溫大人對我有怨,我也認了,畢竟我確實是向著陛下的。陛下雖心慈仁善,但自小學的就是帝王之術,凡事都得先為大局著想,個人的私欲只能擺在最後。一旦有任何忍讓與妥協,難保不會有臣子利用這點欺到他頭上來,所以有些事陛下即便心懷愧疚,也不得不做。」
曹裕似是想起了景帝抱病登基時那段最艱難的日子,又感嘆道:「陛下年紀輕輕,卻已為天下犧牲了很多,包括他自己。」
溫塵聞言一愣,卻未說話。
曹裕暗中觀察溫塵的神色,又繼續道:「難得陛下有心儀之人,我自是不忍破壞。」
溫塵張了張口,想要反駁,可卻又說不出來。這幾日冷靜下來之後,他其實也明白,景帝是一國之君,君無戲言,實在不需要因為愧疚或者安慰他而說出那句情不自禁的話來。然而明白是一回事,能不能接受又是另外一回事。畢竟這實在是有違君臣倫理,也太過驚世駭俗了。
「那也不必……」溫塵不小心脫口而出,卻又不說下去了。即便事實已經發生了,他還是說不出景帝是趁人之危這種貶低的話來。
然而曹裕卻聽懂了,平和問道:「溫大人,若你事先知道陛下的心思,還能夠接受嗎?」
溫塵沒有回答,可答案已經很明顯了。若能有選擇,那他必然是不會接受的。
曹裕再直白地問:「既然接不接受都不影響結果,你是想要在清醒的情況下面對這一切,還是不清醒的情況下面對這一切?」
溫塵的臉色又慘白起來。
縱然找再多的藉口也離不開逼迫溫塵就範的事實,但這確實是景帝考慮過最不會讓彼此難堪的情況了。若他真有心要威脅一個人的話,以溫家全族上下,或者挾持他在朝中為官的父兄性命,也不怕他不從。可景帝究竟沒有這樣做。
曹裕點到此處,也不再多說了,只說了一聲告辭之後就離開了。
而在官宅外頭,一輛樸素的馬車在門前等候多時。太醫已被另一輛馬車先行送走,並不與曹裕同行。曹裕掀開車簾上了車,直到簾子落下,完全擋住了外頭的視線後,才恭敬而小聲道:「陛下。」
原來姜元臻竟一直坐在馬車上,穿著樸素的裝扮,這已是他即位以來罕見的幾次出宮了:「溫塵怎麼樣了?」
曹裕將太醫所說的話,開過的藥方一字不漏地說了,卻未將方才的對話如實稟告。
姜元臻見曹裕又在裡頭待了好一會,大概也猜到了:「你是不是多嘴了。」
曹裕竟也不否認:「陛下恕罪。」
姜元臻難得有些欲言又止,竟少了一些往常的果斷:「他怨我嗎?」
曹裕只是道:「溫大人會想明白的。」
ns 15.158.61.55d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