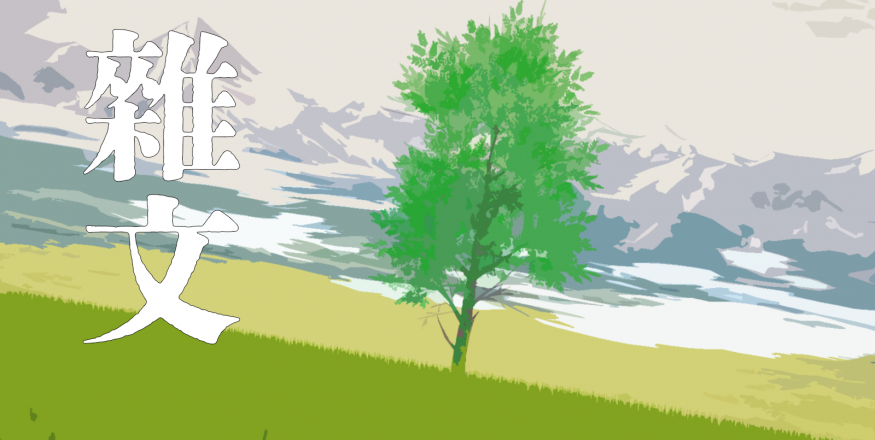粗糙灼熱的沙粒陷入背部的傷口裡,後腦勺的衝擊震得我一陣暈眩。我強行掙開眼睛,一個黑影擋住天上的烈日。
身體反應比意識更快,我往右方翻滾,巨大的石斧劈在原先的位置上。我雙手撿起落在一旁的長柄槌,利落的翻身站起來。
周圍的群眾大聲歡呼,棕岩獸人們拍動他們巨大的雙掌,低沉的掌聲恐怕就要把我的心跳震停。
牛雷氣喘吁吁,鼻環被吹得上下擺動。他舉起石斧,不耐煩的拍掉被我的汗水沾濕而黏到斧刃上的沙粒。他的體格比起圍觀的棕色大塊頭們都要壯,單是脖子就比我的腰還粗。
我把凌亂的長髮撥到身後,明明束了馬尾,但髮絲總是不聽話的跑到肩上。我把長柄槌横舉到身後,大喝一聲箭步衝向牛雷。我以左腳為軸心,旋身槌向他的左腰。
牛雷不退半步,左手硬生生的接住了槌頭。我立刻放開柄子要向後跳,牛雷握住槌頭向上揮,柄尾砸中我的下巴。我整個人飛到了天上,一剎的停頓後又重重摔到地面。
更多沙子陷入傷口中,我的尖叫都被歡呼和掌聲給淹沒。牛雷把長柄槌拋到半空接住柄尾,順勢直擲向我。我的頭往右擺,槌頭落到距離耳朵三厘米旁,揚起的沙子蓋到臉上。
「時間到!平手!」裁判敲響代表戰鬥結束的銅鑼,獸人們再次鼓掌。
牛雷走近我,眼神充滿了不屑和疲憊。我對他微笑,伸出食指和拇指比出『差一點點』。牛雷向我的臉上吐了一口水,又黏又臭的,我閉著眼睛,屏住呼吸,抆緊嘴唇,用手把污物擦掉。
當我再張開眼睛時,牛雷已經離開,圍觀的獸人陸續散去。我大字型躺在沙地上,任由烈日撕裂皮膚,總算捱過晨練了。
「站起來!索爾!」
正當我想小睡片刻,身體就被老獸人狼風粗魯的硬拉起來。一雙花白的眼睛打量我身上鮮紅的傷痕。「過來洗傷口。」他一手抓住我的手臂,另一手握住拐杖,滿步蹣跚的拉著我擠過人群,走入陰暗的帳幕裡。
我坐在老舊的木椅上,深深吸了一口陰涼的空氣。狼風在櫃子上取下一酒瓶,拔開木塞飄出濃烈的苦澀氣味。我趕緊兩手撐住膝蓋並咬緊牙關,他倒出藥酒淋到我的背上。傷口像被火燒般灼熱,我捏緊膝蓋忍住嗚咽。沖走傷口的沙粒後,狼風掀開旁邊的瓦窯,挖出黑色的藥膏厚厚的塗抹在背上。
我嗅著早已習慣的臭味,視線在帳幕裡遊走,三個歪歪斜斜的木櫃,一個堆滿了藥酒,兩個塞滿厚書,書脊的標題皆退色到難以辯認。這裡十年如一日,嘗試在老巫醫的帳幕裡尋找新事物,簡直是異想天開。
「你還要窩囊到甚麼時候?」狼風的口水都噴到背上,我肯定巫醫的唾液沒有醫藥價值。
「你沒看到牛雷的樣子嗎?他被我累壞了。」我奮力擠出嘲笑。「他至今還沒贏過我一次。」
「你也沒贏過別人半次!每次晨練你都只是挻到時間結束!對手是別人還好,每次輪到牛雷當對手,你都一定弄得滿身傷!」
「痛!痛!痛!塗那麼大力會加深傷口的啊!」我跳起來面對狼風不讓他再觸及我的背,「反正我又不夠他們壯!打不贏就只能在不輸這方面努力啊!」
「你沒有更多的機會了!下星期你就十六歲,在成年禮之中只許勝利沒有失敗更沒有打和!明天是牛雷的成年禮,你最好去學習學習!」狼風把一條姑且能稱為背心的髒布碎扔給我。「現在就去打水和劈柴!最好把明天的活兒都幹好!那才騰得出時間去觀禮!聽到就快滾出去幹活!人類小子!」
狼風把我趕出了帳幕,我穿上背心,身上滿滿的藥膏臭味,不過這正符合我的形象。『人類』二字把我和這些大塊頭之間區別出來,這個詞語的意思是怪胎。
ns 15.158.61.51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