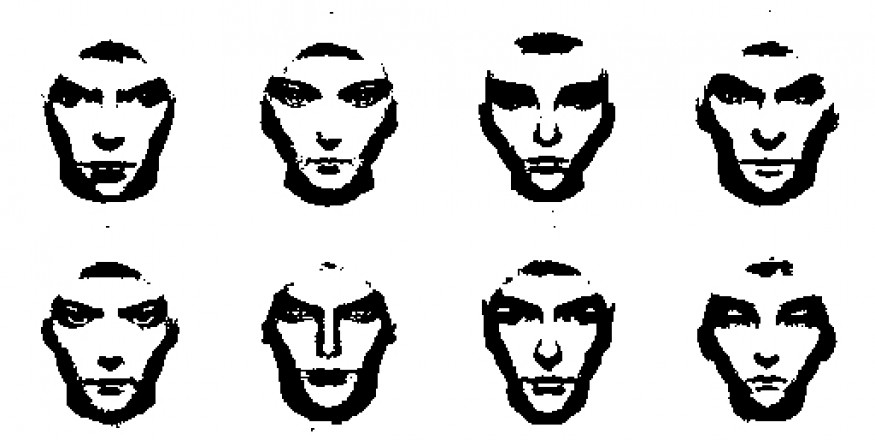講座結束,眾人排隊讓教授為他們的書簽名,又熱情地與教授輪流合照,無論什麼要求,教授都一一照辦。之後大部份來賓散去,只剩下少數人三三兩兩圍著講臺而坐,與教授作小組討論,彼此深入交流。我本想過去跟教授敍舊聊天,但見有些不認識的人在場,便不好打擾,逕自離開宴會廳,與徐健會合去了。
酒店是五星級的,本城中數一數二,裏裏外外,氣派豪華,可我依然是一套背心衛衣,球褲球鞋,大剌剌走進高級餐廳,管他的。
剛一進去,服務生即上前招呼。我向他擺個手勢,直往前走,穿到餐廳最裏邊,尋找徐健身影。
正值淡季,座位只七八成滿,一眼便能瞧出徐健的位置。他拿了個上佳好位,倚靠落地大窗,面臨海港夜色,真是好樣的。我奇怪他怎麼只一個人坐著,便問道:「喂,大老闆,怎麼只有你一個,小伊呢?」他往頭上飄飄然的鬈髮一撥,漫不經心回道:「找過了,還未回覆,不知到了什麼地方玩呢?」我心裏納悶,用自己手機打去,沒人接聽,便發訊說講座完了,叫她快來餐廳。
徐健趴在桌上道:「反正我們吃的是自助餐,吃完可以再拿,用不著等小伊啊,我肚子已經在打鼓了。」我喃喃道:「她應該很期待這一餐才對,現在終於等到了,人卻不知飛到哪裡去。你啊,罪魁禍首就是你,教她尋什麼『雙胞胎』,弄得她一門心思都放在上面。那日壽司店裡你沒看見,她一講起那個M埠的『姊妹』,眉飛色舞,停不下來,一直到人家的店快要打烊才肯打住。這丫頭恨不得馬上游水過M埠,去見她的『雙生姊妹』一面。」
徐健興奮道:「不止她想見,我也想見啊!阿放,你不覺得很神奇嗎?兩個一模一樣的人啊!你們去的時候千萬要叫我,我可不想錯過那個千載難逢的場面。」我「嘖」了一聲,對他大翻白眼,轉頭望出窗外。徐健繼續說:「我們先開動吧,不用等了,反正遲來的不止小伊一個……我去隨便拿點什麼肉來。」說罷,逕自站起,離開座位,拿吃的去了。
等他捧著兩盤肉回來後,我就問他:「你剛才說什麼?要等的人不止小伊一個,還有其他人來嗎?」
徐健擠眉弄眼,賊忒嘻嘻地說:「你待會不就知道了,心急什麼啊,總之今晚一定讓你吃得開心愉快。」一說完,又像風一樣跑走了。看他鬼頭鬼腦的模樣,又不知在打什麼主意。
來回幾趟,滿桌子都是杯碟盤子了。我們兩個男人顧得上什麼儀態,乾脆狼吞虎嚥,給它來個狂風掃葉,風捲殘雲,就算是佳餚美食,也沒耐性慢慢品嚐了。反正是自助餐,吃多少是多少,大肚能容!
忘情埋首於餐桌之際,一把響鈴般的女聲自背後傳來:「對不起,來遲了。」原以為是小伊,想想聲音不太像,似乎比較成熟,便放下刀叉,回頭去看,竟是剛才發佈會上常常與姜教授交頭接耳的年輕女士。
徐健當即站起,拉開座椅,打個手勢,邀請女生就坐,十足的紳士風度。那位女士笑著坐下,向我打了個招呼,然後對她的朋友說:「聽說今晚有人請客,我可不會客氣哦。」徐健笑道:「隨便吃,隨便吃,你看我們都已開動了,吃多少也無所謂,反正都是一樣價錢。」那位女士忍不住噗哧一笑道:「怪不得吃自助餐,原來早有打算,真是服了你。」
二人你一言我一語,談得不亦樂乎。我這才知道眼前女士原來是姜教授女兒,今晚陪同父親出席發佈會,完了後跟我一樣,往隔壁赴徐健的約。她全名「姜蘇靈」,可名片上卻少了個「姜」,僅顯示「蘇靈」二字,認識她的人只道她姓蘇,往往「蘇女士」「蘇醫師」這樣叫著,鮮有知道其父就是鼎鼎大名的姜齊悟教授。至於她為何這樣做,新認識不便多問,跟著叫就好了。
經過一番介紹,我認識了這位精神專科醫師,就是多年前治好徐健重病的大恩人。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呢?不記得了,只知徐健曾患上嚴重抑鬱症,身心受創,不似人形,連我這兄弟好友也拒而不見。你無法想像,如此樂觀開朗,交遊廣闊的一個人,可以患上那麼可怕的心理疾病。當時全賴蘇靈悉心救治,否則他到現在也未必能康復過來。徐健銘感這救命之恩,一有空就上醫務所探望蘇醫師,閒話家常,吃飯聊天,二人遂建立了聯繫,成為無所不談的好朋友。
他對蘇靈道:「前陣子我和阿放有個剛結婚的朋友,妻子新婚當晚竟不認得丈夫,更妄想自己是另一個人,我們差點就要把她送去你的醫務所,只是中間出了意外,去不成,要不然你和阿放早就見面了。」這段經歷,記載於《記憶體》一書中。
蘇靈輕輕托一下她的薄片眼鏡,有意無意道:「有緣的話,遠在千里能碰面;無緣的話,坐在對面不相逢……哎呀,不好意思,我說多了,謝先生,很高興認識你。」微笑伸手,與我相握。我只覺她的手又小又軟,像塊玉一樣溫潤細膩。
接著,蘇靈和我們一起用餐。只見她用刀叉切割蝦球,輕輕送進嘴裏,含住細細咀嚼,咽下了,吃另一塊,又是細細咀嚼,慢慢品嚐;嘴角沾了少許醬汁,便立刻拿紙巾抹掉,始終吃得有禮有節。她見我們直勾勾地看她吃東西,不禁有點尷尬,嗔道:「你們別老是看著人家吃飯啦,剛才你們談什麼?現在就繼續啊,我也可以參與一下嘛。」
徐健接口道:「我們在談陌生雙胞胎的事啊。阿放有個妹妹,在網上找到『另一個自己』,沒騙你,真的長得一模一樣。」蘇靈是姜教授女兒,大概頗有學識,對這種怪事,也許有客觀一點的看法,於是我便詢問了她的意見。
蘇靈抹抹嘴巴,喝了口清水,想了一陣才道:「我們的樣貌雖是由基因決定的,可科學界目前為止仍未能找出哪些基因負責塑造臉部形狀,只能肯定當中涉及多種因素。我的意思是,很難碰巧出現一個長得一模一樣的陌生人,怎麼說呢……打個比方好了,基因組就是撲克牌,人人都有一副,但人人排序都不一樣。牌疊是由父母那裏各抽一半混合而成,每一次的混合,都有不一樣的排序,而且又會受環境影響,使得排序變得更亂。所以,父母與子女之間縱使相像,也不會長得一模一樣,就算拿同卵雙胞胎的例子來說,也總有些許分別。擁有血緣關係的尚且如此,何況風馬牛不相及的陌生人?情況就似任由各人使自己的牌,然後其中兩個竟碰巧把牌疊洗得一模一樣,那個機率是不是很低呢?」
我點頭道:「確實是很低,但也要看看有多少人在洗牌。一個世紀之前,地球人口就只有十億,可如今已是七十個億了,就算撇除其他種族不論,那也是個天文數字。洗牌次數越多,洗出相同牌疊的機率就越高。換句話說,只要你給我足夠的人口基數,我就肯定能找到一個和你長得相似的人。」
蘇靈聽得眼睛也亮了,一下把眼鏡托得老高,熱烈地跟我討論下去。徐健在旁聽得懵懵懂懂,自覺無癮,便藉故走開,拿甜品去了。回來時,見我和蘇靈已在討論別的話題,而且談得興高采烈,笑聲不斷,多想加進來開心一下。他歪著脖子,見縫插針道:「蘇靈,老實說,你覺得我和阿放長得像嗎?我覺得是有那麼一點點像。」
蘇靈撩起耳邊鬢髮,笑道:「論樣貌,你們不像;論個性,你們更不像,真不知道你們是怎樣做成好兄弟的。」徐健疑道:「哦?我們個性怎麼不像了,你何以見得呀?」蘇靈指指我們桌上的殘羹剩菜道:「看你們的吃相就知啦。你看看你,碟子周圍都是骨頭碎肉蝦殼菜汁,弄得跟打仗似的,難看死了。吃個東西都亂七八糟,證明你為人處事無甚條理,只會橫衝直撞;明知要撞上牆壁,也不會先拿個頭盔帶一帶,非撞得臉青鼻腫不可。」
我被蘇靈的話逗得開懷大笑,連連點頭表示認同。徐健鼓起腮幫子,撅著嘴不敢反駁,等我們都笑完了,馬上道:「那麼阿放呢?輪到他了,來來來,你說說他吧,他是個怎樣的人。」
蘇靈眼波流轉,含羞看我一眼,見我一副無可無不可的態度,便挪開我的盤子,說道:「徐健你看,謝放吃過東西的盤子依然乾乾淨淨,刀叉筷子也擺得整整齊齊,骨頭渣宰都給他裹得密密實實,藏在盤子底下,你說他是不是太愛整潔,甚至有些潔癖呢?」接著眨了兩眼,把我上下打量一番,繼續道,「不過你看他一身打扮,灰灰的衛衣灰灰的褲,多麼隨便哦,來這種高級酒店也不想一下合適衣著,這表示他對心目中的小事情總是愛理不理。如果沒猜錯,他應該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是這樣穿的吧。」 這次輪到徐健拊掌而笑,輪到我沒法吭聲了。蘇靈不好意思道:「我也只是胡亂說說而已,你們別介意啊。」徐健笑道:「對極了,說得對極了,阿放就是這種人,從不花心思在衣著上,他這身衛衣球褲,家裏還藏著五套一模一樣的哩。」
ns 15.158.61.37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