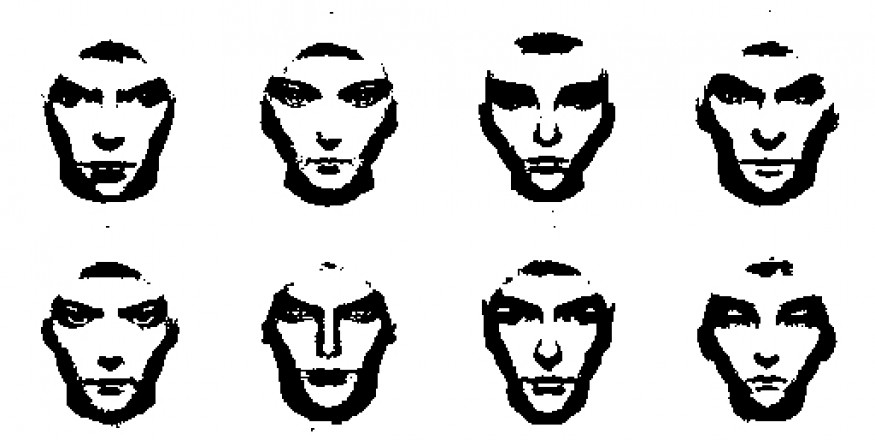我的警察朋友名叫「黑豬」,人如其名,又黑又胖,曾和我有過一段驚心動魄的冒險經歷,因而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前兩天委託過他追查婦科醫生與小伊生父的資料,現在打電話來,恐怕是得到了相關消息。
我和徐健走出房間,前往樓層大堂,較少人出入的地方,接聽這通電話。黑豬劈頭第一句就問,那份基因檢測報告是從哪裏來的。他指出報告中所顯示的醫務所,十年前已經倒閉,負責人從事非法代孕生意,於本城坐了幾年牢,更遭醫務委員會永久吊銷行醫執照。該醫生出獄後,自然混不下去,故移民泰國,繼續幹他的老本行,成為當地著名的地下婦科醫生。泰國政府執法較為寬鬆,城市人口也較為稠密,致使該名醫生的醫務所門庭若市,生意滾滾而來,數年之間,儼然成為東南亞非法代孕中心。
近一兩年,國際刑警盯上了這個人,積極與泰國警方聯絡,暗中蒐集證據,最終在幾個月前搗破了整個非法代孕集團,擒獲集團主腦,亦即那位婦科醫生,並排期於泰國當地法院受審。
國際刑警充公醫務所電腦,收集全部檔案,建立了一個資料庫,裏面備齊所有上門客人、代理孕母,以及捐精者的個人資料,從中發現了一名行蹤詭秘、動機存疑的顧客。那名男子在過往三年間,多次委託醫務所培植試管嬰兒,往往要求使用最高規格的設備,以及聘用經驗最為豐富的代孕母,所費金錢超出醫務所歷年所賺之總和。而最離奇的是,以他提供的精子所誕下的使館嬰兒,合共十六個,或男或女,全是同卵雙胞胎,命中率高達百分之百。
專家指出,人工受孕技術不能保證成功,負責醫生常把多於一個胚胎植入子宮,以增加成功機會,所以,代孕母或會生下異卵雙胞胎,這不是什麼希奇的事。可同卵雙胞胎則不然,他們是同一胚胎分裂為二,只能依靠運氣,不能人為促成,無論是否使用人工受孕技術,原理都是一樣,古今皆然。神秘男子可在短時間內成就如此之多的同卵雙胞胎,實乃醫學界的奇跡,這使得國際刑警不得不深入調查該名男子的身份與去向。
後來,他們發現該男子不只去過泰國尋求代孕生子,還經常出入尼泊爾、柬埔寨、寮國等多個代孕生意蓬勃的國家,期間不知找了多少名代母,生了多少個小孩。國際刑警與東南亞多國警方都以「瘋狂生小孩的隱形富豪」稱之。
那麼,該名男子的骨肉都到哪兒去了?答案可在各國的出入境紀錄輕易找到。那些小孩當中,除了有三對搬入我城居住外,其餘盡皆分佈於世界各大城市,如倫敦、巴黎、柏林、紐約、三藩市、東京、莫斯科、悉尼等等,足跡遍布南北半球;而且,孩子們的住處,全位於城中人口最密集、地段最昂貴的豪宅地區,大概過著衣食不愁的富裕生活。孩子之父如此安排,著實耐人尋味。
黑豬說了那麼多該名神秘男子的事,自然是要告訴我,該男子就是小伊灝兒的父親。十多年前的基因檢測報告可以證實這一點。為了追查此人下落,黑豬根據我城入境紀錄,查到一名單身外籍人士,連續三年為外地所生的嬰兒登記入境,每次申請都是雙胞胎,合共六名子女。一個單身漢生那麼多小孩,實在可疑之極,於是,黑豬夥同其他探員,前往其中一個登記住址,一探究竟。
那是一棟獨立海濱洋房,背山面海,庭院之外,就是白沙綿綿的海灘。按下門鈴後,一個外籍女傭從門縫探頭而出,黑豬當即出示警察證件,要求入內。屋裡五人聽聞警察前來,隨即集合一處,或坐或站,輪流介紹自己。一個保姆,一個乳母,一個護士,兩個傭人,組成黃金陣容,共同服侍一個未滿周歲的小嬰孩。目力所及,家中大部分東西都為嬰孩而設,成人專用物品少之又少。只見小嬰孩睡在乳母懷內,兩眼又開又合,嘴巴依依啞啞,撐起小手胡亂揮舞,實在可愛極了。
黑豬問保姆,洋房主人在哪兒。保姆說,老闆從來不到那裡去,她們五個受聘打理屋子,照料女嬰起居飲食,其他事情一概不知。黑豬又問,小女嬰是否還有一個雙生姊妹。保姆一聽,有點驚訝,猶豫許久才坦白說,女嬰確實有個雙生姐姐,早前被老闆送到歐洲去,要在那邊落地生根,不會回來了。
本想再從保姆口中挖出更多線索,但糾纏良久,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似乎保姆與其他人一樣,不過打工而已,所知有限。
最後,黑豬跟我說,有錢人就是任性,喜歡生多少就多少,完全沒有煩惱。多生了,擲一筆錢出去,不怕沒人照顧。一開始懷疑該男子是人口販子,現在看來真可笑,根本不可能嘛,花在一個小孩身上的錢,便夠買十個八個回來,這盤生意怎樣也不划算。做有錢人的兒女,一出世衣食無愁,一輩子生活豐足,可真是天之驕子。生那麼多小孩,動機確實可疑,但其實際所為,既不涉及人口販賣,也不是虐待兒童,甚至連疏忽照顧都沒有,從頭到尾,就不過生得多而已,我城法律還真是奈何不了。及後,黑豬把自己調查所得告知國際刑警,算是提供了一則額外資料,其餘的,他也沒興趣理了。
與黑豬結束通話後,我拋下徐健,獨自外出,散步透氣,整理思緒。所有謎團全繫於一人身上,那就是小伊灝兒的生父。這個人十多年前通過代孕母生下小伊灝兒一對雙生姊妹,何以十多年後又再生那麼多小孩?這三年間大灑金錢,大費周章,聘請專業團隊照顧嬰孩起居飲食,服侍之周到,如同帝王一般,到底用意為何?再者,小伊灝兒作為兄弟姊妹中年紀最大的一對,為何得不到其他家族成員的同等待遇,一直以來只有單親媽媽養育照顧?其中一個更是過著悲苦的日子,生活捉襟見肘,生存都成問題。她們的父親,直到現在才來找她們,是否另有計劃,欲把她們帶到其他國家定居?滿腦子的疑問,似乎只有姜氏父女才可解答,可他們由始至終不肯透露片言隻語,該怎麼辦?唯有在回城途中,再問問姜教授好了。
我在旅館附近繞了幾圈,正準備回去,忽見蘇靈正走在馬路對面,都是往旅館方向,便匆匆越過馬路,與她同行。
我道:「蘇靈……」她仿佛知我想説什麼,打斷道:「你不用問了,我不想講。」我當即把話吞回肚子裏,靜靜地陪她走。沒多久,她反而開口說:「謝謝你,幫忙勸爸爸。」我道:「其實我可以再幫上一點忙……」她又決絕道:「不用了,太遲了,我爸只怕要在牢獄中度過餘生,現在做什麼都沒用……」一時傷感,濕了眼眶。
我拍拍她肩膀道:「蘇靈,不如……」她又猜中我意思,直道:「不行的,我爸不會答應,他不可能做逃犯。他已經身敗名裂了,如果還做逃犯,怎樣對得起多年來的學生?」我道:「人最緊要對得起自己,哪管得了別人?我們可以在這裏找個僻靜的地方安置教授。」蘇靈搖頭道:「不行的,不行的,你要我爸躲起來,他也對不起自己呀。」
走至中途,我探問道:「蘇靈,坦白跟我說,你覺得教授所做的事有錯嗎?」蘇靈思考一會,然後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從你們的觀點看,他就是錯;從他的觀點看,他是對的。他要那兩個女孩子死,並不是為了他自己。你可以認為他做錯,但不可說他是為了自己而去做。」我對此難以接受,追問道:「我不明白,真的不明白,小伊灝兒犯了什麼過錯?她們沒有害過任何人,為什麼就值得死?」蘇靈一聲不吭,發足奔跑了十幾步,回頭跟我說:「對不起。」然後轉身跑回旅館去。
凌晨時分,我返回旅館,匆匆洗澡,匆匆躺下,輾轉反側,徹夜難眠。徐健老早呼呼大睡,一口涎液從半開合的嘴巴徐徐滑下,濡濕了衣襟。等到天明,一張開眼,便見他精神奕奕,靠在床頭大玩手機。聽見外面有人敲門,他才離開暖烘烘的被窩,去看來者何人。 「嗨,蘇靈,早安。」徐健輕鬆地對門外的人說。蘇靈卻緊張喊道:「爸爸不見了!」
ns 15.158.61.20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