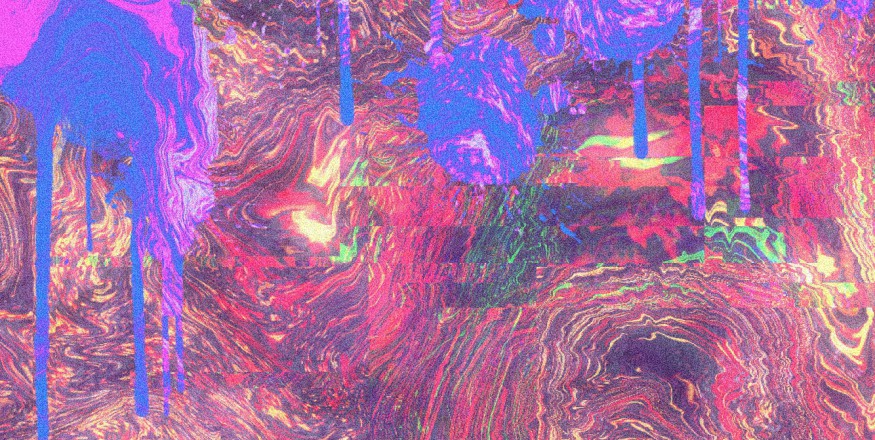*預警:養父女疼痛文學,不能接受者別看
海風悠悠吹過,冬天的日照時間不長,天空已經灰了。我拾起海螺的殼子,佯裝瀟灑地往裏面吹了口氣,沒有吹出聲音。無妨,事情總不如意,我也不是第一次了,上天剝奪了我成功的權利,卻給了我感傷的才能,我怨恨又氣憤,用力踢了踢沙,嗆得自己不斷揉臉。它給了我感傷的才能,卻沒有給予我發展的餘地,我無法盼望自己成為悲情故事裏的主角,只能當個矯情人,在海邊無人看到的地方獨自想像。
閉上眼睛後看到的是什麼,我的養父,他真是個美人。金色的髮絲用髮蠟搭在腦後,顴骨凹陷臉龐蒼白。噴濃厚的男香,飄出來的味道卻清新的,我想著或許老男人也是想要點年輕的體會,他的皺紋卻不這麼說。但是管他呢,養父的香味性感,皺紋也自然性感起來。
對爸爸起性幻想這種事情並沒有對我帶來太多的罪惡感,我和他沒有血緣關係,就算他是我親爹我也不會覺得有大問題。
「我認為我愛你。」這是我對養父說過最多的一句話,第一次說的時候是在十六歲的最後一個月,當時他的黑膠唱片在轉動,播著最為流行的搖滾樂,我的音樂品味說不定就是因此而被薰陶下來的。
他聽到後看了我一眼,把書包遞給了我,讓我快點上學去。
他的裝束總是標奇立異,藏藍色的襯衫、墨綠色的領帶,跟他的香水瓶吻合。養父沉默寡言,是女孩兒最憧憬的那種類型,安靜、成熟、好看,在他每次載我回校的時候都故意動作慢些,讓路過的女同學嫉妒幾分,他皺著眉頭催促我快點,我藉故親吻他的臉頰作道別。
海岸的風景使人靜心,可是沒有多少人喜歡來,他們喜歡去海灘。我喜歡在那邊待上好幾個小時,有一次天黑之後找不著路了,路燈在那邊如同螢火蟲的光,漂亮、但無用。養父的車頭燈救了我一命,他告訴我,海岸的浪濤太過磅礡,容易讓人想起人的渺小,有許多人不願接受現實,唯有去海灘走走,因為沙子比他們更細小。
「但是沙子多、到處都是,且存活於深海。」我答道,養父回我,是的。
車上的電台播著歌,我認得那首歌的旋律,說道:「父親,我認為我愛你。」
他沒有說話,我縮在座位上玩指甲,暗自腹誹:父親和那些只願去海灘的人一模一樣。
我在高中時期學會了抽菸,嗆辣的煙霧從嘴唇灌入內臟,一同灌入來的還有男同學的唾液,他是文學系的,他說非得要用一樣事物來比喻我的話,那肯定是菸草的霧。
「嗆、辣、碰不得、有成癮性——尤其對我來說。」他伏在我的肩膀上說,吐著煙,我當時只覺得噁心,文質彬彬的外表下埋藏的是充滿糞便的廢物,或許其他女孩兒都渴望著這種粘膩吧——他的樣子確實不錯,可比起養父還是差一大截。
胃口被日夜相對的人養大了的後果便是:直到十七歲,我都沒有談過一場戀愛。
我無法喜歡上同齡人,他們在我眼中被劃分到了「普通人」的區域。我在想或許是自己的問題也不定,我總是想得太多,用詞語堆砌出情緒,然後把它們吞食入腹。
那首歌每每響起,我都和養父說:「父親,我認為我愛你。」
十七歲的時候,我進行了我第一次的逃課。我騎著單車到了海岸,坐在岩石上抽菸,我從未見過這個時候的海岸——很早,剛好是潮汐退得最遠的時候。我心生想要下去一看的念頭,可是我怕被路人認為我想輕生,想著想著我就覺得在這個年紀、在這裏死去好像也是不錯的。十七歲,我終於是到了十七歲,脫離了稚嫩,又未至於老成,正正是可以昭彰地年少輕狂的年齡。
我哼著那首歌,想起養父的模樣。我嘗試把童年的傷疤挖開,尋找那首歌的含義,為何我會選擇這首歌,它又承載著什麼。模糊的記憶是自我保護的證明,我不願困住自己,只好鋌而走險,現在是、一直如是。有人的人生是一帆風順的,那肯定無聊至極。
這一天的最後是養父駕車來海岸,他一言不發地把我抓上了車,直到城市的燈照在大馬路上,他才開口問我:「為什麼逃課?」
「父親,我認為我愛你。」這是我的回答。
車裏的電台又響起了那首歌,養父淺金色的眉毛上揚了幾分皺紋,他的樣子很難過,他看著我,在審視我,審視他的女兒。我認為自己糟透了,我是一個不及格的女兒,我透過他的眼睛看見了他對自己的評語。可是父親,父親會包容子女的一切。
從什麼時候開始說的,他似乎在惱怒這幾年都在無視我看似無足輕重的話語。
我品嚐到嘴角的鹹味,淚水不受控地從眼眶中流出。
養父淺得幾近透明的髮絲垂了幾條下來,他最近沒有修剪鬢角,髮膠也維持了八個小時的工作,我發現養父的氣質越發頹靡,而這樣的他散發著腐爛的濃彩。他伸手,用抵了大半輩子筆桿的拇指擦掉我的眼淚。
濃彩從繭上抹到了我的臉上,烙印在我的生命裏,連同我不知所起的感情一同蓋過。我起身親吻了他,把我的青春、愛和那首歌埋葬在車的前座裏。
*
我總是愛得很昭彰。
說是少年氣也不為過,我的戀人們總是訝異我的表現方式——過於淋漓盡致,好像在追求生死盡頭,又好像隨時都會結束的暑假。科技發展快速,潮流也跟著更替,我全身上下都散發著追逐新穎的氣息,唯獨沒有改變的是歌品。
我和高中的時候相差無幾,可是經驗會在眸子裏刻下痕跡,像木桌凳子老舊的凹痕,除了難以清理外並無作用。
戀人們一個換一個,我認為他們不是太腳踏實地就是太幼稚。他們的共通點是——無法接受我愛人的方式。我為此其實感到極其可笑,他們的閱歷不足以理解他人,打著愛的旗號要人改變,說著這樣會讓生活變得美好,卻未曾想過我甚至從未愛過他們。
*
我到了22歲就已經離開了家,離開了這個養育了我這個大逆不道的女兒八年的父親。養父依然是我最愛的人,我記得他的教誨、他的衣品、他的味道、他嘴唇上的觸感。我認為我愛他,卻不認為我可以和他發展關係,他用他的性感把我塑造成一個精神不健全的女孩兒。
我沒有和他做過愛,或者說,我沒有跟任何男人做過愛,他們的性器官使我反胃——那太沒有格調了,誰會喜歡把滴著液體的肉塊含到嘴裏去?這樣想來,或許我的身體也不健全,我的慾望始於海、始於浪潮,卻和人情味差了八百米遠。
*
海岸依然是我最愛的地方。
我穿著毛呢外套,俗氣,和我的人一樣。我打開隨身聽,播起那時候的歌。
時代從黑膠唱片更替到磁帶播放機,現在到了電子隨身聽,實在變得快。過時的樂隊從過時變得再次「流行」,復古變成文藝指標。我頓時覺得自己高雅了起來,家裏依然留著以前的器械,新新舊舊疊在一起。我討厭斷捨離,情感是記憶的奴隸,我喜愛情感,自然也不喜愛拋棄記憶。
我希望成為養父那樣的人,父親,我依然認為我愛他,到至死不渝的地步。我離開了他,這不影響我對他的愛,十七歲的鳥兒總要飛走,我不能阻止凳子被刮花,但我能保持始終如一。
意猶未盡是路途的代表,它不會擁有終點。
ns 15.158.61.51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