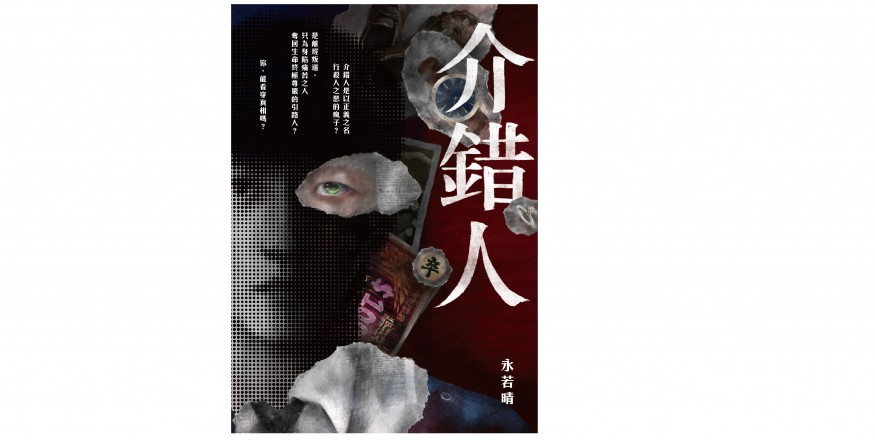二〇二四年,十月五日。1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S0Rzorm6TZ
殘陽把漫天雲彩染得通紅,美豔得使人屏息的卻是綻滿雪白床單的朵朵血花。俯臥在絨毛地氈上的男子身穿漆黑燕尾服,修長的褲管下露出赤裸的雙足,與脖子上的空虛構成另類的首尾呼應。夕陽的餘暉在維多利亞港上蕩漾,牽引着兩岸的天星小輪駛往彼此,絢麗的黃昏景色在二十二樓的套房內一覽無遺,但身首異處的他已經不可能再欣賞這良辰美景。
「死者林匯彥,二十五歲,中國籍男子,最先發現屍體的是酒店女職員。死者逾時仍未辦理退房手續,她以萬用匙卡打開房門才揭發這宗命案。林匯彥的身體就伏在這個位置,而頭顱則放在那邊的雲石窗台,手寫的遺書也是在窗台發現的。」綽號「大支」的警員向剛到埗的上司江浚澄簡述案情。
「有找到兇器嗎?」江浚澄戴上矽膠手套走往窗邊。
「林匯彥的右手握有一把約八吋長的木柄短刀,但看來不似是能斬首的武器。」
「八吋應該比你的還要長吧,大支。」江浚澄故意強調下屬的名字調侃道。
身為全港最年輕高級督察的他,一直相信各種價值都是透過比較才衍生的。長短是相對的,好壞是相對的,善惡也是相對的。他能夠平步青雲是因為同袍的表現不如他,而罪犯需要被懲罰是因為他們的行為偏離了社會的常規,所謂公平的天秤也不過是少數服從多數的遊戲。
江浚澄之前也有處理過斬首的兇案,但如此端正地擺放的頭顱卻是第一次看到。散發着腥鏽味的毛巾置於窗台中央,放在上面的頭顱不帶一絲陰森,高挺的鼻樑與地面形成直角,就像一件早被安排好展出的藝術品。它雙眼合上,嘴巴微張,似乎還有未盡的話語想要交代。
「這肯定是謀殺案吧?遺書應該也是偽造的。」湊過來的大支半蹲着打量屍體。
「不要這麼早下定論,先回去比對筆跡再說。我不相信兇手會這麼愚蠢,留下明顯矛盾的證據。」
江浚澄隱約感到一絲違和,卻說不出是哪兒不對勁。
「嘩,原來這小子是劍橋畢業的物理學博士,上個月發表的論文首次得獎,大好前途的他怎會自殺?」大支嘗試用找到的資料支持自己的想法。
「一定是有人妒忌他年輕有為,所以買兇殺人。」正在掃描指紋的牛金插話。
江浚澄沒有回應,而是重新把只有五句的遺書默唸一遍:「世間萬物在形成之際便開始崩壞,浩瀚似宇宙或渺小如我亦無一例外。生與死並不是相對的。若能以有限的生命換取無限的■■,那將會是我對愛因斯坦開的最大玩笑。」
關鍵的兩個字被血跡遮蔽實在太過掃興,他頓時覺得自己才是被開玩笑的那個人。
「喂,你們覺得生的反義詞是甚麼?」江浚澄問道。
「不就是死嗎?」大支及牛金齊聲反問。
「與生相對的當然也是生啊。」一把低沉的女聲從後方傳來。「大名鼎鼎的警隊哲學家也會有解答不了的問題嗎?」姍姍來遲的法醫談焯然沒有進一步解釋的打算。穿高跟鞋的她逕自走近屍體,江浚澄一行人識趣地自動讓開。
生存的反義詞大概是生活吧,江浚澄這樣理解談焯然的發言。至於死亡的反義詞,他暫時還沒有頭緒。
談焯然蹲下仔細觀察了屍體和四周,再與江浚澄交換眼色,後者默契地把俯臥的無頭屍翻身朝天。只見緋白斑駁的襯衣鈕扣解開,腹部有一道從左至右的橫切口,溢出的腸臟並沒有讓江浚澄反胃,反而勾起了他想一口吞掉謎團的慾望。
「腹部的傷口沒有傷及內臟,初步推斷那不是致命傷。死因應是斬首,但確實狀況需要進一步解剖檢驗。有了報告再通知你們。」談焯然站起身,幹練地說出觀察結果。
「好的。」江浚澄也答得乾脆。
「還有甚麼疑問嗎?」談焯然收回放在江浚澄臉上的目光,用公事公辦的語氣問道。
「沒有了。」江浚澄的全副心神已投入到思考案情之中。
天色漸暗,江浚澄俊俏的臉龐清楚映照在落地玻璃上,左額上的疤痕恰巧與剛冒出來的彎月重疊。他深深呼一口氣,決心要儘快把兇手緝拿歸案。
1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EH8OycHdDx
1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OXau4oZJ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