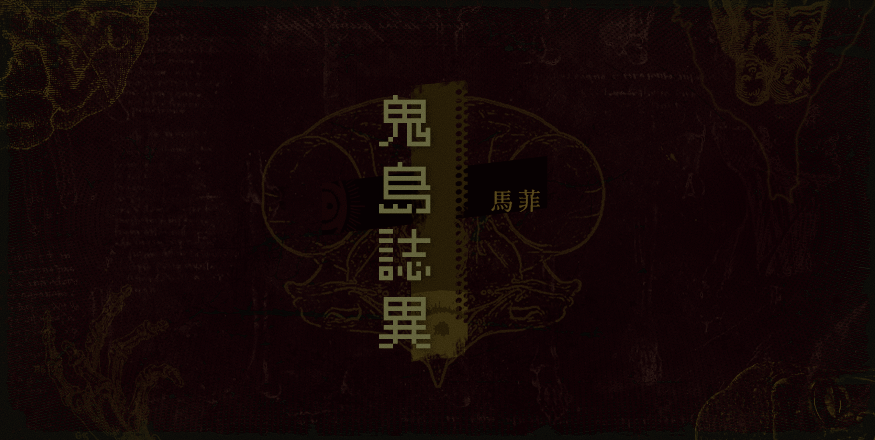嘉萱一大早就起床,梳洗過後就做早餐、為女兒小惠準備好上學用的衣服鞋襪,待一切都準備就緒,才喚醒她的心肝寶貝,只為讓她可多睡個十五分鐘。
嘉萱離婚之後就一直獨力撫養小惠,雖然有從前夫手上領些撫養費,但要一個人照顧只得八歲,在讀國小的小惠,仍是挺吃力的。不過就算多辛苦都好,嘉萱從沒有怨過半句,因為小惠就是她的一切。嘉萱曾經為了給小惠一個完整的家庭,而一直忍耐著她前夫的虐打,直至三年前在感到生命受威脅的情況下,才終於下定決心離婚。
嘉萱帶著小惠搬過幾個地方,最近就搬到了天天社區,這社區雖然離市中心有點遠,但租金相宜,環境舒適。嘉萱希望在這裡能有個新開始。
小惠吃過早餐,換好校服,與嘉萱牽著手出門。
「早啊!于老師。」住四樓的黃太進升降機時跟嘉萱打招呼。
「早啊!」嘉萱禮貌地回應著。
黃太之所以會稱嘉萱作于老師,因為嘉萱姓于,而且她告訴黃太自己在幼兒園上班,黃太順理成章以為她是老師。其實嘉萱只是當教保助理,主要是打雜,工作包括派茶點、哄午睡、洗屁屁等。不過就算如此,一般人都照樣把她稱作老師——于老師。
工作無分貴賤,只要她敬業樂業,做好本份,也配得上「老師」之名。
「隆隆——」嘉萱催動機車的油門,雖然聲音打雷般響,其實只是一台老舊的速克達,她每天都會駕著這嘈吵的速克達送女兒上學,然後上班。小惠就讀的國小跟嘉萱上班的幼兒園相距不過五分鐘車程,方便嘉萱每天管接管送。
嘉萱在國小門外跟小惠道別,叮嚀:「要乖乖聽老師話,專心上課啊!」
「我知道了。」小惠是個乖巧的小孩。
「好,那我們下午見。」嘉萱揮手道別。
「拜拜,媽媽。」小惠也一樣揮揮手,然後轉身走進校門。
「咦?」剛目送小惠走遠的嘉萱忽然回頭,然後環目四顧,她忽然有種怪怪的感覺,彷彿在隱藏的某處有人正在向他行注目禮。然而,任嘉萱搜索四周,還是沒有把那個人找出來。
「是我多心了嗎?」嘉萱如是想,卻又並非打從心底那麼想,因為她自問這方面的感覺很靈敏。
嘉萱看看手機上的時鐘,微一沉吟,還是決定回到機車上,扭動油門,絕塵而去。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絕對不容遲到。
回到幼兒園外,嘉萱先把機車停好,然後三步併兩步的跑進園內。往常嘉萱上班,進園後會第一時間到員工更衣室換衣服,然後將行囊放進貯物櫃。今天,嘉萱卻一反常態,躡手躡足的跑到雜物房,裡頭有一個小窗,裝有拉提式的百頁簾,只要提高少許,就可以從園內看到外面,從外面卻看不到園內。
嘉萱一直觀察外面,希望將監視她的人找出來,但她等了很久,對方仍沒有露出什麼把柄。
就在這時,一名工友剛巧走進雜物房來拿工具,看見嘉萱躡手躡足的在偷看外邊,奇奇怪怪似的,就問:「妳在幹嘛?」
嘉萱被他一問,老臉一紅的說:「我整個早上感覺有人在跟蹤我。」
「哈哈哈……」那工友忍不住笑說:「妳以為妳是天后巨星嗎?誰有空跟縱妳啊?」
嘉萱被這樣揶揄,立時漲紅了臉,遲疑半響,才尷尬地說:「我是怕我的前夫又跟到來了,他有對我和女兒行使暴力的前科。法院已頒過禁制令,不准他接近我們,但他還是經常偷偷的跟蹤我們。我已經為了避他搬過幾次,所以才會來到這裡……」嘉萱說罷眼眶一紅,眼淚欲滴未滴,她告訴自己必須堅強,不可有淚輕彈。
工友聽著動了惻隱之心,態度立改,關心的說:「要幫你報警嗎?讓警察處理比較好吧?」
嘉萱立即伸手示意不要,復說:「我就是想看清楚有否他的蹤影,不想胡亂報警,浪費警力。」
工友點頭表示明白,然後說:「有什麼需要幫忙的話,儘管告訴我。」
「好的,謝謝你。不過似乎是我多心了。」嘉萱說罷就匆匆告辭了。
幼兒園的學生陸續上學了,嘉萱身為教保助理必須站在校門前迎接學生,例如有家長駕車前來,不方便停泊太久,她就要負責開門把學生接下車等。
嘉萱站到校門外,堆起親切的笑容,跟每個上學的孩子揮手說早晨,而剛才那種被監視的感覺終於消失了,她不禁問自己:「難道是我多心?」
又一個忙碌的早上,嘉萱以前在幾間不同的幼兒園也做過相類的工作,總算駕輕就熟,辦得妥貼。
直至午餐過後,到了小孩們的午睡時間,大部份的小孩都乖乖自動上床,未幾就已進入夢鄉。只有三四個精力特別充沛的仍不願睡,嘉萱就要負責哄他們睡覺。
過了一會,其他的孩子都已經睡了,唯獨一個花名叫小豆的男生仍不肯睡,不單如此,而且還吵鬧著要玩。
嘉萱把他抱到小床上,想試著再哄他,哪知小豆把她推開,然後把被子踢到地上,枕頭扔到老遠,直說不依。
嘉萱試著勸他,說這會吵到其他同學,但小豆就是不依。嘉萱屢哄無果,發現附近幾個本已睡著的小孩開始輾轉反側,似乎是受小豆的叫囂所擾,好夢難酣。
嘉萱撿起了掉在地上的枕頭,暗忖若有小孩被吵醒,只怕又會吵鬧,這樣一來就會似潮水般擴散開去,沒完沒了。情況惡化下去的話,不單她自己沒得休息,若然驚動到其他老師,又是麻煩。
嘉萱越想越不對勁,越想就越是緊張,她捉著枕頭的手越捉越緊,心中一動,就想使硬,於是用頗惡的語氣說:「你快點給我睡覺,要不然我就不客氣了。」
小豆見嘉萱忽然板起黑臉,語氣嚴肅,立即躺到床上,不敢亂動,原來是受硬不受軟。嘉萱將枕頭還給小豆,還為他蓋好被,未幾小豆亦已睡著,嘉萱總算舒了口氣。
嘉萱一直忙到期盼已久的下班時間,隨即駕著他的速克達去接小惠。
「什麼?小惠被接走了?我不是說過由我親自接她嗎?」嘉萱用近乎咆哮的聲線跟負責放學接送的老師說。
「是的,因為對方是小惠的父親,所以……」老師試著解釋。
「父親?什麼父親?小惠沒有父親的,她父親是個壞人,是個賤人!」嘉萱聽到小惠父親把她接走,瘋了般。
「妳先別激動,我是想解釋妳聽,因為學校的接送流程是這樣。我也想了解一下,她爸爸來接是有什麼問題嗎?」老師問。
嘉萱忽然從暴怒中沉靜下來,沒有回答老師的問題,樣子變得冰一般冷酷。
老師嚇了一跳,過了幾秒才敢開口:「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
「不用了,我自己找。」嘉萱冷冷的說:「別再有下次。」也不等老師回應,就轉身跑回自己的速克達上,駕車離去。
嘉萱急不及待,一邊駕車就一邊致電小惠的爸。
「喂。」藍芽耳機傳來小惠爸爸的聲音。
「你他媽的將我女兒接到哪裡去了?」嘉萱一來就怒罵。
「妳說話放尊重點,我接女兒放學有什麼問題?妳忽然帶著她跑了我還沒問妳是怎麼回事。」小惠的爸說。
「我現在不想跟你吵。小惠現在在哪?我過去接她。」嘉萱說。
「什麼叫不想跟我吵?你到底在小惠面前說了我什麼壞話,為什麼她……」
嘉萱沒有聽畢對方的話,然後驚呼了一聲,速克達與旁邊的輕旅車發生擦撞,速克達迅速傾側,嘉萱連人帶車倒地,在馬路上如盤子般轉了好幾圈,最後眼前一黑,昏了過去。
醒來的時候,嘉萱感到混物疼痛,動彈不得。然而,動不了並不是因為受傷,而是手腳都被綁在一張反轉的方桌四隻卓腳上。
嘉萱才剛恢復意識,一時間搞不清楚的事實在有太多。
這是哪?為什麼我會被人綁著?在我昏迷期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傢伙終於醒來了。」說話的是個中年女子,就在嘉萱身處的房間之內。
嘉萱試著左顧右盼,礙於身體被綁,看到的畫面有限,但看得出來自己正身處於一間廢屋之中,屋內殘破不堪,一片凌亂。嘉萱也有看見說話的女子,覺得有點眼熟,但認不出是誰。
「終於等到今天了……」中年男子這樣一說,這綁架嘉萱的計劃看來已準備了一段時間。
另外一對老年夫婦則你一言我一語的說:「可惜抓不著她的女兒,要不就可以在這臭婆娘面前把她深愛的女兒殺掉,讓她也嚐嚐那滋味。」
「算了算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女孩無辜,我們殺她就好。」中年男子說。
老翁聽罷滿臉怒容的說:「她的女兒無辜?那我的乖孫就死有餘辜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中年男子說。
嘉萱聽得心寒,顫聲說:「你……你們是誰?到底……到底想怎樣?」
「你們有沒有聽到,這臭三八連我們是誰都忘了。」老婦氣憤的說。
「不認得我們,也總認得相中人吧?」中年男子拿著手機在嘉萱面前晃了晃,螢幕裡頭是個可愛的小女孩。
嘉萱認得螢幕裡頭的小女孩。
中年女子也掏出手機讓嘉萱看,這次是個小男孩,嘉萱認得。
老年夫婦拿出的是一張照片,是他倆跟一個小男孩的合照,嘉萱一看,閉上了眼,然後緩緩說:「你們殺了我也沒用啊!他們也不會死而復生的。」
話畢,換來老婦的一記耳光,以及一聲咒罵:「你這該死的賤人。」
「我是實話實說。」這時嘉萱換了一張臉,又是那張如冰一樣冷酷的臉。
中年女子沒似老婦般憤怒,反而面帶微笑的說:「放心,想殺妳的是他們,我從沒打算殺妳。我是個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人,妳把我兒子弄得一邊耳失聰,我也把妳一邊耳朵弄聾,很公平吧?」
中年女子說的是事實,她兒子小豪因為不聽當時就讀的幼兒園教保助理嘉萱的話,被她狠狠地搧了一記耳光,從此左邊耳朵聽不見聲音。不過,這個事實並沒有公布出來,校方為了卸責,竟然將當日的監視器片段銷毀,而且在事發後不久就關門大吉。訴訟方面,因為缺少了最重要的錄影片段,只得小豪的片面之詞……
「法庭已經判我無罪了,你要索償找校方去呀!把我抓起來也沒用的……」嘉萱說。
中年女子繼續保持微笑說:「這些妳跟我說也沒用,跟法官和警察說。我為人母親,當然是相信兒子的話。」說罷掏出一根黑底鑲金邊的鋼筆,把尖的一邊放進嘉萱的耳朵裡。
嘉萱滿臉驚詫,急出冷汗,顫聲說:「別……別亂來。」
「放鬆點,很快完事。」中年女子說罷大力一拍,整支鋼筆沒入嘉萱左耳耳孔,痛得她慘叫起來。
一直保持微笑的中年女子這刻反而收起了笑容,起身回首說:「輪到你們了。」
「鍾先生,你先請。」老婦說。
「不,你們不是已急不及待嗎?我在你們之後下手不遲,不等都等了兩年呢!」中年男子,亦即老婦口中的鍾先生說。
老婦對鍾先生微笑點頭,說:「謝謝,那我們不客氣了。」
老婦偕老翁來到嘉萱面前,由老婦說:「妳認得我們的孫子家俊吧?妳就因為他動來動去,就說他不乖,整個人壓在他身上要他別亂動,結果把他壓死了。」
「法醫報告出來說不是我直接壓死他的……」
嘉萱還未說完,老婦又再給她一記耳光,復說:「誰聽妳那麼多解釋,無論家俊做了什麼,都不該這樣整個人壓在他身上吧?」
法醫報告指是擠壓造成家俊的哮喘病發,真正死因是哮喘引致的呼吸困難。
然而,對於這對老夫婦來說,家俊死因為何並不重要,他們知道始作俑者就是嘉萱。
老婦從她已經用了二十年的老式皮包中拿出了兩柄刀,又彎又尖的廚刀,她望著這兩柄刀,滿意地說:「我特地跑到新光三越的刀具專賣店買的,售貨員說這是德國貨,最適合用來分筋斷骨。」說罷將其中一柄交到老翁手上。
「我也要妳嚐嚐不能動彈的滋味。」
老婦負責雙手,老翁則負責雙腳,把刀子鑽進關節,手肘、手腕、膝蓋、足踝等,然後把筋骨挫開、挑斷、刮破……
嘉萱發出像在屠場裡被宰的豬的慘叫聲,可憐的是她一直保持著清醒,劇烈的痛楚並沒有讓她昏迷過去,只是被蹂躪得有點虛弱,只聽她沒氣力的說:「你們逃不掉的,警察會抓到你們,通通被判死刑、死刑、死刑……」
「妳殺傷了三個小孩,不是還沒受到法律制裁嗎?」鍾先生說。
「對,法律制裁不了妳,就由我們親自制裁妳。」老婦說。
鍾先生伸手示意老婦別說話,因為接下來是他的時間,只聽他說:「我女兒麗麗不肯午睡,就給妳用枕頭悶死,結果妳棄保潛逃,這次沒什麼好解釋吧?」
「你……你以為我想這樣做的嗎?要不是你的女兒一直吵,我哪會要她閉嘴?她這樣可是會吵到其他小朋友的呀!」嘉萱忍著痛解釋。
「對,妳現在也有夠吵的,可以放心去死了。」鍾先生說。
「你……你別亂來,我也有個女兒,你們也是知道的,就當行行好心,不要讓她年紀輕輕就沒了媽媽,好嗎?」嘉萱終於第一次作出哀求。
「死到臨頭就別說冷笑話了。」鍾先生掏出一塊手帕和一樽水,先用水將手帕弄濕,然後拿到嘉萱的面前,又說:「只是剛巧有一塊濕毛巾掉到妳的臉上而已。」
嘉萱的口鼻被濕毛巾所遮蔽,空氣被水氣所阻隔,任嘉萱如何用力呼吸,也吸不進半點空氣,反而讓濕毛巾更加緊貼她的臉龐。
嘉萱不斷掙扎,直至身體變得跟毛巾同樣濕冷為止。
ns 15.158.61.48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