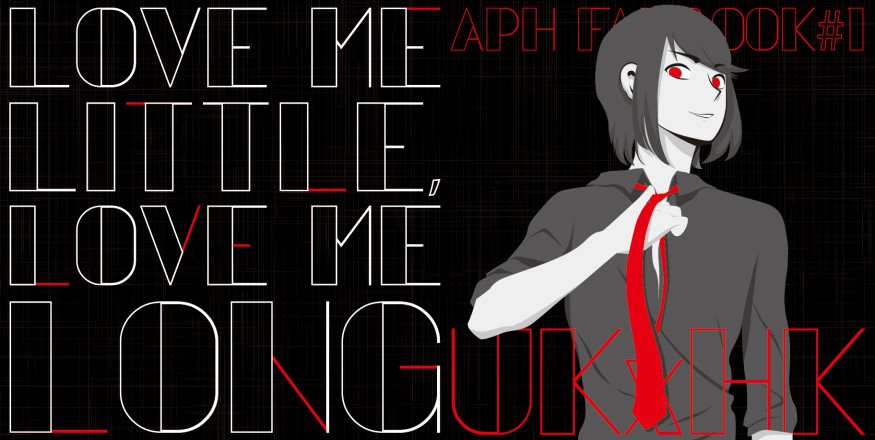王嘉龍提前了十分鐘到達酒吧門口。
卻發現約他的人早已站在那邊等了。
他穿着淡色的休閒襯衫,雙腿的線條貼着黑色的修身長褲,姿態隨意地半靠在路邊的欄杆上,一手插着褲袋,一手玩着電話,然後在王嘉龍即將靠近之際,略有所感地抬起了頭,看見了他。
兩眼相對,誰都沒說話。
Arthur先生抬高了下巴,向着酒吧的方向揚了揚,王嘉龍會意,腳下的步伐改變了方向,也跟着前方的英國人步入了酒吧之內。
⋯⋯他錯了,是餐廳之內才對。
窄小的店舖內裡卻是一應俱全,王嘉龍望着眼前左有廚房出餐點的吧枱位、右有一排供客人用餐的卡座,他思考着需不需要在眾多空位中選個卡位坐下,要坐嗎?要坐吧?然後開始懷疑人生。
幸而他想的所有都沒有發生,Arthur先生跟門口收款位置的店員談了幾句,店員就從櫃枱裡頭拿出了一條鑰匙,「啪」的一聲被放了在枱面上。Arthur先生用廣東話說了一句「唔該」,就順走了鑰匙。
他回頭看他,他順意地踏出了餐廳。
回到街上的兩人,這次到王嘉龍回頭看他,他倒是滿臉得意地用食指扣住了匙圈,任由有點老舊的鑰匙在空中瘋狂圈圈,顯然Arthur先生搖鑰匙搖得很是起勁。
他失笑。
Arthur先生帶着他往餐廳右邊的小巷裡拐,左邊的前端位置屹立着一道平常都能在巷子裡看見的金屬門,他剛要疑惑這是要做甚麼的時候,就見Arthur先生拿着他手上的鑰匙,伸向了那個掛着貓頭鷹木偶的門把。
咔嚓。
大門被打開。
映入眼簾的是,向內延伸下去的階梯。
……這還能做生意?
Arthur先生站在門旁側,側身面向了他,左手按壓在胸前,右手卻向着門口方向揮舞,帶着明顯的笑意,優雅地向他做了個「請」的姿勢。
被各種意料之外的狀況砸到有點呆的王嘉龍,只覺得好玩又好笑,這瞬間他不知道該臉紅還是該笑出來,可能兩者都有。但他一定已經被激起了好奇心,胸口湧出來的雀躍心情彷彿要按捺不住似的。
他一直以為他沒有這種,那麼鮮明的感情。
他可是被朋友笑稱,就算要他拿起刀殺人,也能木着臉執起摺櫈的人。
他記得他當時是以白眼兩枚作回應。
而現在的他卻像是個孩子般,期待着他可能會得到些甚麼。
用石磚築成的梯間,配上暗黃的微弱燈光,只有一人寬度的空間,這平靜而又有點老舊的感覺,王嘉龍並不討厭,可能還有點喜歡。
然後當他踏出了樓梯範圍後,他也終於明白為何Arthur先生會讓他先走。
那是視覺衝擊上的差別。
跟樓梯間不同,酒吧內採用現代感很強的設計,以黑色巨型磚瓦為主調的裝潢,金色的燈光十分巧妙地沿着吧枱底下、牆角邊、門框後側等地方包圍着整間酒吧,明亮但不刺眼,襯托着黑磚裡映出來的反光,一切都配合得如此高貴、且神秘。但這些都不是讓王嘉龍讚嘆的原因。
大量的鳥籠、冷金屬交錯的飾物佈滿了酒吧的任何一隅角落,雙目觸及之處總能看到打開着的空籠子,有掛着的,有堆着的,也有直接這樣放着的。就算是不適合放鐵籠的位置,也會有些幼長鐵枝凌亂地填滿那個空間。看着是頹然的意境,心裡釀出來的卻是驚艷。
現代,懷舊。
兩個本應是對立的詞語,是如此融洽地混和在一起。
Arthur先生從後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後推着王嘉龍向前走。而王嘉龍也放鬆着身體,任由背後的力度帶他上座。
竟然連座椅都是藤椅外觀的。
王嘉龍坐在為數不多的座位上,耳聽着酒吧內環迴的古典音樂,坐了在他對面的Arthur先生摸着鼻子,用着愉快的語調問他:「看你的反應我猜這個地方應該選得不錯?」
他望向他,彎起的嘴角柔和了臉上的輪廓,露出了這個夜晚裡首個稱得上是温柔的神色,嘴邊卻是游刃有餘地回答道:「那還要看看你選的酒才能定奪呢。」
Arthur先生挑起了眉,臉部肌肉拉起了接受挑戰的笑容,站起身向吧枱走去。
這家店沒有侍應生,客人以外的唯一活人就只有在吧枱後的調酒師。不過這間酒吧也沒有很大,不足十桌的座位也只有三四桌坐了客人。
Arthur先生在調酒師耳邊說了些甚麼,王嘉龍沒聽到、亦沒有用心去聽,只是靜靜地窩在藤椅裡,托着腮地看着Arthur先生談話的背影。
不久後Arthur先生就回了座位,王嘉龍看着兩手空空的他,雖然他知道要客人自己送餐是不怎樣可能的事,但他還是很好奇怎麼樣的酒、會以怎麼樣的方式送到他手上。
Arthur先生迎上了他探究的目光,再次得意地笑了笑,「等會你就知道的了。」於是他也不心急,慢慢地看店的四周、看調着酒的調酒師、看他。
Arthur先生似乎對他的視線感到不好意思,也許是還未以酒精壯膽的關係,他看起來並不像他們第一次相遇那樣般開放,要知道當初王嘉龍才是被搭訕的那個。於是他們倆開始有一句沒一句地談起話來。也不算尷尬,因為兩人似乎都樂於觀察對方的反應。
調酒也不需要他等多久,暗地裡一直觀察着吧枱那邊的王嘉龍,注意到調酒師將兩杯酒放在枱面上的某個位置,然後在旁邊按了甚麼機關似的,托着酒杯的平板物體徐徐向上升,原來是有四條鋼線分別吊在托板的四角,然後在天板上眾多鐵枝裝飾中,沿着正確的軌道前進,來到了他們桌的上方,再而穩定地降落。
見他專心盯着送餐過程的Arthur先生,十分體貼地沒有發話打斷他,他看酒,他看他。
王嘉龍望着枱面上的兩杯酒,那是透明的酒,兩杯透明的雞尾酒。
Arthur先生抬手,示意他請便,他就拿起了接近自己的那杯,Arthur先生也拿走了另一杯,那塊托板隨即向上爬升,沿路回到了調酒師的身邊。
王嘉龍飲了一口,滑過味蕾的居然是Whiskey Sour的味道。
Whiskey Sour是一種以威士忌為基酒,再配以檸檬汁及糖漿組成的酒。這種酒的份量拿捏十分重要,酸味跟甜味互相制衡,不能一份多了而另一份少了,而兩者的總量也不能佔太大份,因為兩者份量愈多,酒就愈軟。
他猜這杯的基酒是波本,他嚐到了波本的香甜。
細細品嚐着這杯不是威士忌琥珀色、而是透明的Whiskey Sour,他俯身向前,雙肘壓在枱面上,雙手交疊在高腳杯底,好奇地打量對面那個人手上的那杯。
他會意,也向前拉近了雙方的距離,向他舉了杯,答:「The Gone Gimlet。」
Gone Gimlet,是由再蒸餾的乳酪琴酒、檸檬皮、零陵香豆、忌廉和自家特製青檸汁等等混合而成的。首當其衝的應是酸酸的乳酪味,入口後才會嚐到琴酒和檸檬的香味,留下清新醒神的餘韻。好吧,他只是以以往的經驗來點評的,畢竟他也不知道對方嘴邊的那杯透明的酒是否有些不同。
酒精的作用開始溜入王嘉龍的大腦,不至於醉,但卻增添了讓他想做些甚麼的衝動。
例如就嚐嚐那個他很在意的味道。
於是他蹲高了身子,雙眼直視着對方的綠色眼眸,嘴唇緩緩靠近對方的酒杯,貼近了杯沿,抿了一口。
Arthur先生愣了一愣,卻任由王嘉龍盯着他、靠近他、再而親吻他的酒杯。
也許他不介意他跟他的酒杯有親密接觸,但或許他介意那是他的酒杯,而不是他。
他喝的份量只有一丁點,直至王嘉龍喝夠了也只是一息間的時間,就着他想要退回去的瞬間,Arthur先生快速地飲了一口酒,空着的手繞過他的身側托住他後退的後頸,向着自己拉回來,然後——
吻了上去。
ns 15.158.61.41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