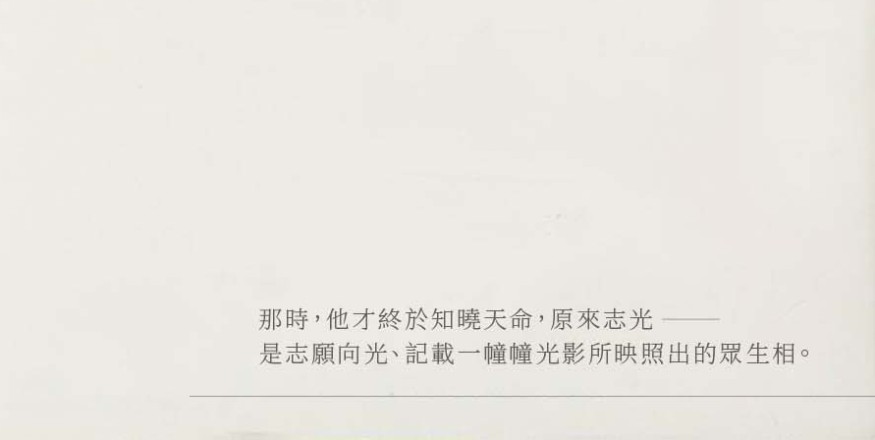「琬華……小姐。」高志光猶豫了一會兒,還是加上了個禮貌的稱呼。又花了點時間組織語言,隨後這些疑問就像連珠炮似的拋了出來:「昨晚……是妳在對我說話嗎?剛剛那個聲音不是妳嗎?如果不是,那是誰?為什麼妳,不、妳們……可以沒有透過任何通訊器具就對我說話?或我昨晚其實見過妳,但因為我喝醉記不清,所以誤會了?」
琬華早已料到他會有這些疑問,人很難輕信原來不信的事情,尤其是高志光這樣死腦筋的人。她是很明白高志光的,不能解答他的問題、不讓他親眼見到那些事,不說服他,他便不會接受這些「存在」——這對他們未來的合作不是好事。
「昨晚是我。」她率先肯定了這個提問,「我們沒有見過,那不是誤會。」琬華瞥了眼神龕上的姑娘神像,說道:「到方便說話的地方吧,在這兒說話,會打擾她的。」
志光還有疑問要待琬華解釋,再者,他對這姑娘廟也沒有非留下不可的理由,對此便也就沒有太多意見。
他隨著琬華來到離姑娘廟不遠的地方,那是在大街上的燈籠店,他抬頭望向那塊有別於其他招牌的木製牌匾,上頭寫著「聚暉坊」三個大字,這讓他心中有股異樣的感覺,彷彿真有什麼被凝聚在這裡。
門廊上掛著大大小小、樣式不一的燈籠,自他和琬華從姑娘廟出來以後,因為把靜心燈落在廟中,耳畔的嗚咽聲又恢復如常,而此刻他還另外聽見一種聲音,那是自燈籠裡傳來的,和平日裡聽見的細碎耳語同樣的呢喃。
「這些燈……」
「等會兒再說。」琬華知道帶他來這裡,他肯定會有更多的疑問,不過要和他解釋的事多了去,不差這一星半點。
踏進店裡,就像走進另一個時空,木造的房室和方正的格局,各式燈籠或掛在樑上、或整齊地排列在地上,文雅古典的氣息充斥其中,唯有一張顯得格格不入的辦公桌放在盡頭,桌上還散放著幾張設計圖紙。
「坐。」琬華要志光坐在辦公桌另一頭的客座,把圖紙收進抽屜,倒了兩杯茶,並將其中一杯遞給他,方才落座。「我知道你有很多疑問,不過,在回答之前,我想先問你一個問題。」
「你對於那些聲音是怎麼想的?腦神經衰弱?幻聽?」琬華啜了口茶,好整以暇的等待他的答案,她沒有舉列關於靈異的選項,是因為她知道,眼前這個人無論如何都不會選。
「本來覺得是幻聽,或某種醫學上還無法解釋的雜音。」高志光努力按下那已經快要衝破胸腔的好奇心,卻還是沒忍住,急切地問道:「但妳的確透過什麼來跟我說話,對吧?」
「是我在問你問題。」琬華噙著笑,帶有幾分審視的意味,「我明白了。」琬華看著志光,想起師父告訴她的那句話:「那個人腦筋是死的,但妳會喜歡他的眼睛。」那是一雙純正無邪的眼睛,和他這副笨拙的模樣不符,她說不上喜不喜歡,不過,他的話的確可以相信。
這抹笑讓高志光心中一凜,難道他誤入賊窟?但除了他這條命,也沒有什麼值得索要的。或者,其實這一切都是為了整他?但會是誰要這麼作弄他?又到底為了什麼要這樣做?
「現在換我回答你了,再不回答,你怕是要憋死了。」琬華再啜了口茶,才緩緩說道:「和你說話的人是我,至於剛剛那個聲音……說來話長,總之不是什麼好東西,以後提防點就是。」她顯然沒有打算在這個話題上多作著墨,幾句話便草草帶過,接著道:「你不相信鬼神。」從高志光在姑娘廟的反應看來,他大抵是不信的,只不過是為了配合自己,以求得一個答案罷了。
「不過,不論你信不信,你聽見的就是鬼語,或更精確地說,是眾生之念的其中一支。這不是病,自然沒有醫學可以解釋的道理。」
「眾生之念?」志光沒有想到,林琬華非但沒有立刻解決他的困惑,反而說出更多讓他難以理解的詞彙,這些和他有什麼關係?
「眾生之念即天上地下一切生靈之音,無論苦樂憂喜皆有所聞。而能聽見這些的法門,便是天耳通。」琬華在紙上寫下天耳通三字,又說:「你天生便有這項神通,卻未修煉,所以你尚且只聽得見三惡道,且祂們說話只能以那樣的雜音顯現,不曾清晰。」
「你又不信鬼神,便更加不能與其相通。人的心念很複雜,有時要比種種神通要強上許多,有時卻又什麼都辦不到。」話至此,琬華又笑了,這回的笑容中帶有一點苦澀。她接著道:「為什麼你會在那個時間點聽見我,這個問題我卻無法回答你,因為我也不曉得。或許是緣分到了吧,你我有同一條道要走。」
志光看著她的笑,卻不解其意,只知道自己若真如她所說身懷神通,似乎就必然要走往另一個未曾知曉的世界去,無論他願不願意。
他盯著眼前逐漸轉涼的茶水,想起在諮商所和葉岑的對話,轉涼的茶,真的還是原先那杯茶嗎?冷或熱是一種性質而不影響本質嗎?或者茶水是會因此改變的?此刻的他,還會依著自己的好奇心,義無反顧地將它喝下嗎?饒是那樣的志光,也開始搖擺不定了。
「聽過走馬燈嗎?人將死前,一生中重要的記憶會一幀幀從眼前掠過。」琬華歛起笑,又恢復到原本那副清冷的模樣,「車馳馬驟,團團不休,燭滅則頓止矣。」她起身從邊上歸置整齊的燈籠裡,隨意拾起一盞,「那些『念』,會被收在裡頭,所以你從這兒也能聽到聲音。」
她手上的那一盞,是一隻冤死的魂,正聲聲哀嘆著天道不公。
「那……他在說什麼?」志光只看見一盞普通的燈籠,那些哀嘆,在他耳裡也只是一道沉悶的嗚咽。
「我聽不見。」琬華輕聲應道,她將燈放下,從辦公桌的抽屜裡抽出一本線裝筆記,紙頁有些泛黃,但看得出悉心保存的痕跡,上頭的字跡雖算不上娟秀整齊,仍是可以辨識字句。她將筆記交給志光,「這個你拿去。剛才說的那些,若有不懂得的,把它讀過一遍便能懂了。」
「妳聽不見嗎?」志光拿著筆記,卻沒有立刻翻閱,他更關注琬華的回應,原來她是聽不見那些聲音的。
「是,我聽不見。我只看得見祂們,卻無法知道祂們究竟發生了什麼,又想要什麼。」她沒有再回應志光,反而解釋起了筆記的來由:「這是那位留下的東西,修煉的東西我不擅於解釋,看她的筆記對你會有幫助。」
她一向是實踐主義者,比起解釋,起身而行要簡單得多。雖然面對這樣一張白紙,她不得不多說幾句,但方才那些也就是極限了。「之所以要你到姑娘廟來,便是要讓那位看看你,確認我沒有找錯人。」
「小廟無廟名,但裡頭的姑娘卻有名字,她叫祝雨。」她將餘下的茶水一飲而盡,「我師父,你師祖。」
「哦。」志光先是訥訥地應了聲,後才反應過來:「等等,師祖?」那不就意味著眼前這個人是自己的師父?他怎麼就在這越聽越不明白的對話之下,白白多了一個師父?
「我不是說了嗎?你和我有同一條道要走。」琬華將祝雨說過的話複述一遍,「善見聞者,以身行道,方可攝眾生苦。」
「我不明白。」
「我知道。」琬華有那麼一瞬感到疲累,若非她有不得不做的事,而他又在其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真想就這麼算了。「忍著你的好奇,跟我走一遭便懂了。」如果他不是笨蛋的話,會懂的。
希望他不是。
ns 15.158.61.48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