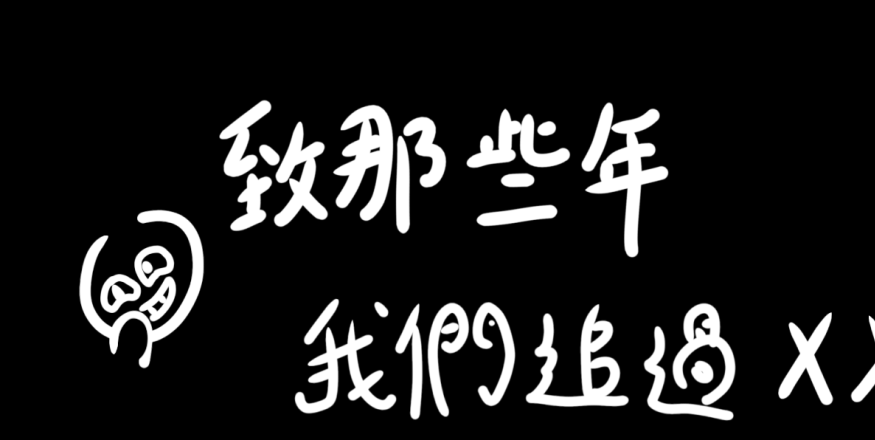一、
對我來說,芥川龍之介是眾多文人之中、少數真正懷有憂患意識的。他清楚自己這個生在動盪時刻的知識份子要對該時代負責的義務(noblesse oblige)。作品並不拘泥在一類形式與風格上,所寫的歷史題材小說竟能契合住屬於現代性的心理分析,在冷澈的理智之間闡述出生命最幽微奧妙之處,這只有將藝術融於生活的詩人才做得到的——徹底地生活於藝術中——也就如此,也為了藝術在受苦,他的心中才滿懷「恍惚的不安」。
他之神經衰弱症折磨他近半輩子,他曾說道:「最可怕的是停滯。不,在藝術之境裡是沒有停滯的。不進步就必然是退步。當藝術家退步時,常開始一種自動作品,那就是意味著,永遠寫著同樣的作品。」
1927年7月24日,他仰藥自殺,享年三十五歲。
不知曾幾何時,我對這名病懨懨的作家有種親切感,在我踽步獨行在創作路上,總有那麼一名陰鬱的、不領情的、雙魚座的遊魂驅策著,那是不是私自解讀他的我,所要擔下的負罪感呢?
149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lp3tbrnyv2
149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3makrVjcxm
二、
下一名要被我記在《諛墓記》的,卻是在7月24號出生的作家。谷崎潤一郎的美學是異於芥川的,他認為小說就該有「故事」的樣貌。並非詩,而是小說本身須有結構美。
「耽美」一詞正是如他的小說:沉溺於美、甚至罔顧道德,是能讓人觸動的無瑕之美。(如今已是完全不同的用法。)而對我來說,美正體現在他描寫的女人,雖然不顧倫理這點常常被人指摘為「惡魔」,他筆下的奇情畸戀卻是如此迷人——例如《春琴抄》中,對盲眼人的戀慕、還是《鍵》記載的兩性角力,都講述著就因為具有情慾(有創造力)而一個個與美媾和,對追求這種境界的人來說,恐怕稱作「天堂」也不為過。
至於谷崎潤一郎的死,我就沒記得如此清楚了,只記得墓石上有「空」、「寂」二字,可是他作品中的角色卻是最不知這二字涵義的痴人,也許是谷崎他要我去記得作品,而不是一無所有的墓吧。
149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qxo85aCgWS
149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BTAGfRuH2s
三、
說到三島由紀夫,常讓人想起的正是他的死吧。他最後選擇切腹自殺一直以來都是歷史之謎(或該說過了五十年,仍是日本政壇的禁語)
當然,在《諛墓記》中,並不是要探討這些紛紛擾擾,對我來說,那就像是一齣表演——令觀者齟齬,而演繹者如願以償。一如《金閣寺》,「不被人所理解」是主角自豪之處。
「殺孔雀,是人類所企圖的一切犯罪中最自然的意圖。那不是撕裂,而是把美與毀滅肉感地結合。 」《孔雀》講述的正是為了美,什麼都可以犧牲。
「讓藝術實現,即使世界得滅亡」(Fiat ars, pereat mundus),毋寧是右派的口號,三島由紀夫用著作完美地實現「為藝術而藝術」。現今人們能為自己表演,自己變得疏離陌生,陌生到可以經歷自身的毀滅,甚至將其化約為一體的美感享樂。149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8yRTnskpyy
四、149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o3rFYiOEd5
這些文學的巨擘們——如今也成了一具具沒有反應、不會思考的枯骨,一部部作品也都成了碑上的墓誌銘。留下來的我,得要掘開他們的著述、重新在時間軸上定義他們。即便如此,以我的哲學來思考這世間的一切,仍然有想不透的事情。
因為他們死了,所以如斯不幸?還是得要活著去阿諛奉承他們留下的事物的我才不幸?這些文物總體的歷史,到底有多不幸?
「始知——最大的悲觀竟等於最大的樂觀。」
寫到這裡,忽有《巖頭之感》。那湍急的憂慮傾倒在思緒的荒涼心境呵。
ns 15.158.61.45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