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 Fretes,飛機還有二十分鐘會抵達目的地。」
寧靜的頭等艙裡,一個綁著高馬尾的金髮女性,手裡拿著資料夾,鼻梁上掛著十分專業的金框眼鏡,正站在一位男性身後。那位男性穿著完全不像是在機上該穿的開襟睡衣,頭上戴著英國阿媽常戴的那種法蘭呢絨睡帽,好像還正在敷臉。
男人背對著他的祕書,透過機窗看著窗外湛藍的天空,沒有轉過頭來。
「是嗎?沒想到南國沒有想像中遠嘛,辛苦妳了,妳可以去休息一下了。」
金髮美人看著男人寬闊的背影,張口又說:「另外,剛才接到資訊安全部的匯報,就在兩個半小時前,有人駭進了我們的中央電腦,安全部門現在正在緊急處理中。」
男人的背影動了一下。「喔?竟然有本事駭進Centre Control,有查到來源嗎?」
「沒有。資訊安全部門的經理說,從IP來看駭客似乎來自臺灣,但是對方很狡猾,在被發現的瞬間就主動切斷所有追蹤管道,對方也有自己獨立ISP環境的樣子,沒有辦法利用封包流向追蹤。不過損失的資料不多,對方只拿了您的行程表。」
「臺灣嗎?真有趣……沒想到這個南國的小島還有這麼有趣的人。」
金髮美人猶豫了半晌,又說:「經理說對方可能來頭不小,他在安全部門待了這麼多年,還是第一次遇到這種狠角色。Mr. Fretes,您覺得要不要……」
男人仍舊沒有回過身來,只是打了個小小的呵欠。
「不要緊的,就讓資訊安全部門去處理吧,頂多就釋出假消息,就說我們的飛機因為亂流在青康藏高原上迫降好了。」
他又歎口氣:「而且親愛的Lady Lan,我有說過我現在人在度假中,跟工作有關的事情都不要打擾我。何況我現在根本沒有心情去想那些凡塵俗事。」
Lady Lan挑了一下眉毛,因為她家老闆剛剛用字正腔圓的中文跟她說話。據她有限的所知,她們家的執行長在與某位神祕的東方女性通信後就愛上了中文,還在辦公室裡推行中文成語運動。害她被逼得也去學了點這種詰曲聱牙的四大古文明語。
「那麼,我就回報安全部說這個事件暫時懸置了。」金髮祕書說。
「嗯,隨便怎樣都好啦,妳決定就行。」
男人說著,用趕蒼蠅的手勢往後揮了揮,旋及把注意力放回他法蘭呢絨帽下的頭髮。
「GOD,希望我的髮型在降落之前可以固定,Lady Lan,妳那邊還有髮膠嗎?」
金髮女子長長歎了口氣,知道現在要她的老闆聽進任何匯報都是不可能的了。轉身離開機艙時,她還聽到男人宛如在愛侶耳邊的細語。
「就快要見面了,親愛的愛蜜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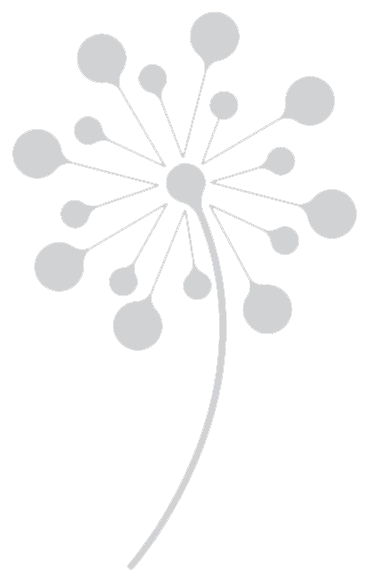
「知之,這樣絕對、絕對、絕對、絕對會被拆穿的!」
桃園機場第一航廈大廳,響起了一聲這樣的悲鳴。
知之的全名是李知之,今年號稱二十五歲。這名字是他爺爺取的,李知之和那對聽說都是大學教授的父母從很早就已經斷絕關係了。
爺爺取這名字的緣由據說是來自《論語.為政》:「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但知之對這個名字非常不滿,因為大學生聽到助教的名字後總是會問他:「吱吱耶,是綠吱吱還是藍吱吱?」
知之現在掛名的職業是S大考古人類學系助理研究員。知之做這個工作至今已經有五年了,他還記得五年前,說到考古人類學系,大多數人的反應都是一臉茫然,不知道這個系是在幹什麼的。
但是這情況在幾年前有了變化,知之工作的大學裡有些女學生,一聽到他念考古相關科系,就會一臉興奮地問他:「考古學系?請問你們會去盜墓嗎?」而他們以前辦什麼研討會演講的都乏人問津,現在關心的人也莫名多了起來。上次知之還在系館門口看到有人貼了紙條:「我們不是盜墓系,這裡沒有悶油瓶。」諸如此類意義不明的標語。
不過考古也好盜墓也好,知之都沒有太大興趣,他本來選這個系是因為他被S大分在文學院,而文學院是男性比較少的系所。他厭惡與男人共事,但比起男人他更討厭文學,所以才選了考古人類學系。
之所以會混在大學裡面當助理,也是因為大學生給人的印象比較清純,警察要進來抓人還得三思而行。這可以方便知之做很多事情。
包括安安穩穩地待在這個看似平凡的家裡。
知之坐在第一航廈接機區的沙發上,發現整個航廈的目光頻頻往這裡聚集。
不過原因倒不是他,而是現在站在他身邊,滿臉清淚外加焦慮不安的,他的室友,顧善存小朋友。
雖然知之對室友皮囊之下裝的內容物抱持懷疑,但對於善存這具皮囊,知之必須承認他真的沒有什麼好挑剔的。
眼前的美少年穿著一襲水藍色的洋裝,頭上戴著黑色柔順的假髮,還煞有其事地編成了雙馬尾,結上同樣水藍色的蝴蝶結,布製馬甲優美地禁錮住少年纖細的腰肢,給人一種莫名禁欲的美感。而少年腳上的白色蕾絲半筒襪雖然稍嫌粗壯了點,在裙襬若隱若現遮掩下絲毫不構成威脅,手上抱的那隻巨大泰迪熊更可愛得足以讓人忽略一切破綻。
知之仔細地檢視自己精心為室友設計一晚的裝扮,滿意地再次點了點頭。
「Perfect.」知之推了眼鏡。
「Perfect你個頭!這樣絕對、百分之兩百會被拆穿的!吱吱,我錯看你了,沒想到你竟然是這麼重色輕友的人!嗚嗚,完蛋了,這次真的會被閹掉了,天上的爸、天上的媽,我對不起你們,你的兒子不能為我們顧家傳宗接代了……」
善存抱著熊寶寶跪倒在地上哭泣,好像那是他在世上僅存的依靠。為了讓善存的臉部線條更像個十七歲的女孩子,知之還花了一晚上的時間替善存上眼線、裝假睫毛。
只見路過的旅客有好幾個都停下腳步,用遲疑但帶著讚賞的目光看著地上的善存。
『好可愛……』
『哪來的女孩啊?外國人?臺灣人?』
『欸欸,好像在哭呢,是不是迷路了呢……?』
知之毫不留情地一腳踩在善存那張讓無數少女尖叫的臉蛋上。「吵死了,是你要本大神拯救你的,這是現在能夠救你的唯一方法。你照著我的話做就對了,還是你對我精心設計的詭計有意見?」
「但是這樣超明顯的啊!我是男的耶!是如花似玉的十七歲高中男生耶!」
「『如花似玉』不該用在形容雄性的名詞上,你應該練習的是中文信才對。我說不會被識破就不會被識破,男人都是視覺的動物。」知之以一種旁觀者的語氣說。
「但要是他偷襲我胸部怎麼辦?」善存含淚抱著熊寶寶問。
「以你五年來和他通信的印象,你覺得對方是會做那種事的人?」
「嗯。」善存含淚頷首。
「你可以說你貧乳。」知之扶了下額。
「但是聲音呢?我的聲音一聽就破功了啊!」善存抱緊熊寶寶的肚子。
「我記得你有時候也會在團裡唱女性Vocal。」
「但那是假音耶!你要我一直用假音跟他說話嗎?」
「反正只是吃個飯、聊個天而已。你的聲帶和你的雞雞,選一個。」知之無情地說。
「……」
有時候善存會覺得,知之在搬進那間屋子前,一定是暴力討債集團出身的。否則怎麼會每次被知之三言兩語外加冷冷地一瞪,善存就覺得他要被連皮扒光了。
「對、對了,念哥呢?他不是說他也要來?」
善存看著航班看板,看著知之昨晚查到的班機號碼從「On Time」轉變成「Arrival」,善存覺得擠在馬甲裡的心臟從胸膛提到了嗓子眼,都快不能呼吸了。
「不知道。多半是工作又耽擱了吧。」知之淡淡地說:「這很正常。」
這時候知之握在掌心的手機叮叮噹噹地響了起來,善存驚弓之鳥般抖了下。知之把手機面板拿起來正對著自己,看了半秒鐘,按了掛斷鍵,又把手機放下來。
「呃,剛剛是念哥打來的吧……?」
善存端詳著知之的表情,不確定地問:「你不接嗎知之?」
知之沒說話,手機很快地又響了一次,知之如法炮製,把手機拿起來看半秒按掉又放下。手機再響,知之再按掉,再放下。每次都間隔半秒鐘,比機械還要準確,動作熟練到好像已經做過同樣的事情很多次那樣。
善存聽見手機大約響了第十四次,這回知之把手機拿起來,總算按了接通鍵,把手機放到耳邊,但是沒有出聲。
『小知嗎?』
對方竟然還用無比溫柔的聲音問,好像是第一次打電話來那樣。善存暗忖要是有人膽敢掛他十三次電話,他一定在對方接起電話的瞬間先問候他老媽的老媽的老媽。
能夠這樣忍受這種事情的這世上也不會有第二個人。善存合理推斷電話那頭的一定是他那好脾氣的表哥,現職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法醫的徐念長徐同鞋。
「你打錯電話了。」知之說。
『小知,抱歉。樹林這邊有一起姦殺案件,他們人手不夠,臨時叫我過去支援。』電話那頭說。
「我說你打錯電話了,這裡沒有叫李知之的人。」
『我真的很抱歉,小知,只是現場情況有點棘手,被害者的下體塞了很多東西,有梳子還有牙刷什麼的,和腸子混在一起,一時半刻清理不出來,這裡的鑑識組又都是新手,我得留下來指揮。你們什麼時候吃完晚飯?會在機場附近吃嗎?我開車去接你們。』
電話那頭依舊語氣溫和地交涉著。
「你對男人的肛門這麼感興趣的話,不用勉強。」知之淡淡地說。
『小知怎麼知道被害人是男性?』男人的嗓音在那頭溫煦地笑著。
「以牙刷的長度,從陰道捅得出來的東西有限,至少捅不到腸子。而喜歡玩肛門的蘿莉控並不多。」
『這很難說,有的戀童癖患者因為年幼女性陰道狹窄,無法進入,就改由肛門侵入的也很常見。』念長用「薯條要沾蕃茄醬還是蜂蜜芥末醬好?」的語氣說著這些話。
「你在描述年幼的孩童時,通常習慣用『那孩子』。但是你沒用,代表這次的被害人是成年人。成年人的括約肌也比較鬆弛,比小女孩容易插到深處。」
「我可以拜託你們不要在桃園機場的大廳聊這種事情嗎……」
善存在旁邊小聲地說,但沒人理他。
『小知真的很厲害呢。』念長由衷地稱讚,善存看知之板著臉沒吭聲。
『善存和你在一起嗎?』念長又問。
「不關你的事。」知之說。
『替我跟善存說,要他好好去上課,阿姨上次打電話來,說她很擔心善存再這樣玩下去會考不上大學聯考。』
念長似乎非常理解怎麼和知之這種人應對,這也是善存最佩服他家表哥的地方,『阿姨把善存託給我,我有責任。』
「大學聯考這種東西現在錄取率比馬英九穿泳褲出現在新聞上的機率還高,有什麼好擔心的。」
知之冷漠地說,念長在電話那頭輕輕笑了幾聲,這時電話那頭傳來嘈雜聲。
『抱歉我得掛了,組長叫我過去。小知,你晚上有沒有空,我去……』
「滴」的一聲,善存看知之狠狠按下掛斷鍵,還順手關了機,把手機塞到卡其褲後的褲袋裡,大步往廁所方向走。
善存看著知之始終不茍言笑的臉,他得承認,要不是他這神祕室友性格古怪外加不太好相處,光就外表而言,李知之還真是他們這些視覺系搖滾青少年嚮往的對象。知之有一張非常藝術的臉,善存不知道該怎麼形容,不是世俗金城武式的那種帥氣,而是一種古典美。
古典美,嗯,善存覺得自己中文還挺不錯的,真想給自己按個讚。
善存一直以為知之有女朋友,長得像知之這樣的男人又成天混在琳琅滿目的大學女生中,善存不認為有哪個雄性生物能夠倖存。
但知之從沒帶過女人回家。光是善存今年十七歲,從國中到現在都交過一、兩個,呃可能是兩、三個倒貼的小女朋友了。但今年情人節知之整天都把自己關在房間裡,研究尼安塔德人的頭骨。
順帶一提他家表哥好像也是一樣,雖然就皮相來講也是型男一枚,但可能是個性太古板,今年情人節念長因為日月潭發生船難,整天都在跟溺死的腐屍Say I Love You。
知之板著臉一路走向男廁所,隔壁的女廁因為剛有一班飛機降落,正在大排長龍。一個女陸客拉著行李就往知之這裡撞過來,知之來不及閃躲,一晃就往牆上摔。
這時有隻手伸到知之腰間,一把就撐住了知之,還善盡紳士義務地把知之扶了起來。
「謝……」
知之伸手扶了差點掉下去的眼鏡,抬起頭來正要道謝。一照面不由得怔住了,因為扶住他的不是他想的另一個陸客,而是個令人一見就難以忘懷的人。
那是個男人。知之想他應該不是搭這班深圳到臺北的班機,因為怎麼看也不像是中國人。
男人有著一頭黑髮,修剪成類似羽毛剪的模樣,他臉上戴著墨鏡,讓知之看不清他的眼睛顏色。但從高挺的鼻梁和深遂的輪廓看來,這人不是亞利安就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種,考古人類學系的助教這樣判斷。
不過令人矚目的是男人的穿著。知之不知道他是不是誤會了什麼──他穿著一件印有紅色大扶桑花,印象中只有夏威夷度假村之類的地方才看得到人穿的花襯衫,外加同花色的及膝短褲,小腿上還看得到熱情奔放的腿毛。
再配上那個幾乎遮住他整張臉的墨鏡。知之覺得待會說不定就會有頭上插著花的女孩冒出來,替男人套上花圈。
「Hello?」
大概是知之發呆太久,那個白種男人出了聲。
「May I help you?(需要我協助你嗎?)」
男人的聲音相當具磁性,充滿了某種戲劇化的熱情。這種嗓音讓知之想起了徐念長,那個對死人比對活人還熱情的傢伙。
「No, I'm alright.(不了,我很好。)」
知之說著扶著牆直起身,才發現男人的手還一直停在他的腰上,五指還往內縮攏,根本是用手捏著知之的腰肉。尋常人要是敢這樣對待他,指骨早就被他折斷了。
「Or maybe you can help me?(或者,你願意協助我?)」男人彎下腰來微笑。
但不知為什麼,這白種人雖然熱情,身上卻散發出一種類似獅子或是山豹類的氣息,讓知之不敢輕舉妄動。
「What do you want?(你想要什麼?)」知之冷漠地問。
「Wow, wow. Don't be so hostile to me. I'm not trying to be rude.(喔,別這麼殺氣騰騰的,我無意冒犯。)」
男人咧嘴笑了,知之在他唇內看見一排雪白的牙齒,面部寬闊下頷卻尖峭,果然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種。但男人的英語意外地沒有英國腔。
知之還沒回答,長廊那一頭就傳來聲音。
「知之,知之!你跑到哪裡去了?大事不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