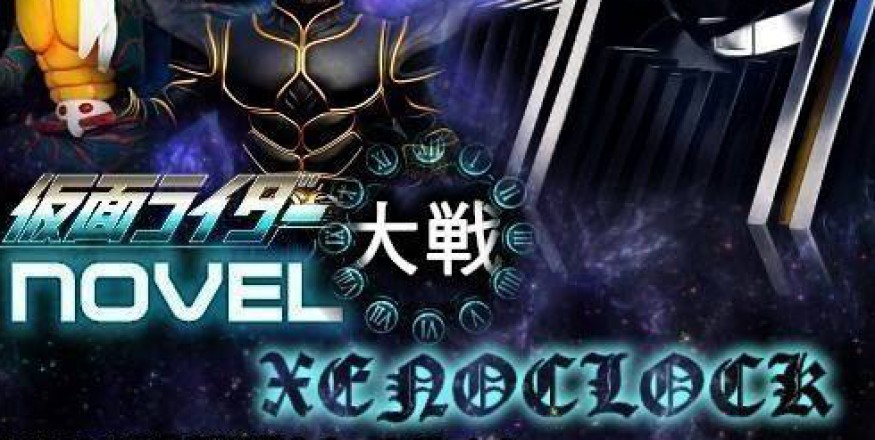幪面超人NOVEL大戰XENOCLOCK
一切始於小眾知情者掌控之法理:「世界將會終結」。所有並行發展的世界會歸納成同一界域而亡,破壞的敗瓦裡會吹拂重生之風,世界、宇宙,由零重啟。--飛彩體內的陌生人鴻上光生、永夢久違重遇的友朋艾瑪。曾定義的印象,可能已變更於不知何時何地。結果,或許他們都遇上了「最熟悉的陌生人」。--異界(XENO)戰記第二集:幪面超人NOVEL大戰XENOCLOCK,即將開始。
第四話 Familiar Stranger
除了當ANKH離開,無法習慣哥哥回復成那個溫柔善良的樣子後的一個月外,比奈幾乎沒有感到如此不自然過。現在她正跟一位西裝不挺、樣子不俗的男子並肩而行,每當轉頭望去便見他眨下單眼,不是為送秋波,只是單純向比奈傳達「請放心」的訊息而已。
然而,即使比奈不熟悉男子,也清楚男子平常不會擺出那種表情。陌生的外貌加上不相襯的舉動,令比奈感到二重尷尬。
身邊的男子叫鏡飛彩,是位很有名的醫生。從熟識他的人口中僅僅得到丁點情報,因為他們知道再多的情報也是無謂。現在的鏡飛彩不是他們相識的鏡飛彩,只是擁有鏡飛彩外貌的「人」。
如果以比奈最近看過的熱門動畫電影來比喻,鏡飛彩就似電影的主角一樣有他人的靈魂在他體內,成為了他。在鏡飛彩入面的人、對比奈眨單眼的人,全都是鴻上基金會的會長:鴻上光生。
與明日那小姐按電話內容去到鴻上基金會大樓,望到飛彩哼住歌做蛋糕時,其實一早已猜到他是會長。可是實際望住陌生男子擺出各種會長的舉動,實在無法不感到詭異。
載住會長靈魂的飛彩在外頭活動之際,失去意識的會長的身體仍在CR總部休息,沒有跟來的明日那小姐回去看顧他與里中小姐。會長不聽勸說使用飛彩身體外出,是為了跟比奈出席本來預定好的畫展。比奈當然盡力拒絕,卻始終敗給會長的意向。
飛彩從一身白袍換上整齊西裝,帶住比奈進入畫展入口。因為畫展是限定展示,只有受到邀請的名人才能進入,果然兩人馬上就被阻下。
兩位身高差多的保安請他們出示請柬。以「一高一矮」形容他們絕不適合,其中一人的高度不算上是「矮」,只是因為另一人高得過份而看似矮小而已。可能因為太高的保安知道自己僅靠外觀已能嚇走人,所以一直保持沉默,由另一個人滿面笑容的對應客人。
飛彩假裝在身上尋找請柬,但他早已知道請柬正在CR的身體身上。在身上搜來搜去幾分鐘,兩位保安不想令彼此難堪,主動又友善地請飛彩與比奈離開,直至一把富有莊嚴的低沉聲線叫住他們。
畫展會場內走出一位頭髮略有花白的中年男子,他留住比奈。
「他們是我的客人。」僅僅一句說話,便令兩位保安放開限制退開。擁有這般權限的人,當然就是開辦這個畫展的主人,富豪藍軌石正。他一身禮服亦無失禮場合,只是他的氣質比起「富豪」,更似一位老邁的伯伯。絲毫架子都不擺,他和藹地迎接二人進場。
比奈呼一口氣,總算避過了最難為情的一瞬。石正先向比奈示好,然後便開始打量起飛彩,視線由頭掃到腳下。
「嗯……真是和電話中所說的一樣,完全是別人的模樣呢。」
來到前其實會長已透過電影向石正交待,所以才會由他親自出來迎接。石正望到飛彩後,只不過吃驚了一下,隨後便開始帶住兩人去欣賞會展。
「等等!我不是想失禮,但藍軌先生你的反應好似太少了吧……」
換作一般人應該更驚訝吧?這種想法令比奈忍不住閉嘴,而石正反而才被她的反應嚇到。
「呵呵,失禮的是我才對,正常的話的確要更吃驚才對。」石正把手搭到飛彩肩上,兩人間身高的差距也令他感到違和。「不過不論活多久啊,光生這傢伙都會製造不同驚喜。我都習慣了。」
飛彩聽完,舉起姆指大叫「斯巴拉西!」接著又對比奈介紹起石正這位友人的獨特之處:「這傢伙才是最令人吃驚的一個。以往他都只是個充滿野心又冷血的企業家,倒是近年來忽然換了個人一樣,又致力於慈善之類的發展。你應該也是有他人入了你的身體吧?」
「哈哈,是被我遇到的一些人與事,改變了我至今的價值觀而已。」
每個人都會遇上改變一生的事物,藍軌石正在幾年前亦有過難忘經常,使他將企業轉形成更加考慮社會低層跟其他第三世界的優異品牌,幾年間媒體對他的探究都從未停止,好似不容許一個人忽然展示良心一樣。
而正因為石正的改頭換面,成為了與鴻上會長之間的友好關係。可惜在比奈眼中,不過是望到兩個怪人的友情而已。
「事不宜遲,這裡展出的除了我與朋友閒暇畫的作品外,還有從其他地方購買回來、很有特色的作品。……雖然不盡是什麼名畫展覽,如果可以成為比奈小姐妳的靈感就好了。」
聽上去不似是客套說話,反而更似是藍軌石正出自內心的祝福。比奈微笑接受,開始靜下來欣賞牆上的畫作,被襲擊的不安與對鴻上先生他們的擔憂都暫時先放下。
說起來,海東在離開前還打算到這個畫展偷走有價值的東西,若他在場的話一定會失望吧?因為這裡的畫作都不是名畫,反而是一些不被注目、在世界各地的「一般人」所畫的作品,應該都不屬於價值不菲的一類。
再者,知道藍軌先生是一位多麼友善的人後,比奈也不希望他會被海東的壞習慣傷害。
「比奈小姐,請妳看一看這張畫。」完全不似才剛遇到的陌生人,石正親切地介紹每張畫作。比奈似乎亦拋開了心中的芥蒂,走到石正那邊聽他解說。解說期間飛彩一直沉默,而又不是在聆聽。
剛才已說:會長的精神在飛彩體內,身體則在CR總部。他們兩人不是交換了身體,現在飛彩體內還有屬於他個人的意識。打從來到畫展前數十分鐘前,飛彩的意識便已經醒來。
默不作聲的外表下,飛彩的腦中一直都有兩個意識在對話。
-
身體被綁住鉛鐵,突破一切浮力地直墮名為疲困的深海。
墮落的過程雙眼仍然張著,因為疲累的只有身體,精神卻似個不願入睡的孩子。
昏倒前的一瞬,永夢好似見到了艾瑪──那個與他一樣喜歡遊戲的少女。是幻覺嗎?是因為今天早上看顧小朋友時,想起了關於艾瑪的續關理論嗎?以為沒有機會重遇的對象,不會因為一個小小的回憶而現身面前吧。
當時永夢沒有足夠時間判斷她是真實還是幻覺,唯一望到的只有她那雙綠寶石一樣的眼睛。提起綠寶石,艾瑪的別名其實就是有綠寶石意思的EMERALD,尚記得永夢與她初初認識時,一直都難以發出EMERALD的正確發音,最終雙方都放棄──變成了以暱稱「艾瑪」稱呼。
而且當時雙方都很滿意這個稱號,永夢(EMU)與艾瑪(EMMA),相近的發音對二人而言也成了親近的證明。
想跟艾瑪說的話有好多好多,兩人都一樣喜歡遊戲,自艾瑪離開後的每個新遊戲發售日,永夢都想與她相見、如昔日一樣討論遊戲。當然永夢從未想過現在的生活中欠缺了什麼,只是如果那些日子裡有艾瑪在的話,一定會比想像中更要快樂。
如果能重遇艾瑪的話……永夢在水底中閉上雙眼,溫熱的觸感遍佈滿面。咦,深海是這麼溫暖的地方嗎?觸感與視覺的差異將永夢的精神召回,雙眼再打開後,四周已由水底變成一間不熟識的房間,刻意調教成不刺眼的柔和橙燈置在床的旁邊,一滴溫熱從臉頰留下。
「這裡是……」意識仍然混亂,永夢先將溫暖觸感的來源從額上摘下,那是條未擰乾的毛巾,面上的水滴全都來自它。起床後,幾乎沒有彈性的枕頭看似是別人的用品,四周的擺設也是個人的物品。看來這裡既不是醫院的床位,或是什麼酒店的房間。
「起來了?」聽到床舖上的雜音,有人打開門開了天花的燈。多得床邊那盞燈光的關係,乍然明亮的環境令永夢雙眼刺痛。走入的人正是夢中一直見到的艾瑪,永夢呆著以為自己仍然在夢中。「忽然昏到地上,嚇壞我了。」
艾瑪從永夢手中拿走毛巾,不以為以接觸到他的手。真實的觸感向永夢證明了眼前的景色與人物都不是夢境。
「艾瑪?」由回憶、幻覺再加上夢境,多次浮現的樣貌真的實在眼前,永夢依然不肯相信這種偶然。「真的是妳?」捉緊住拿走毛巾的纖細手臂,可能是因為水底的夢境影響,永夢也沒預想到自己反應會這麼誇張。那種自然地抓緊的催促感,似乎是意識到不伸手便會令它消失一樣。
「你太大反應了啦,永夢。」艾瑪亦溫柔地叫出永夢的名字,他那種反應看來艾瑪並不討厭,應該說是理解他因何而抓緊自己,好歹自己當時沒有告別便離開了。視彼此為友朋過後,一句再見都沒有就走去,或許已成了一種微小的背叛。
「因為、因為……我一直都想找到妳啊!」幾乎是以快哭出來的聲音說。
「抱歉,不過能夠再見到你真是太好了。」溫柔的笑容、翠綠的雙瞳,艾瑪的一切都跟一年前沒有差別。「已經成為醫生了呢,永夢。」
「不,現在也只是實習期間而已。」永夢搔著頭,難為情地回答。「倒是艾瑪妳,這一年到底去了哪裡啊!」
「嗯……嘛,我回去了英國一下。」艾瑪本來就出生在英國,在中學生階段跟隨祖母來到日本生活,除了名字與樣貌外幾乎已經是個完美的日本人。在日本生活了那麼長時間,卻忽然要回去英國,恐怕是家人的關係吧?很怕觸碰到艾瑪感到敏感的話題,永夢也不多問。
「聽我說,我真的有好多好多想跟你分享,例如MIGHTY ACTION X終於發售。記得嗎?當時我們一起笑過它又會延期的遊戲!」興奮得幾乎要從床上跳下來,永夢尋找一直帶備身上的遊戲機想跟艾瑪分享,精神的疲累與身體酸痛都被他拋諸腦後。
然後艾瑪緩緩將手放他背上,讓永夢安靜下來。
「永夢真的很喜歡遊戲呢,不過你先多休息一下吧?我到冰箱看看有沒有喝的。」是因為一時之間太興奮了嗎?艾瑪看來對永夢的態度不太適應,好似刻意想逃離他的話題一樣離開了房間。
她的舉動無疑令永夢感到失落,因為跟艾瑪之間的羈絆,難道不就是由遊戲所結成的嗎?然而她卻擺出了不感興趣的模樣。永夢感到失落,直至剛才都以為惜別一年的艾瑪仍是那個熟悉的她,沒想到她身影一轉,竟不知不覺間成為了似是陌生人一樣的存在。
一年,想想也覺得這是足夠改變一個人的性格。
永夢放開身體的力量躺回去床上,剛才尋找遊戲機時好似摸到手機在胸前口袋。將它拿出來望,多次來電在他昏迷時撥來,幾乎都是來自同一人:九條貴利矢。
那個滿口謊言的人嗎……唯獨現在這種時候不想理會他呢。永夢厭惡著,可是來電次數的數目已透露著來電的重要性,考慮到可能跟他人的性命有關,永夢也不得不按下回撥的按鈕。
接通了,永夢以鬱悶的聲音問:「貴利矢先生,找我有要事嗎?」常人也感知到下一句將是「沒要事的話我就掛掉了。」沒想到對話那端的貴利矢卻不是以往那慢條斯理的語氣。
他急忙地說:「名人?太好了,你正在跟小相好一起吧?」
什麼小相好,連跟艾瑪一起的事都被知道,永夢自然地感到一股被監視的厭惡感,使他的語氣更加惡劣。
「是又怎樣。」
「是你就趕快逃。」
「咦?」
「好好聽住,我收到POPPY的電話說現在肆虐的遺失病,有機會又跟黑色EXAID有關。」
黑色EXAID……對,昏倒前永夢望到了他跟他人戰鬥的過程。的確似是遺失病那麼怪異的現象,並不難與BUGSTER扯上關係。只是,兩者的關係也跟艾瑪沒有任何關係才對。永夢就聽住貴利矢的聲音一詞一字吐出:
「……而我看到了,你的那個小相好與黑色EXAID是同一伙的。」
證據只有貴利矢的目擊,而他所指的指控都是與現實不符。就似之前他指黑色EXAID的正體是幻夢集體的社長一樣,黑色EXAID偷走了卡帶、協助BUGSTER,又怎麼可能是想阻止病毒擴散的社長。
同樣,艾瑪不過是個喜愛遊戲的普通人,又有什麼動機去與黑色EXAID同流合污?
「……你又撒謊了吧,貴利矢先生。」
冷淡的語氣再次成為刺入心胸的一根刺,貴利矢這次沒有閉口沉默。
「誰會在你的生死關頭撒謊啊!醒醒吧名人,不要因為對方是你的相好就不願面對事實!」
電話的那頭是難得一見認真起來的貴利矢,或許他尚未察覺到「事實」一字在他口中有多可笑。然而,正因為他緊張得連自嘲都做不出,才更令人覺得他可信。
不論那是事實還是謊言,說服力都瞬間倍增。永夢知道有點愚笨,可能對方只是裝出可怕的語氣而叫人相信,這種方式對率直的永夢而言十分奏效。
「你知道我不相信你的。」
「你看一下那小妞的身上吧,既然她與黑色EXAID一伙,那就一定沾滿了BUGSTER病毒。你自己看完的話就趕快逃,就這樣!」貴利矢怒氣沖沖地掛了電話,感覺被人教訓一頓的永夢猶如被雪上加霜。還未搞清楚來自艾瑪忽然的疏遠感,現在又不得不懷疑她是BUGSTER方的人。
內心知道已不會再相信貴利矢的說話,卻又無法否定他──只要讓永夢自己看見證據,那就無可反駁了。
身體與聽筒變得前所未有的沉重,永夢推開了門走出大廳。不願抬高的視線沒有留意艾瑪的家的擺設,只是望到艾瑪停在面前。
拿著一杯溫水,艾瑪問:「怎麼了?」
默不作聲,永夢朝她伸出特殊聽診器,和以往一樣進行病毒掃瞄。由CR配置的BUGSTER專用聽診器,向來都被用於對遊戲病病患的初步判斷。因為有機會出現誤診,用聽診器判定為帶病者都會被帶入CR,利用大型掃描器作更進一步診斷,也就是說聽診器的結果不一定可信。
然而……當聽診器投影出的結果畫面前所未有的強烈時,永夢再也無法用任何藉口說服自己。
艾瑪的確帶住BUSTER病毒,並沒有出現病患的徵狀。唯一的可能信只有一,如貴利矢所說:她跟黑色EXAID一樣跟BUGSTER有所關係。
剛才從艾瑪身上的疏遠、陌生,現今與貴利矢所說的事實重疊在一起。腦中擅自用了一條線將兩件事連繫,永夢開始理解一年間艾瑪的改變到底有多大,大得幾乎顛倒至今的認知。
「艾瑪,妳這一年間到底做了什麼?」
始終不肯抬高視線,眼角望到她將水杯放下了。
「回了英國。」
「……請不要騙我。」感知距離疏遠,永夢也不再用只對朋友使用的親密口吻。
「我沒有騙你。」
「那麼告訴我,妳……已經不喜歡遊戲了嗎?」
「我喜歡。」艾瑪嘗試伸出手抓緊永夢──卻被絕情地甩開,永夢步步退開,去到陽台的位置。
「既然喜歡為何會成為用遊戲害人的身份啊!」永夢怒吼,這下不論艾瑪再多掩藏,也知道無法不說出事實。「現在在街上受苦的人們也是、至今受苦的患者也是,我無法原諒妳是那些BUGSTER的一部份!」
「永夢,你聽我說。」
「沒用的,直接殺了他吧。」兩人激烈的對話途中有第三者插話,退到陽台的永夢旁邊,一直藏身的黑色EXAID衝出。永夢還未趕得切反抗,而艾瑪遏阻的聲音還未傳達開去,黑色EXAID就把永夢從陽台拋了下去。
從足足十層樓高度的位置,永夢被投下──教心肝掏空的離心力促成發自腹腔的高呼,與地面的距離正以驚人速度縮減。
一絲絲代表亡命的氣流掃過臉頰,永夢在風中切換成遊戲時的狀態。急速運轉的腦與思緒命令身體戴上了GAMER DRIVER,只要變身的話多多少少能從逃過死亡的關口吧?說時遲那時快,自由落體狀態的永夢已穿過光屏
「變身!」
MIGHTY MIGHTY ACTION X!
在空中變身成EXAID,永夢能做到就只有這麼多而已。
死亡是可以避過,但摔斷雙腿的結果還是難逃吧……。抱著這種決斷,EXAID任由身體投入死亡速度。
「二速!」
及時從地上跳開,是由一直徘徊附近尋找永夢的貴利矢。他變身成的二頭身穿過光屏,軀體不自然地撟起,LV2的LAZER是賽車遊戲的化身,一台載有意識的越野摩托。
爆走獨走激走暴走!!──爆走BIKE!
車尾的排氣管噴出加速火舌,趕上了EXAID下半身宣佈報廢前接住他。EXAID一手抓住把手,在空中坐座位上成功落地,人車一同呼一口氣。若時機偏離半秒,EXAID就只能在輪椅渡過下半生了。
「……多謝你,貴利矢先生。還有,抱歉。」
「啥,叫你多點懷疑人的是我。若你還是充滿謎團就死去,我作為監測醫望住你的死屍也找不到答案。沒事就好。」
未能夠指出LAZER的藉口太勉強,EXAID便望到同一路上早已現身的黑色EXAID。不知道他們是用什麼方法瞬間落到地上,但反正黑色EXAID平時都是神出鬼沒,連LAZER跟EXAID也沒有在意。
反而更重要的事,他旁邊站著的是艾瑪──大概「鐵證如山」就是這麼回事吧?艾瑪確實是跟BUGSTER是一伙的。
「艾瑪……」
「永夢……」不似EXAID,艾瑪反而好似還想說什麼。在她發出聲音前,黑色EXAID已湊到她耳邊,輕聲唸道:「不要白費至今的計劃。」艾瑪立即面有難色,本來要說的話都吞下,伸出了雙手,轉成冰冷的語氣說:
「……我已經棄去艾瑪這個名字了。我是琳博斯。」
純白色的機甲手套包住她兩手,手背分別有半圓的造型,都嵌住半個深綠色玻璃球。
那一刻,那個眼神,艾瑪已由熟悉的友人成為了陌生人。
EXAID清楚對方表明敵意,下車拿出紅色卡帶,展開新遊戲領域後一個紅色機械人被召出,在EXAID的頭上待命。
激突ROBOTS!
「大.大.大變身!」
紅色卡帶插入腰帶上的第二個插槽,EXAID重覆一遍開關蓋子的動作,機械人便張開口想咬住EXAID頸以上的位置。
被遮住視線,他沒察覺艾瑪舉出手,手背的球體浮出代表「十」的古文字。一眨眼間,對面機械人的身影乍分為十,每個都咬住EXAID身上不同位置。僅僅一瞬的痛楚被倍化為十,EXAID痛得大叫,LAZER亦被忽然增加的機械人嚇倒。
敵人型態轉換失敗之際,黑色EXAID毫不打算留情,BUGVISOR光槍模式飛射疾呼的黑線。
「危險!」LAZER見狀將卡帶插入車身側面的插槽,對襲來的射擊抬高前輪。
GIRI GIRI CRITICAL STRIKE!
車胎被盔甲包住後伸出刀刃,疾旋形成了鋸齒切開光線。以爆炸揚起的塵沙遮蔽,LAZER在情勢不對下只好強行把EXAID扛到座位上,趕在RIDER CAGE變零前離開。
他們離開的背後令艾瑪低頭,她用顫抖的聲音問向黑色EXAID。
「你們在令人們痛苦嗎?」
黑色EXAID頭也不回,也想往另一個方向離開。他回答:「一切都是為了妳口中的『續關』。」
帕拉德忽然現身在黑色EXAID的旁邊,以深不可測而由略帶稚氣的語氣說:「數據收集得很順利呢。」
黑色EXAID頷首。
「大概只差數十個人而已,很快便完成。」
-
夜深,離開藍軌石正的畫展後,飛彩安排別人送比奈回家。而他自己一人則走在街上,轉入一條小小的道路,仍然營業的食店點起柔和燈光。
「還想用我的身體做什麼?」無人的小道只有飛彩一人的聲音。參觀畫展途中,飛彩本來的意識已完全醒來,他不斷與體內的鴻上會長爭論有關身體控制權。將一整天都用在畫展上已經令飛彩做不成幾個手術,現在已過了十二時,對注重規則的飛彩而言是必須入睡的時間。
「嘛,又不會害你。當是抽抽時間陪下老人家吧。」兩個意識都經由同一張口對話,憑不同的語氣作區別。鴻上會長似乎還想用飛彩的身體到別的地點。
飛彩嘆息,思索自己為何會遇上這種麻煩的狀況──當然他知道答案,自從被魔王KIVA控制與黑色EXAID在空中相撞後,自己的體內便多出名叫鴻上光生的意識。平常而言,飛彩也是個會尊重老人的人,可惜現在的狀況絕對稱不上平常,而且鴻上會長也不是個普通的老人。
一般的老人哪會這麼中氣十足地大叫「斯巴拉西」?
「呵呵,那是我自小以來的習慣。」會長發言回答飛彩,二人共享意識,只是在腦中所想的事都會不自覺被對方知道。
本著大家都不是按自己意欲而變成這種狀態,飛彩忍口不頂撞會長,但責備的話總是在腦中透露給他。
「現在這個狀況也沒有太差吧?」
「何止太差,完全是NO THANK YOU。」
「為什麼?」
「你也試一下在平穩的日常生活中被陌生人控制身體,去做一些不習慣的事如何?」飛彩注意到自己的語氣太不尊重,於是趕緊解釋:「抱歉,但我想說的是這不是我習慣的生活規律。」
「不是每一步都按計劃進行才能叫生活的。」與鴻上會長共識意識令飛彩更感受說話背後的意思,他是用自己的人生經驗來跟飛彩對話。「你應該也有過意外吧?不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飛彩的日常當然充滿大大小小的意外,像是見習醫生見入CR也好,還有最近BUGSTER的活躍模樣也好──而最大的意外,就只有關於他已不存在於世的戀人:小姬。
小姬的死令飛彩的人生走入最大偏離。若小姬仍然存在,可能他沒有為了根絕BUGSTER而當上幪面超人,自己也跟小姬幸福地生活著。
不好,回想太多的話會被鴻上先生知道。當飛彩察覺到已太遲,他作好心理準備會被問起關於小姬的事,沒想到鴻上卻控制身體停在一間店前面。
「這裡是?」
一所不起眼的地方,招牌就只寫住「食店」。
會長沒有回答便推開門進入,如外表所見是一間普通的小店,由座位圍出供人上菜的空間,還能清楚見到廚房內部。這種店對飛彩而言都是從未進入過的地方。
著住簡單服裝的男子出來迎候,一身鬆緩的和式衣著雖然隨意而又不失禮,最大的特徵是他臉上有一條長長的疤痕。教人忘記去幻想那條疤痕背後的故事,他用和藹可親的微笑接待說:「歡迎光臨。」
店入面都沒有半個人,飛彩隨便找個座位。老闆刻意用濕巾抹掉飛彩面前的位置,一塵不染的環境令飛彩沒有太厭惡。
「現在四圍都是什麼遺失病,很少人會夜深仍留在街上,更別說光顧了。所以有點塵,失禮了。」說明完後他便束好腰間的布衫,準備好入去料理。他問飛彩:「那麼,要吃什麼?」
說起來還不知這裡有賣什麼食物,飛彩急忙環境四周,除了列在酒品與價錢旁邊寫住豚汁定食的紙條外,周圍幾乎沒有稱得上是菜單的東西。不知所措之際,會長控制嘴巴說出「酒蒸蛤蜊」,飛彩與老闆都嚇一跳。
隨便就說出不知菜單有沒有的要求太無理了吧!飛彩試在腦中責備他,沒想到老闆馬上便回答「好」然後走入廚房。
會長則不再出聲,好似只是讓飛彩吃完那道料理一樣。
良久,熱烘烘的酒蒸蛤蜊端出。飛彩見會長一直沒有反應,怕一直不動也會顯得失禮,下意識就合起掌說「我開動了」。然後用不習慣的筷子,一個接一個把蛤蜊的肉夾出。
眼見飛彩笨拙的動作,老闆也不禁失笑。飛彩立即停下手來說:「啊,對不起,忽然就點了菜單沒有的菜。」
「不,只要是能力所及的料理的話便隨便客人點,是這裡向來的方針。」老闆看來也想與飛彩聊下去,點了支煙坐在他面前。「倒是令我驚訝的是你點這個,又不是什麼名物,但以前也有不同的客人很愛吃它。」
「你記得其他客人點什麼嗎?」
「多多少少吧,每份料理都有各自的故事,進入店內的人,走在街上的人都有不同背景。我就在店裡做著料理聽他們講述,不知不覺就記住了。」
老闆望住那碗蛤蜊,笑說:「其中很愛吃這個的客人是對母子,經常爭吵,都不知他們是關係還是關係差。」
「啊,是嗎……」
「另外還有個愛吃酒蒸蛤蜊的男客人。他啊,有自己一套的想法──例如對慶祝啊生日啊份外的執著,還經常提起什麼欲望之類的話。他一光臨,周圍的客人都覺得他是怪人,默默地吃完飯便離開。」
意識中有一道苦笑聲,大概不是飛彩的錯覺。
「他已經很久沒來了,可能是察覺他為其他人做成困擾吧。最後一次光顧時,不僅點了酒蒸蛤蜊,還帶了個蛋糕給我。」
「蛋糕?」
飛彩追問,不想透露太多其他客人資料的老闆先猶豫一下,及後才避開敏感的部份,大概地交待事情。
「他說他與妻子離婚了約一年,當日是她跟其他人再婚的日子,想將最美味的蛋糕送給她作結婚禮物。所以刻意帶了蛋糕來叫我嚐嚐,真是個怪人呢……。」吸一口煙,又說:「至今沒陪她渡過的聖誕、紀念日還有她的生日,他想用那個蛋糕彌補妻子。」
端子的煙灰被拍落缸中,明明才只吸了兩口,老闆便將它壓熄。
「我說得太多了,你慢慢吃吧。」轉身又回去廚房繼續料理。
飛彩吃完後,明明身體不受他人控制,卻仍不自覺地到了附近公園。微弱的街燈下,他坐在鞦韆上,這時會長才肯開口說話。飛彩與他對話,彷彿會長就坐在旁邊的鞦韆上一樣。
「多謝你,很久都沒嚐過老闆的手藝。要知道我的年齡與身份,都不允許我在這種時間到小巷吃有酒的料理嘛?哈哈哈!」
彷彿當是什麼事都沒有,會長繼續他誇張的笑聲與語氣。可能他沒察覺,剛才一番話已承認他就是老闆口中的「客人」。
「對不起。」飛彩道歉。
「幹嗎道歉,是我帶你過去的。」會長窺望飛彩的腦中。「你現在正有歉意,覺得聽完我的往事後有點不快樂,同情我、想我開心起來是不是?」
雖然他用的字眼過於籠統,但既然是出自能夠窺探自己腦海的人說的話,飛彩都無力否定。
「但我的往事與你的女朋友比起,不過是一件小事不是嗎?世上有多少人會知道你的遭遇,感受被BUGSTER奪去所愛的悲痛。」
「……但這也不代表你經歷完你的事會不悲傷。」
「就是說你的同理心令你為我設想?」
沒有回答,只是點頭。
「既然如此,為何你會不肯接受他人的好意?」會長問,一針見血。「你不介入患者,將別人拒絕到遙距之遠,以冷淡的態度去應對別人,卻不能以同樣態度應付腦入面的老人?」
「這是……」
「不只由自己出發,甚至連別人的同情與關懷都被你拒絕。難道那些被你指為沒有類近經歷、不明白你苦痛的人,不就等於剛才抱有同理心的你自己嗎?」
至今被自己指為NO THANK YOU的存在,POPPYPIPOPAPO、見習醫生還有其他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不能因此隨便改變我走過來的路。」飛彩又擺起了拒絕的姿勢,甚至在腦中重覆叫會長不要窺探自己記憶,那心情既不安又不快。「對陌生人打開心窗什麼的,只會阻礙我為小姬報復、阻止我根絕BUGSTER。」
「但你最大的仇人,不就是你自己嗎?」
當日就是因為過於埋首醫學,才令小姬離開自己身邊。一切都如會長所言。
「我也為了研究欲望而花上一切精神跟時間,因此無視了妻子的欲望:她希望我花更多時間陪她。這點我跟你都相同。」
沒有主動去了解這位老人,飛彩一直待他為陌生人。
「我不會叫你不要報復、不要原諒你的敵人,那些是你的欲望、你的能量。但追求欲望同時,真的有必要封閉自己嗎?欲望是種可以生出萬物的能源,然而固步自封,卻只會令自己走入死胡同。」
「……我會考慮一下。」難得地,飛彩沒有立即拒絕他。大概他知道會長就似一面鏡子,將自己的心完美地映照出來吧。「或許我也該道歉,剛才我說對你這樣的陌生人要NO THANK YOU……但像你這樣的陌生人,卻有種異常的熟悉感。」
「HAPPY BIRTHDAY!!!!」
中午時他控制飛彩身體喊出的說話又響起,公園中迴盪飛彩聲音,路過的人都投以怪異眼光。
「今天……不是我生日啊?」
「但今天是全新的鏡飛彩的誕生,斯巴拉西!!!!」
只能苦笑,飛彩驅使身體在被投訴有人滋擾前離開公園。
-
同一夜幕下,艾瑪──不,琳博斯家附近的公園。
她為剛才攻擊永夢的事苦惱著,決心與昔日的友誼對持不下,而她知道自己前進的路只有一條。
一條不能回頭的道路。
忽然在琳博斯面前,出現一個小身影,一位小男孩。男孩的表情嚴肅,他盯住琳博斯。
雙方透過眼神大概已交流了某個訊息。
由男孩率先扯下頸上的吊飾,握住它唸道:「變身。」
琳博斯雙手亦浮出不亞於雙眼的翠綠,幻化成手套後吐出同樣字眼:「變身。」
「我是XENOCLOCK的使者,韓斯(HANDS)。」
「同樣……我是琳博斯(NUMBERS)。」
兩人的造型相約,同樣帶有灰白聖堂風格。只是琳博斯的下半身明顯成為了裙擺的形狀。雙眼亦不似韓斯一樣戴一間間的罩子,反而是一片橙色的護目鏡,保護住綠色發光的雙目。
大家都變了身,目的都是一樣:為了得到XENOCLOCK而除去對方。
「請原諒我,為了阻止XENOCLOCK運作,我必須得到它。」
「你就是悠遇到的使者嗎……世界末日是必然的,阻止運行只是你個人的幻想。」琳博斯變出光球,藉由手背寶珠浮的古文字,光球被倍化成好似仰天能見的繁星之數。
「難道妳有更好的方法?請務必讓我洗耳恭聽。」
「你打過遊戲機嗎?」
「當然。」好歹韓斯覺醒前,都只是一個普通的男孩而已。
「那就方便我說明了。我的目的是──讓整個世界續關(CONTINUE)。」和一年前跟永夢所爭論的話題一樣,琳博斯堅持她續關的一說。
「不明所以。」韓斯不理解她,亦不打算理解,既然雙方都有不同目的那就只有一個解決方法。他雙手握成拳狀,光化成實體在指間滲出。「TRACER SECOND。」
被叫成「追秒」的聖劍顯現,劍身猶如一條細絲。琳博斯控制星光飛翔,連水都流不過去的緊密彈幕是滿盤的針芒,筆直朝韓斯發出。
韓斯把追秒劍連續揮舞,劃過肩旁、掃過頭上、入到腋下──因為劍身太過細長,琳博斯根本望不到劍的痕跡。但唯一可以肉眼判斷的,就是飛去的光彈在劍舞下已被全數斬碎。
琳博斯再發動能量,利用光芒織成一把擁有精密細節的斧劍,又利用手套力量倍化,列成整齊的戰陣。
不似剛才的光陣,琳博斯刻意準備了堅硬百倍的兵器,這就令韓斯無法以無形之劍斬斷。
可惜,韓斯亦有他的對應方法。琳博斯都察覺不到他把追秒聖劍收起,手上透出的光已幻化成另一把劍刃。
「ENGAGEMENT MINUTE!」
一樣細長,不過起碼可以用肉眼判斷它的存在。對戰斧劍之陣的,是韓斯曾在香港斬傷AMAZON OMEGA的那把「戰分」聖劍。
琳博斯舉起手,正要下令戰陣開火之際,夜色的月影下竟跳出一頭巨大的怪物。牠一出現就咬碎了所有斧劍,仰天發出無聲咆哮,牠的軀體在燈下又似犬類又似是蜥蝪。
最詭異的是構成牠身體的物質……那是一團團光滑的棕色肉塊。
怪物咬碎戰斧後望到韓斯,以本能襲擊他。忽然被亂入戰鬥的韓斯當然毫無準備,輕易就被怪物咬到,又被牠撞開……傷勢比想像中還要嚴重,他只好先放棄對付琳博斯的念頭離開。
剩下怪物跟琳博斯,牠不攻擊,使剛才擊退韓斯的舉動似是保護球博斯一樣……琳博斯根本不認識牠,但對方卻肯跟她四目交投──直至一發槍聲響起,四周的樹林休息中的小鳥都被槍聲嚇到。眼見牠們飛走途中,四周的空間明顯被一新。景色不變,卻再也沒有小鳥飛走。
這裡是……遊戲領域?琳博斯立即想起中午變身成EXAID的永夢,可惜一同現身的那些染上油漆的鐵桶已證明領域不是永夢打開。
開槍的人是幪面超人SNIPE。
他開口問琳博斯,那聲音是黑道醫生花家大我。
「你帶來的傢伙是什麼人!」他開槍牽制怪物,並令琳博斯明白剛才怪物為何會保護她。不願接受這是現實的眼神望向巨大的怪物,她說:
「不是人,」
「……是AMAZON。」
-
已閉門的畫展,中午時透明化跟住比奈的海東,現在利用時空灰牆現身。
無人的畫展,海東就只盯住了其中一張畫。這裡展出的畫作都是世界各地、寂寂無名的作品,卻出現了一張海東有所印象的畫。
比奈說這裡會令海東失望,也不盡是正確。
他朝那張畫舉出擺成手槍形狀的手指,靜靜說了一聲「BINGO」。
畫下面的介紹已說明了海東來到的原因──它就是海東與韓斯到步前被某位富豪買走的「線索」。
來自菲律賓的畫,標題是「OUR TIME」。
待續
ns 15.158.61.17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