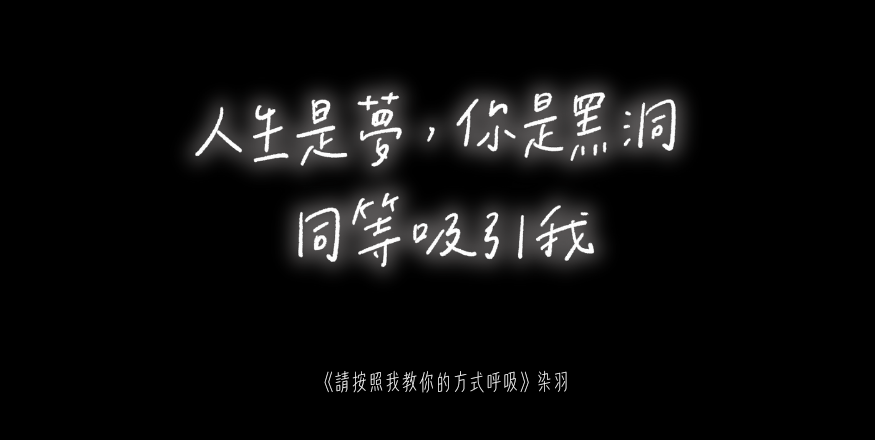每年,想要飛越大洋,卻直接死於馬路的蝴蝶多得我們算不清。
我並不知道每年凋零於這種死法的蝴蝶數目有多少,但我知道今天我們的擋風玻璃至少撞上了七隻,其中一對是雙殺,蝴蝶翅膀卡在縫隙間,另五隻則孤獨地死亡。
蝶的死亡對於我的男友,江紹勛來說,其實只是拉開雨刷桿子的幾秒鐘的事;但對於我一個多愁善感的女孩,我總會想要在雨刷落下前,仔細看一眼牠們死後的樣貌。
不是指牠們絢麗繽紛的翅膀,而是指牠們的眼睛,是否還看著東海岸的那片大洋──你問蝴蝶有眼睛嗎?有的,牠們當然有。蝶的眼睛是由無以計數的許多小眼睛(複眼)所組成的單眼,所以牠們的視野很廣,也因此身為人類的我其實並無法看到牠們死後,那些細密微小的複眼,究竟都倒映著些什麼。
「妳又在看牠們的複眼了嗎?」剛用雨刷把蝶屍掃下擋風玻璃的男友瞄了我一眼,我聳聳肩把向前探去的身子安分縮回座位,手腕因此而從袖襬跑出。冷氣的溫度有些刺人,我下意識把手縮了回去。
「明明什麼也看不到,不是嗎?」他邊熟稔轉動著方向盤,邊向我問道。
前方出現發散著橘黃光輝的隧道,我沉默幾秒,直到那抹光芒把車內的我們都覆上一層暖色調,才緩緩開口:「你也知道我很固執的。明明知道什麼都看不到,但還是會為了愛,繼續撐下去。」
語畢,我沉默轉過頭,看著那些快速從視野掠過的慘白的牆。即使被燈光照成了令人有點壓抑而反胃的橘色,但還是可以看出水泥原本的慘白。
江紹勛亦是沉默無話,在前方出現光點,出口的灰藍色光芒慢慢變大時,伸手把爵士樂的聲音轉大,彷彿想要掩蓋掉剛才我冷漠的字句,還有一路上的我們的沉默。
男歌手婉轉悠揚的歌聲迴盪在車內,然而音浪強得車體微微發顫,本來撫慰心靈的抒情爵士變成了刺激耳膜的雜樂。耳邊出現了短暫的耳鳴,那一瞬間腦海跑出了很多無聲的畫面,人物手舞足蹈,玻璃安靜碎裂。
掩蓋不掉的。音樂跟沉默,都掩蓋不掉的。
……
他是咖啡店店長,而我是他的常客。通常也是關店前才肯離開的最後一位忠實客人。
剛開始,我只是因為身為一名大三生,為了要做報告,所以才常常在咖啡店裡熬到晚上快十點,熬到我杯子裡的咖啡都已經浮上一層脂。
我記得很清楚,第一天他對我說的是:「小姐,我們要打烊了喔。」接著我便老老實實地抱著筆電離去。
而第二天,他沒有再趕我離開:「今天也要做報告呀?」只是默默幫我把咖啡收回,換了一杯牛奶。
第三天,他微笑說了聲:「今天也加油呀。」把大部分燈關掉,只留我頭頂與他坐在吧檯的兩盞,仍為我換了一杯牛奶。
第四天,我的報告只剩下最後一點,於是我趁著剩餘的時間與他閒聊,得知他的名字叫做江紹勛,也發現我們在很多事情上的觀點都很一致,價值觀相同,不停感嘆相見恨晚。
「欸不過,為什麼你知道我要熬夜,還給我倒牛奶啊?」我把喝剩三分滿的杯子舉起,在昏黃的燈光下輕輕搖晃。如果是紅酒杯子的話,應該還挺有氣氛的,但偏偏我手裡的是直筒玻璃杯,裡頭裝盛的是香醇牛奶。
「希望能幫妳助眠囉。年輕人不要常熬夜,對身體不好。」他像是摸小孩子似的拍了拍我的頭,「何況妳看起來一點都不高,趕快再補補鈣質吧。」
「你才不高。」我對他翻了個白眼,下意識衝出這句話,卻忘記他之前給我送牛奶的時候,一米八多的身高足以將燈光遮擋,纖細修長的影子覆蓋我的目光。
「先追上我再說吧,在妳頭可以擱到我肩膀前,不準點咖啡。」他輕輕彈了我的腦袋瓜,我登即不滿地摀住額頭,雖然不痛,但還是乾瞪著他。
「為什麼是長到能擱你肩膀的高度?」我側眼問道,眼角染上不解。。
「這樣……」江紹勛正想接著講,放在一旁的手機卻很不是時候地響起音樂,是一首抒情的爵士樂,男歌手低沉深情的歌聲悠悠迴盪在只有我們的咖啡館裡頭。
江紹勛拿起手機,歉意向我說了聲:「抱歉啊。」接著便急匆匆上樓,留下我一個人坐在吧檯前,手裡還拿著那杯三分滿的牛奶。
想必是很重要的事吧?雖然還納悶著剛剛斷掉的對話,但我還是貼心的把剩下的牛奶一飲而盡,繞進吧檯內側把杯子給洗乾淨了,放回原位。而後我在桌上留了張紙條,上頭寫著我的電話跟一句「我明天再來」,想了想,再在句末畫了隻我最喜歡的蝴蝶,還有笑臉。悄然離去。
而就在那個晚上,江紹勛打了電話過來,大致就是向我道歉剛剛有公事要辦,所以留我一個人在原地等待。電話裡的他聲音有些沙啞,傳入耳裡略為撓人。
「啊,沒關係啦。不用專程為這種事打過來的。」背部靠在枕頭上,我邊這麼說,邊掀開書頁的一角,紙張摩娑聲一時取代了對面短暫的沉默。
「可是……」他聽起來有些躊躇,就這麼斷在這裡不說了。
「可是?」我忍不住問道。
「可是,我想聽聽妳的聲音。」
「……什麼?」腦袋彷彿嗡了聲,眼睫顫動,我翻書的動作定格在半空中。
「沒什麼……趕快睡覺吧,好夢。」
話音剛落,電話就被切斷了。
我的心情瞬間紛亂如麻,充斥著慌張、驚訝、不解,甚至還有隱隱的期待……攤於手裡的書頁不被聚焦,模糊成一片黑白色。我盯著手機良久,直到窗外一隻鳥從餘光飛過,才把手機扔到一邊,用棉被悶住頭。
耳邊不斷迴響著那句「我想聽聽妳的聲音」,還有在咖啡館裡那句「長到能擱我肩膀的高度」,都在很不是時候的時間點斷掉,反而造成我不停遐想。
直到後來,不只是耳邊,就連我閉上眼,腦海都會浮現他那張文藝氣質、留著少許鬍鬚的俊逸的臉……我的眼睛時不時會突然睜圓而乾瞪棉被。
毫無疑問地,我失眠了。
並毫無懸念地,跳進了他所設下的陷阱。
……
接下來連續兩個月的時間,不管颳風下雨還是多麼克難的狀況,我每天都一定會準時在晚上七點去到咖啡館。只有準時抵達,沒有準時離開。
江紹勛是一個很會拿捏與女孩距離的人。他總是能輕易撩撥年輕女孩的心弦(當然也包括剛升大三的我),而後又故意在該死的關鍵時刻切斷話題,不斷讓女孩覺得自己跟他很曖昧,但是又僅僅只是點到為止。
而我們就是這樣藕斷絲連的關係。
每到夜深人靜,他把我送回家之後,我都很想悶在被窩肆無忌憚地尖叫。大吼問他我們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咆哮問他到底為什麼要這樣玩弄年輕女孩脆如蝶翼的心……但膽懦的我,終究不會這麼問他。至少當時的我不會。
而且,其實我沒資格的。
這種若即若離的狀況一直到了我們認識三個月,期間除了他休假以外,我都準時到咖啡館裡等他下班,就只為了能夠再跟他多說一些話。很傻,但也很值得。我明白那種情愫已經從剛開始的仰慕,慢慢萌發成了無可抑止的愛,於是我在一個無風的夜晚,他陪我回家時,跟他告白。
「紹勛,我想問你點事。」昏黃的路燈,使我的目光有些迷濛。
「問吶,怎麼突然變這麼扭捏了?」他勾起笑容,欲離開的腳步在我抓住他衣角後停下,轉頭看向我。我的耳朵肯定紅了吧?耳垂的灼燙與瘋狂劇烈的心跳都讓我快要抓狂,但他還是淡然自若地看著我。
「我想問你,我們兩個究竟是什麼關係?」不敢抬頭的我,只敢低頭看著他纖細瘦長的影子,在光影裡微微搖晃。
「妳希望我們是什麼關係?」江紹勛驀地將我的下巴捏住,抬起,逼我注視著他的褐色眼眸。明明就是琥珀石一樣的顏色,但此時卻深不見底。
「我……」我突然意識到這樣的距離太近,伸手想要推開他,卻僅僅只是抵在他的胸膛,變得毫無反抗意味。那一剎那,不知道是不是錯覺,我感到他眼底多了分得逞的笑意,接著便將身子向我傾來,灼熱的鼻息噴灑在臉上,我幾乎無法思考。
看著他愈甚靠近的臉,我甚至能夠數清楚他如蝶翼般輕微撲朔的長睫有幾根。我不敢往下看去,那對微微敞開的薄唇,因此選擇了緊閉雙眼,做一名等待愛人親吻的情竇初開的女孩。
然而他並沒有吻我,而只是輕輕擦過我的唇角。但就算只有那樣,被他擦過的那片肌膚仍熾熱地燃燒起來,我無可抑止地被自己給灼傷。我迷茫地看向他,而江紹勛則撇開臉,歉意地說:「對不起,我們不能在一起。」
「為什麼?」我壓抑著自己顫抖的聲音,想要讓自己聽起來比較平靜。
「因為……」江紹勛頓了頓,從口袋裡拿出一枚戒指,於燈光下閃著刺目的冷光。
「我已經有家世了。」
在說完這幾句話之後,我們沉默許久,直到頭頂的燈明滅幾下,江紹勛輕聲說道:「對不起,子瑄。」接著便回身要離開。
而我終究是不願意要就此放棄一個與我價值觀相同、成熟、情商高的男人,沒有妄多思索這會不會是一個閱歷豐富的男人所故意耍出來的圈套,就直直拉住他的手,用力把他扯回我的面前。
「那你在乎嗎?」我直視著他的眼睛,看見了表面的茫然與眼底的狡黠。
「我不在乎。」不多等他回答,我直直踮高腳尖,把自己的吻奉上。
江紹勛的嘴唇很冰涼,帶著一點咖啡的苦澀味道,起初似是愣住,毫無反應,但很快就反客為主地按住我的後腦,傾下身子,舌頭從貝齒間的隙縫靈巧探入。我們彼此渴望的索求,在夜裡發散著獸般的氣息。
「你愛我嗎?」連綿的一吻結束,我喘著氣抬眼看向他。
「從第一個夜晚我看到妳的那一剎那,我就已經愛上妳了。」
下一刻,我們再次湊在一起,我抓著他的衣領,而他則捧著我的臉,彼此索求、吸吮著。即使他的身分讓我起初退卻三分,但最終我仍無可自拔地沉淪於他的氣息。
於是那一晚,我們上床了。我,跟一個有婦之夫。
……
我們的戀情一直持續到我大學畢業,我決定轉到他的咖啡館做服務生的工作,但直接被江紹勛果斷拒絕。理由是,怕我們的事被周品媛發現……嗯,周品媛就是他結婚七年的老婆,那個讓我嫉妒得快要發瘋的女人。
我始終不懂,為什麼她有那麼多大好機會可以死死地綁住江紹勛,但還是把他們倆的婚事搞得一蹋糊塗。聽到這裡,你應該覺得我也很過分,但我不在意,因為我對江紹勛的愛,足以支撐我做出更多不擇手段的事。
而那一句話,剛交往時我以為我這輩子都不會說出的那句話,我終究還是在渴望攫取更多愛意的貪婪之下,問了出來:
「你什麼時候會跟那女人離婚?」
我轉身靠在他溫熱厚實的背上,雙手環繞住他的腰,撒嬌般地將下巴擱在肩膀上,「什麼時候……嗯?」抬眼看向他假寐著的側顏。我一向能分辨出人有沒有真睡,正如我一眼就能看出一隻蝶的生死。
「我知道你沒睡。」
江紹勛睜開眼睛,微微轉頭將咖啡色澤的雙眼直視我,回答出乎我意外的堅定:「我們不會離婚的。」
「……為什麼?你對她又沒有感覺,不是嗎?」我試圖拼湊如玻璃瞬間碎裂的笑容,低下眼睫,伸出手在他的背上畫著圓圈。
「但妳對他有感覺,不是嗎?」江紹勛的聲音陡然變得咄咄逼人,宛如一把以冰製成的刀刃,直直扎入我的心臟。他拿出手機,滑開一張照片,正是我跟一名清秀男子的親密合影。
「你,你怎麼知道的?」我木訥撐起身子,看著他穿拾起衣服。
「記得確認過我沒有在可看貼文的名單,再上傳呀。」江紹勛嘲弄般勾起殘忍的笑容:「笨女孩。」他撿起最後一件外套,想要離去。我狼狽地抱住他的腿。
「紹勛!你不要離開我,好不好?」眼角泛起一層朦朧的淚霧,我低聲啜泣起來,視野裡模糊的他似乎轉過身,蹲在我的面前。
「妳要怎麼做?」他歪頭勾起笑容,頓了頓,改問:「妳能怎麼做?」
我直直把我的手機拿過,「我現在就跟他分手。」望了眼他,我毫不猶豫地按了一串號碼,打電話給我從大一交往到現在的男友邱翊。
「嘟──嘟──」我按下擴音鍵,而他沒有阻止我,彷彿想看看,一個被他灌迷湯的忠誠女孩,可以為他做到什麼程度。
「喂?」對面熟悉的聲音傳來,乍聽之下正常,但知道他身患重病的我,聽得出虛弱得他正忍著強烈的不適感在跟我說話。
我在他還沒喚出我的暱稱之前,瞪著江紹勛玩味的眼,經淚水流過的肌膚濕潤而滾燙,我決絕地對著手機另一端的他講道:「邱翊,我們分手。」
時間彷彿凝滯了一樣,空間的膠著感令我幾近窒息,無法呼吸。
對面的邱翊亦良久無話,最後才緩慢吐出幾個字:「我知道了。」
「小蝶,祝妳……」還未等他說完那句話,我立即切斷了電話,瞪向仍勾著笑容的江紹勛。
「這樣可以了嗎?你可以繼續留在我的身邊嗎?」
江紹勛無所謂地聳了聳肩,嘴角的笑意愈發深然,張開手臂抱住了像個想要用心愛的娃娃挽留令他無可自拔的玩具的孩子。我緊緊回抱住這個男人,在他的胸前啜泣起來。
「妳做得很好,子瑄。」
……
邱翊的喪禮我沒有參加。
據說他在我告訴他要分手,切斷有關於他的一切聯繫之後不久,他就因為受寒而加重病情,接著沒有生存意志的他,靈魂便永遠留在了那張病床上。
我知道我應該參與他的喪禮的,但我知道我會被唾棄,雖然這只是一小部分我所退卻的原因。而另一部分,得歸咎於我實在無法抗拒周品媛對我提出見一面的邀約,即使江紹勛很早就警告過我,不准私下與她會面──但不管怎麼樣,我想見見這個讓江紹勛離不開的女人是怎樣的一個存在。
我們約在一間風格迥異於江紹勛咖啡館的店,這讓長期待在他店的我感到無所適從,十分不習慣。但我終於見到了周品媛──一名舉止優雅,打扮談吐都透露著一絲高貴雍容的女人。
「妳就是周品媛?」她低頭輕啜了口咖啡,從容成熟的姿態與心情起伏盡寫在臉上的我,形成極大反差。
「幸會,徐小姐。」我坐下來等她把那口咖啡喝完,這才舉起手欲與她相握。而她只是微笑注視著我,毫不理會我僵在半空的手。
「妳就是紹勛的妻子吧,果然保養得很好,絲毫看不出老態呢。」我悻悻收回了手,把髮絲挽至耳後,淺笑著與她對視。
「還是別玩這些勾心鬥角的事了,徐小姐。」周品媛不動聲色地從身邊的皮包抽出一疊厚實的牛皮信封,明眼人一看便會意過來。
「我希望妳能離開江紹勛。徐小姐,妳還很年輕,所以我選擇開恩給妳一筆錢離開他,而不是一狀把妳告到法院。嗯,以勾引有婦之夫的罪名。」周品媛把那疊信封推至我的面前,聲音平淡無比,像是沒有情緒一樣。
「前幾個,我可都是選擇提告。」
我微微頓在原地,心裡升起了一股怒氣,但很快就平靜下來。我微笑著把那疊錢推回她的面前,「妳太輕視我對他的愛了。」
周品媛輕笑一聲,淡然自若地望向窗外,正順著玻璃表面而緩慢滑落的雨水。
「愛他愛到自殘?妳捨得妳自己就算了,他也還真的捨得呀。」
「不甘妳的事。」像是瘡疤被揭開一樣,我把手腕藏入長袖外套裡,已經掛不住笑容的我直直起身,拿起包包後便逕自離開,隱隱約約還聽得見後面傳來周品媛輕飄飄的、帶著嘲笑意味的話語:「傻妞。」
離開咖啡廳後,我沒有回家,而是躲在一處附近的窄巷,拿出包包裡的美工刀,發瘋般地把刀片割向自己病態的蒼白手腕,妖冶的血珠如玫瑰花瓣於水氣之中泌出、盛開,綻放在我癲狂的目光。
許多剛結痂的疤被割開,左臂又添了許多新傷,但都割得不深,只淺淺的劃過而已──如果我死了,還怎麼愛江紹勛呢?我的呼吸緩緩平息下來,恢復冷靜的我把美工刀放回包裡,重新把袖子拉下,遮擋住那些醜陋的疤與新傷。
自殘的習慣大概是從我與邱翊分手之後養成的。我很愧對總是很細心體貼的邱翊,也常質疑自己是否應該離開江紹勛,回去照顧那名真正愛我的人。我並不介意邱翊生病這事,我介意的是,他無法給我我所想要的,江紹勛成熟的魅力與炙熱的愛。
如果邱翊的愛是含蓄內斂的蜂蜜水,江紹勛的愛便是昂貴的我只能乞求的一劑毒品。而我上癮了。只要他仍持續把愛施捨給我,哪怕一點點,我都會因此發瘋離不開他。
我往巷子外探出頭,看見周品媛坐上她的車後,也立即招了臺計程車,一路尾隨她那臺銀色賓士回家。過了許久,她把車停下來,而我看見門口停了那臺我所熟悉的,江紹勛的車子後,我終於確認這便是江紹勛所一直隱瞞我的,他們的住址。
默默記下周品媛與江紹勛的房子住在哪裡,我回到家,洗完澡後愜意躺到床上,向江紹勛發了條訊息,勾起勢在必得的微笑。
……
池畔,一隻紋白蝶拍動翅膀,我伸出手,牠便親暱停在我的指尖。
「妳真的很喜歡蝴蝶。」坐在我身旁的江紹勛手臂往後撐,悠閒笑看我指尖的蝴蝶將翅膀緩慢張合。
「是啊,蝴蝶也很喜歡我呢。大概是被我的喜歡給打動的吧?」我似笑非笑地看著他,把視線轉回紋白蝶的身上。「你知道嗎?我只要看一眼蝴蝶,就能直接確定牠是否還活著。」
「是嗎?那牠是活的還是死的?」江紹勛指了指我手上的蝶,未驚動牠。
「死的。」我燦笑著看牠的翅膀張合著,望不清牠的複眼看到了些什麼,但肯定倒映著我們兩個吧。
江紹勛輕笑了聲,「看來妳這能力也不怎麼準啊。」
「我見過周品媛了。」下一句,我直直把重點說出。雖然沒有轉過頭看,但他臉上的表情肯定很精采。
「……妳見過她了?為什麼?」江紹勛的錯愕突然轉為憤怒,責罵著我為什麼要擅自去見她。
我蠻不在意地聳聳肩,「她主動找我的,還給我一信封鈔票呢。不過我沒答應。」
「她主動找妳,那妳幹嘛去赴約?我不是都跟妳說……」
「江紹勛。」我倏然轉頭看向他,勾起期待的笑容。「上次,我傳給你的那條簡訊你考慮得怎麼樣了?希望你不要讓我失望。」
他似乎被我突如其來的變化給略微嚇了一嚇,也是,溫馴只會哭著求合的小綿羊突然換了種怪異的腔調,他當然會嚇到。江紹勛隔了許久才開口:「我早就告訴過妳答案了,我不可能娶妳!也不可能跟周品媛離婚!」
指尖輕輕一捏,紋白蝶柔軟的腹部因此而塌陷、擠壓成與原本截然不同的形狀,牠仍奮力地掙扎著,然而生命卻毫無保留地快速流逝,很快就再也不會動彈。翅膀垂落,我的手指沾滿了牠掙扎時所撲打而落的鱗粉。
「好吧,我明白了。」我以撫摸愛人的溫柔姿態,把沾了鱗粉的手輕柔覆在他的面龐,另隻手則捏著不再動作的蝶屍,湊近他的眼前。
「──看,確實死了。」
……
江紹勛在那一天之後就像是人間蒸發一樣,把我有的所有聯絡方式刪掉,甚至把咖啡館轉手讓給其他人。可能他注意到這次玩大了吧?發現我已經不是那麼個單純的女學生,已經出社會了、不嫩了、不天真了。而我也大膽承認我的貪婪。
雖然起初他的迴避令我很抓狂,但隨即我便釋懷了,畢竟我手裡還有著他的住址;而他們,對於我已經知道這件事渾然不知。為了不打草驚蛇,我忍著不把我精心準備的上百隻蝴蝶屍體扔在他們家門口。
而後我住在他們家附近的小旅館觀察他們許久,發現江紹勛每天晚上十點都會出門,大概凌晨一、兩點才會回家。哈,真難想像周品媛會是一個這麼大方的人,丈夫出門鬼混,自己還乖乖空守閨房。
把時間算好過後,我等著夜晚降臨,站在玻璃窗前看著遠方熟悉的那點身影開車離去,而自己則悄悄潛入他們家──他家三樓有扇窗子,長期不關,於是我便用我所帶來的工具,悄然爬入室內。
尚未落地,我幾乎就快被迎面而來的灰塵給嗆到,使勁抑制著大聲咳嗽的衝動,只悶悶咳了幾聲。蒼藍色的月光從窗外斜映而入,許多因我而揚起的粉塵在月光裡飄搖,似是夢幻的藍色蝶翼,在撲打間無意落下的鱗粉。
打開手電後,我環顧四周,發現這裡似乎是座廢棄的閣樓,但什麼也沒有放,把燈光掃過之後就能看見位於中後方的拉環,大概是出入口。
於是我把耳朵傾到木板上聆聽,確定無動靜後便拉開鐵環,一躍而下。
躡手躡腳地繞過二樓過後,我站定在了確定周品媛在裡頭的房門前,背後拿著一把刀,輕輕敲了敲。她似乎正要入睡,慵懶從容的語調傳來:「喲,你今天怎麼會這麼早回來?」
而當她一開門,冰冷的刀刃便直直擱在了她白皙的頸上,力道稍稍沒控制好,在上頭留下一串鮮紅的血珠。周品媛明顯震顫一下,但看起來還算處變不驚,沒有尖叫,而是瞇著眼睛看向我的臉。
「是妳?」
「是我。很驚訝嗎?」我似笑非笑看著她。
「倒不。不過妳的愛情還真是讓我佩服。」
「妳也不差。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放任自己老公四處採花的妻子。」我戲謔歪了歪頭,想要在她眼裡看到任何一絲的羞恥、不堪。
「妳把刀放下,我們談件事情如何?」周品媛仍牽著那抹令我厭惡至極的笑容,即使刀子架在她的脖子上,她仍心如止水。
「周品媛,妳覺得妳有資格跟我談條件?」我嗤笑。
「我最大的籌碼,把他重重擊落,再由妳來救贖他的籌碼──還不夠資格嗎?」下巴挑釁般地抬起,周品媛的頸子因此而滲出更多血液,她嘴角愈發加深的笑容令我寒毛豎起。
「妳什麼意思?」我警惕看著她,想要在她包裝得毫無破綻的臉上找出任何端倪。
周品媛從容把她頸子前的刀給撥開,黑色的絲質睡衣隨著她的腳步而輕微晃蕩,血紅的刀痕與雪白肌膚成為強烈對比,但她絲毫不在意,反而勾起一抹如玫瑰般盛開的燦笑。
「我帶走他的財產,而妳坐等收割愛情。」
「這樣的條件,很棒吧?」
我在她眼裡看見了熟悉的神色。
那是江紹勛等待了我幾個月後,看著獵物上鉤的,得逞的笑意。
……
江紹勛在得知自己的錢財、所有資產,都被他同床共枕近十年的女人給帶走之後,失意了好一陣子。
而我始終不明白他們那種愛情倒底是建立在什麼之上,會是恩情嗎?我實在想不出為什麼江紹勛這樣花心的男人,可以娶到周品媛那樣的女人,而周品媛又為什麼願意待在他的身邊那麼久。直到我的到來,打破了他們的平衡。
情感真的是一種很微妙的物事,脆如蝶翼時美得令人流連,韌如橡膠時又變得一文不值。我們遊走在道德底線與情慾之間,用著最無保障的方式去維持所謂的新鮮與刺激。
很矛盾的一件物事。
我靜默看著被搬空的房子,還有脆弱的江紹勛來回走動,不停重複著暴躁打電話、無力捶牆哭泣的循環動作。如果是以往的我,我肯定會選擇奔上前要他不要再捶牆了,忘掉那個賤人吧,你還有我啊!
但此時此刻,我的心臟卻平靜得不可思議,全然失去了當初得不到,所以特別渴望的感覺。對於他需要救贖這一點,似乎激不起我腦海裡的半點漣漪。
突然之間,江紹勛憤怒走了過來,大力把我推攘到地上。
「妳他媽說點什麼啊!為什麼只是站在這裡不動?妳為什麼都不講話,啊?」他怒瞪著我,憤懣的眼神幾乎濺出花火,如鳳蝶般於此迴盪,鮮豔的色彩把我灼傷。
猛然間,他拿起一塊木板,狠狠往玻璃窗砸去,窗戶在瞬間碎裂成許多微小的玻璃屑,在燈光照射下隱隱折射出不可思議的彩光,但鋒利的玻璃渣立即飛散一片,連帶我跟他都被碎屑給扎傷。
在拔出一塊刺入手背的玻璃渣後,我突然意識到自己不能就這樣拋棄掉他,江紹勛的落魄我也參做為一名主謀,他的失意、潦倒、窮困,不就是我正想要的嗎?並非出於報復,而是出於戲劇一般的救贖。
「紹勛……」
我輕輕呼喚了聲,發現他站在原地絲毫不動。
「你沒事吧?」
良久,江紹勛的身影微微晃動,走過來抱住了我,下巴擱在我的肩膀上,溫熱的液體濡濕了我肩頭的一大片布料。我溫柔地回抱住了他,眼神有些空洞,腦袋有意無意的運作著,最後浮出了一個奇特的念頭。但我仍舊沒有說出口。
……
「第八……第九隻,今天遇到的第二對。」我順著那對泛著幽幽藍光的蝴蝶,將側向大海的頭轉正,靜靜凝視著那對翅膀相疊的紫斑蝶,彷彿還沒死般,底下那一隻小幅度地晃動著牠如針般纖細的腳。
江紹勛把音浪調低,仍看著前方的路,「牠們還活著嗎?還是死了?」
「一隻死了,一隻活著。」剛說完,被夥伴疊在下面的那隻紫斑蝶便從縫隙間竄出,振振翅膀,逃跑般地飛向太平洋的方向。只留下鱗粉與牠的伴侶,靜靜躺在擋風玻璃上。
我彷彿看見死去的蝶的眼睛,雖然擁有眾多複眼,但牠卻直直凝視著伴侶離自己遠去的身影,還有那片寬蔚的海洋,眼裡沒有我與他。
我突然很想問我的男友,他是否還愛著他的前妻,即使她毫不流連地就把他的所有財產都打包出國,但江紹勛在情場裡,終究是名讓人看不透的獵手。即使此時的他已經收心。
「紹勛。」我凝視著面前迎來的下一個隧道,橙黃色燈光將我們、那隻已經死去的紫斑蝶,以及許久之前就卡在縫隙間的蝶翼都覆上一層柔和的外殼。
「嗯?」他打開雨刷,新的一片殘破的蝴蝶翅膀卡在隙縫之間,與舊的相互交疊。
「如果我告訴你,周品媛現在待在哪裡,你會不會想要拋下我離去?」我還是問出了那個,他失意潦倒時我就想要問的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我肯定知道答案,只是願不願意問出口罷了。
難怪那女人離開時一臉贏家樣,不得不說,她真的下了一盤好棋。連被當作棋子的我,都不比棋手還要了解我自己。
江紹勛短暫呆愣後,誠實回答:「會。」
我微微一笑,把周品媛留給我的名片塞到他胸前的口袋,傾身吻住他的嘴唇。那股初次與他親吻所感受到的燥熱、焦急、違背倫理的刺激感,似乎都在瞬間回到了我們所在彼此身上烙下的,熾熱的痕跡。
我想,我永遠只適合做一名情人。
眼前的隧道出口已經不再是前幾小時的灰藍色,而成為了清明開闊的天藍。我們緩緩行駛著離開,開向蔚藍海洋盡頭的那一片天空。兩片藍紫色的殘翼在出隧道的那一剎那,往波光粼粼的大洋飄去。
每年,想要飛越大洋,卻直接死於馬路的蝴蝶多得我們算不清。
但在愛情裡,有些看似殘破不堪的愛,卻能帶著早已死去的蝶,往大洋飛行。34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gT00PDd2BK
引用句子:34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pHsTdCvKen
「世界在崩塌的過程中,還不忘送你一把砂糖,多麼慈悲。」
「能夠為你心碎是我莫大的榮幸。」
「這個城市人潮擁擠,死傷無數,你沒看見我,我也看不見你。」34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CPjZe2XxTF
PS . 其實只挑最後一句做發想,但寫著寫著就歪成微病嬌了,覺得另外兩句反而比較貼合女主的經歷,所以寫到中間就乾脆把前兩句的元素也加進去www
PS 2.0. 很感謝看到這裡的大家!
ns3.137.168.234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