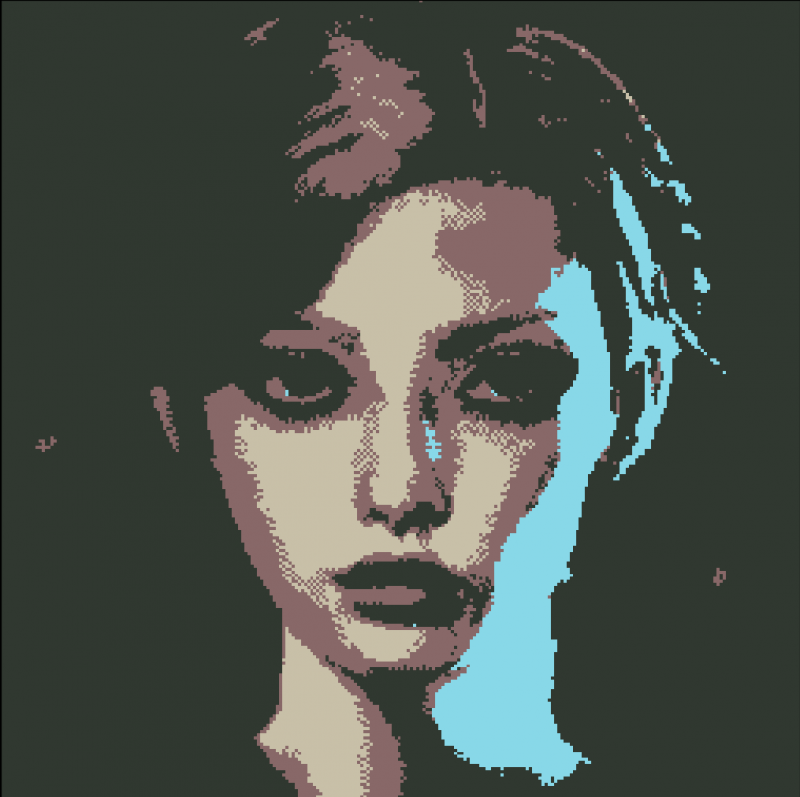 x
x
香腸、烤肉、蔬菜蘑菇等濃烈味道在咀嚼時,如濃郁龍捲般旋轉。吞嚥時,喉頭蠕縮,滿是味道食糜落入肚子,卻沒有任何實感,倒感覺食物的營養有如,某種眼睛所看不見的光點穿梭在體內,墜落,消弭雙腳裡轉瞬即逝的殘碎痠痛。
我呼出一口氣,假裝自己「吃飽」了。看了下手錶——三根時針裡,其中一根剛過四分之三圈,而最新的才正要啟程。就算我沒辦法像普通一樣「吃食」,依然有夠多時間,做完想做與必須完成的任務了。我一如既往地,讓身子開始移動。
我從商辦大樓周圍的水泥欄跳下,短靴與平整的石磚街道悶撞,輕輕叩了一聲。我伸展雙手,坐滿八小時辦公室的背脊咖嚓咖嚓響。時間依然相當充足,但,我一轉頭⋯⋯
綾就在那裡。
純白大衣裹住她單薄、纖瘦的身子,長髮末稍燙捲的烏弧在大水閘牆橋捲起的風中飄舞。她向路邊小販買了昂貴的氣泡飲,面色疲倦灰暗,按著太陽穴而嘆息,直接將紙幣從她的黃色皮夾抽出來、塞入漫不經心的小販手中。
綾仰頭看向巨大、橢圓繭形的工廠,縷縷濃煙從數根煙囪上飄,還有無數水管、煙霧管線從建築側邊突出,如血管上竄下沿。這種建築,在十樓以下是居住區,十樓左右之上,全是工廠——建築間有輸送能源的粗電纜、運載產品與原料的流水線道掛聯,繫起各棟寬大高樓。在煙氣中巨聳、突出地表的幢幢橢圓建築高影,蔓延在米林閣拉市各處。綾這樣看著被抹上煙霧的碎斷天空,神情泫然欲泣。
城裡一片灰暗死寂。在烈陽猛燃的傍晚彩霞下,工廠逐漸亮起窗口的橘紅火光。
她很蒼白,看似工裝的牛仔褲在她身上,遮掩綾身軀的無比削瘦。水道急流的激烈氣息,使她在輕盈大衣裡有如幽魂。黑眼圈,她臉上連淡妝也沒有,但我完全不覺得她像城裡工人或上班族那樣皮膚枯槁。
綾變瘦了啊。
我只能這樣想道。綾瘦到,任何人見到她都會心疼吧。然而寥寥路過的人們,身心俱疲,回眸看向她時是看見綾青春年華的美貌依然餘香綻放,還是見到她那宛如脫離整座忙碌工業城的氛圍呢。
「妳回來啦?」我走上綾身邊搭話。
「咦⋯⋯你怎麼在這?」綾相當驚訝,她手中紙杯的氣泡水裡,冰塊輕撞。
「我一直都住在米林閣拉啊,倒是妳,什麼時候回來的?」
「一個禮拜前⋯⋯呵呵,這好是你在高中畢業以來,第一次主動和我搭話吧?」
「好像是呢。」我抓了抓頭,心跳加快了一瞬。「不是我不主動找妳,是我們在學校之外,根本不常碰面啊。」
「你是想說,我不常回來吧?」
「呃,這,也沒說錯啦。但老實說,妳完全沒有回來米林閣拉?這⋯⋯有點、很意外呢。反倒是我不怎麼像米林閣拉人,卻留了下來。」我一彈被我當外套穿的素灰無扣襯衫,外套上穿了件多口袋束帶戰術背心,加上七分短褲和短靴,在所有人都緊緊包住身體、就連工裝外也加上一層層厚外套或大衣,甚至也隨時帶著面罩時,我的穿著便特別突兀。
「綾妳感覺比我更像米林閣拉人吧?」
「你在說什麼鬼話?」
「國高中時,妳不都知道該要去哪裡才有好玩的嗎?」
她拉緊衣服,強擠出笑容,搖頭:「城裡變化太大了。南國那邊步調很慢⋯⋯你這表情,不會是忘記我去南國讀書吧?」
我連忙搖頭後,她眼神飄向橫跨寬敞水道的水閘:「之前這邊,根本沒有這種水閘橋。」
「市政府他們拓展了很多工廠用地呢。妳真的沒有經常回來吧?事業這麼成功,就連人行道哪邊能走都不知道了。」
她敲了下我肩膀,柔拳分外無力。我不禁想起以往我倆和其他同學們的互動,微笑道:「嘛,事業做這麼大還是要回一下家。看妳似乎和以前沒多少變化,感覺起來也很安心呢。」
「我還是和以前一樣喔。」綾挺胸,驕傲的神情讓她臉上多了點紅暈。
「是啊,只是瘦了。」
綾的笑臉被劇烈咳嗽打斷。我等著她的呼吸平撫。早春的冷風夾帶水氣,似乎對剛回北方的綾,有些太過冷冽。綾雙手摀住口鼻,對凍紅的指尖哈氣。我走離,跟剛才與綾交談的小販,要了份奶油烤馬鈴薯,遞給她暖手。
「難得回來,為什麼不多在家休息呢?妳看起來身體狀況不是很好。」
綾猶豫地,注視著手中這份點心。乳白,但溫暖蒸騰。
綾思考著自己該不該吃掉這份點心,吹著氣,緩道:「可是這麼久沒回來了,我想好好看看米林閣拉現在是什麼樣子。倒是你,為什麼會在這裡?你是在這附近工作嗎?」
「沒。我工作之後總會到處走走。」我輕輕踢起鞋子,讓她看到我那已經走得破爛的短靴:「殺殺時間——反正我也沒多少娛樂。」
「你不再讀那些看起來很艱深的書了嗎?」
「不太可能讀書了。城裡,現在能找到書店就不錯了,不可能期待他們有進新書,再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樣走走冒險都能看到非常特別的風景。妳有特別想看的地方嗎?」
「我記得⋯⋯」綾走到水道邊緣,靠上水泥扶手,看向昏綠的急流:「米林閣拉一直都不怎麼注重美化或綠化,現在回想,都不知道到底城裡到底有哪裡能欣賞呢?」
「雖然大家都不在意美感,但是,有些時候可是能看到廢墟喔?」
「你是想說什麼、城市探索嗎?」
「是啊。」像是,沒有成功拆遷的國民住宅——那如蜂巢層層堆疊的人類臭氣生產區——工廠進入機械化轉型後,就成了複雜的違建、垃圾堆集與社會外人士的聚集地。但整棟蛋形建築,於住宅地位落寞、交通天橋年久失修而坍塌後,化為人們不再注目、路過了也會遮掩、閉氣之處,避免以任何方式進入其中。
我想,沒有人知道國民住宅為何失敗,就如,米林閣拉市裡所有繭狀建築都有用不完的天然氣、取之不竭的水源,蒸騰滋潤著那名為死靈的生活樣式。有些時候我想著,到底為什麼米林閣拉市裡,能有遍佈整片盆地平原的巨大工廠呢?似乎,工廠的濃煙與居住區全日蒸騰的濃熱水氣,掩蓋住任何天空的蹤跡,是另一片巨大的魔法陣,不斷被整座城市的瘋狂工業生產所維持⋯⋯不管如何,我都只能知道自己所體認到的事物。
「我知道一棟國民住宅附近,有人做出原始森林喔?」
「什麼?那也太好笑了吧?那種東西真的在米林閣拉嗎?」
「其實只是個非常無聊的森林罷了。我看了好幾次,才有人把那裡的空地重新整治呢。」那時,除了我,沒有人注視那荒廢景象,而就連居住在其中的人們,自身也融入了廢墟。
「我⋯⋯我想要看海。或是寒緋。」
綾如此說道。
「海?妳在南國已經看夠了吧?還是,妳還不習慣米林閣拉的蒸煙空氣品質?而且寒緋的方向完全相反喔,要走到舊城區會花不少時間,而且還得爬坡。」
「那麼,我想先看海。」綾這時,才與我對視。
「嗯。那就,一路順風了。」我與她揮了手道別。綾將暖暖的馬鈴薯包起來,放入大衣內側口袋,向北方的小路走去。我不禁叫住她:「啊,城裡已經沒有地面層的快速行人帶了。現在大家如果要走,就只剩水道路,或者妳能搭上產業圓環線。」
「那,地鐵⋯⋯」
我拍拍身旁的水泥欄杆:「大部分都用來裝水管,或污水處理設備,或可能是市政府不想再管各家工廠的地底倉儲了吧。天知道是什麼原因,反正路上沒有人,並不是平白如此呢。」轉頭一望,能望到小販自顧自抽起菸,沈浸於雕塑一顆原木人像的專注中,攤販旁的蒸汽水煙緲緲卻無能影響他——小販老闆讓餐車的管線接起公寓排出的熱騰蒸氣,以此取得食物箱保冷和加熱的能源。他毫不在意周圍空無一人的面北T字交叉口,到底有沒有客人。
綾嘆了口氣,沒回話,只是看著水道而靜默不語。她眼中閃過種種思緒與情感色彩,而彷彿不斷奔走的水流帶去了她已過於疲倦、僅剩不多的精力。
「我可以陪妳走一走喔。這條路我有走過,而且,我本來就要散步了。」
「不會麻煩到你嗎?」
「絕對不會。」我微笑。
「你是因為⋯⋯之前喜歡我,才對我這麼好嗎?我沒辦法回應你的感情喔。」綾仰望著我,雙手拉緊大衣衣口,身子似乎又更縮起,不僅僅是畏風,還有其他的情感在她顫抖的語尾中糾結。
「我還是很喜歡妳啊。我們不是好朋友嗎?就我看來,我們基本上和高中時差不多呢——一直,都是如此。只是妳離開了一陣子而已。」
「才不是一陣子吧!」綾拍了下我肩膀,但她回話中的力道速度都感覺,像以往那樣彼此打屁、鬥嘴的節奏——時間就像,完全沒有流逝一樣。
人行道上幾乎沒被磨平,石磚隨意堆疊排列,靠著水泥填補其中粗心而不一致的空隙。旁邊的水道有如小河。愈走離市中心,欄杆的水泥塊就愈為水氣侵蝕,暴露出銹跡斑斑的欄杆本體,妄想中的「小河」,大部分都是清黑色的污水溝。
綾講起我們小時候的紙船艦隊比賽,從那時起,人們不再常於地面層走路了。而米林閣拉的水道人行道,正如髒水清水分隔相間,似乎從那以來就沒有改變。
她在我們緩緩數算著過去的時光,遠方西陽早已沈落在叢叢巨大建築後方,綾踩著這樣朦朧的影子,問道:「你為什麼像老人家一樣散步?」
「其實我碰巧成為米林閣拉市的守護魔法師,只要每天散步,就能讓城市的生命力順利運轉流動。」
「聽你在說笑。我是認真問啦。而且,一個人守護這麼大的工業都市,應該根本忙不過來吧?」
「孤身一人的守護者⋯⋯聽起來滿厲害的啊。」我笑道。
「我很討厭孤獨。如果,能有同伴就好了⋯⋯這樣還能拓展其他故事線。」
「就像超能少年戰隊那樣嗎?」
「就像超能少年戰隊那樣。」綾也微笑。「先不說這個了。你到底為什麼開始散步?是想養生?」
實話實說,總是最佳策略。「我的工作是幫一家螺絲設計廠的商業書信,整天坐辦公室,只有在午休和廁所時才能離開椅子。整天動腦,回到家裡就算腦子累了身體也睡不著,就可以出來健走啦。我最快紀錄是一天繞完全城喔。」
綾噗哧笑了一聲,不敢置信地皺眉:「你超像老頭子啊!」
「米林閣拉市都這麼破舊了,總是得要有人來欣賞、欣賞吧。」
「那我謹代表整座米林閣拉市的居民,感謝你的貢獻。」
我們走過一個轉角後,進入一條筆直,但兩側牆壁高聳不見、夾在兩棟工廠中間,而人行道從石磚變成水道上的鑄鐵網。這裏實在沒辦法兩人併行,我便站到一側,讓路示意綾先行。「女士優先。」
「你什麼時候這麼紳士了?」她微笑,邁開步伐向前走,而我也跟了上去,刻意限制自己的步速以免撞上她的纖瘦背脊。
「我以為⋯⋯」我開口,望向她走路時微微搖擺的背影:「妳會在城裡找工作呢。米林閣拉再怎麼大,廠房和公寓都是一體,錢不一定多,事情不一定少,但一定能離家近。而且,妳以前又那麼喜歡探險⋯⋯」
「你是想說,身為驕傲的米林閣拉人,我為什麼不繼續留在自己所愛的城市吧。」綾沒有回頭。她就算加快步伐,也不會使我跟不上她,但鐵網底下放出的蒸氣吞沒了綾的大衣身影,就像,她允許這城市吸納自己。
「就算沒住在這裡,也可以繼續當驕傲的米林閣拉人,繼續愛著這座城市吧?」
綾猛然停頓,我也趕緊煞住腳步,而我胸膛幾乎撞上她時,只要我伸出雙手,就能輕易將綾攬入懷中。但她以前有這樣嬌小嗎?
「以前的你的話,一定會想出些聰明的話來酸我吧。」
「我已經沒那麼屁孩了。」我在綾轉身回望我時,瞥開眼神。她有些期待地望向我,雙手擺在身後。有某股引力慣性,使我繼續說:「而且我也不會想弄哭妳呢,就算是如此亭亭玉立的骨感美人,被嗆哭的臉還是很醜吧。」
「沒錯。我就是個美女。但你果然和以前一樣,一點都沒成長!」
綾看著我刻意做出無奈神情,幽幽笑了下,回身繼續走著,她隨著流水聲低哼著旋律。我們很快便走出窄巷,一出去,水道與人行道再次分隔,路側的牆面一如往常,與路面泥灰磚同樣塗了層厚重工業漆。年久的濃煙霧霾下,濕氣與廢棄化合物使牆面,越前往外側,便越發衰頹摧毀,但在無聊的灰色穹頂罩下,就有了其他色彩。
我眨眼,路燈有些過於刺眼,不過我依然沒在這裡看到真正的「荒廢」。嗯,還有蒸氣,所以,這裡還有人住、有人開暖氣吧。
「我還記得,我們的水船艦隊有跑過這邊呢。」綾的輕輕撫過斑雜綠漆與鏽紅相間的欄杆,她望向我們面前的蜿蜒水道,隨著數條其他水道接匯過來,水勢愈發澎湧。「我們總是和哥哥他朋友一起,跑到大河那邊去」
「當時的紙船如果有留下來就好了,查了那麼多圖鑑、做了那麼多模型,最後全都被水沖走。」
「不行。」綾毅然否定,她眼神中閃過一抹堅定的冰冷:「那怎麼行呢?如果艦隊都離開了,只有一艘、兩艘船被留下來,或者你為了艦隊做出紙船,但最後卻發現艦隊早已離去,只有那艘船留下⋯⋯但船不就該在水上飛馳嗎?那樣,才最美啊。」
我認真地考慮著,想起公司樓上的業內展場——那如夢境國度似的、晶瑩剔透的世界:「紙船在玻璃瓶裡也能十分美麗。」眾人所注目的睛光凝聚在展覽品上,不斷積累而幾乎抹蓋物品本身。
我伸出手觸碰那些商品標籤時,睛光便化為碎灰般的溫暖烈火,於我指尖成圓成球,吸沒入我體內。周圍人們身上的「期待」的重量化為巨大的無色凝膠團塊,填補上展覽品頓時的靈色黯淡,重燃起睛光。如此來回二十一次觸碰,我左手那無數字的錶面便會多出一根指針,在那層層繞圈的細顫圓陣上緩緩跑動。
「妳若要紙船有行駛的感覺,可以用矽膠拉出水浪。」
「但如果瓶中船壞掉了⋯⋯」
「可以再做吧。總是有方法的。」
我們兩人,沈默,並肩走著。這裏的繭型巨大工廠彼此間隔距離相當有次序,能在工廠間的水道,一眼望向地平線,看見一棟又一棟一模一樣的工廠大樓延展到地平線外。而不論在米林閣拉市的某處,只要在日光下的人行道,旁邊定有水道。
海風從巨大的建築群間,跨入大型水溝,在水道匯集的髒浪上,吹起的純白泡沫不斷被波浪推擠而無法沈下水面。水道如河隆隆湧流,其噪音與四周工廠噪音彼此響應、衝撞然後融合。
再走過兩、三棟工廠,排水系統便幾乎激噴奔流。走道過了個彎後,便讓人行道拉升、遠遠超過水道水面三層樓高。拱橋般設計的寬大水閘,限制了水流速度,那裡正是進入真正的城內主要排水道的水質檢查口。
我在那看到了一小片平地,就在拱橋水閘旁,能望向五百多公尺長的橋型與蒼白水流。平地是由老舊、龜裂的水泥地鋪成,而在靠近水道的那側,有一張看似破爛的金屬長椅。長椅旁,還有兩組貌似曾裝設過長椅的四腳洞口。平地上,四處都有類似的洞口——像曾是翹翹板所在處的長條陰影水泥,或桌子椅子留下的柱腳,以及彈簧木馬的粗大根基孔。這是片,被忘卻的水泥公園,然而,我還能在長椅上,看到金屬座椅陰影中的細小睛光閃爍。
「小時候來海邊,就是來這座公園。」綾的語調空洞,彷彿被那幾乎淹沒我倆聲音的洪水所貫穿出巨大、無可彌補的洞口。
「公園?」我忍不住問道。「這裏距離海邊,還有差不多一半距離喔?」
「你不記得了?」綾轉頭看向,在她身邊、與她一同停下來的我,皺眉的眉間有些控訴、狐疑的味道。
我眨眨眼,更認真「注視」的話就能看見這裡殘留了許多過去的歡樂和星點懷舊,勉強支持這裡作為「公園」的存在特質。但不論如何,這裡不會是儀式的終點。我說:「或許之前,這裡真的是公園吧,但我從來沒看過有多少人出現在這區域——這裡工廠都是新建的。八成在室內的設施,會比在室外的多吧。」
「你都不會對失去海洋,感覺到難過嗎?」綾的語氣現在確實有了指責的尖銳音調。我聳了肩。
「這差不多有六、七年了吧。政府開始第二波填海造陸計畫,把海岸線推到更外側,說是要增加工廠和物流空間。妳知道米林閣拉就是這樣子呢。」
綾撫著胸口,秋波雙眉錦蹙而神情沈痛,望向水道。水閘下的白霧濃郁而緩慢飄落、再生而又緩落入急流水面。海風吹擺著她的大衣衣襬,使綾靠在欄杆上的身影,看起來確實像融入了那刮除城市煙霾的水道。
欄杆尖聲裂開,綾猛然回頭,張嘴彷彿想說什麼,臉色全然慘白,無力地往前傾倒。我趕緊踏步、撈住她的細腰。
她太輕了。綾身著大衣,所以我才沒想像到,她如此瘦弱、有如紙雕。
我還在注視水泥公園的睛光時,風景的轉換跟不上身體移動,這才發現綾某些類似內核的事物——或她的心——在剛才欄杆崩解的瞬間裡,崩落了一部份。若要拿綾和這座水泥公園相比,絕對是她先倒下。
「妳生病了。」但不是,普通人所說的疾⋯⋯
「小感冒而已。」綾推開我,呼吸急促。她凝視著那從欄杆上崩落的金屬碎塊,在空中翻滾著,然後被急流吞沒。
我沒想到自己無心的思緒竟然會猜中,不太敢肯定地搖頭:「要說現在這時代裡,小感冒都能讓妳一副死人樣,我會比較相信妳被吸血鬼咬呢。」
「至少,吸血鬼永遠都會美美的。只要考慮有沒有血可吸就好了。癌症也殺不死吸血鬼的吧?」
「癌症?」
綾走近長椅,坐了下來。她雙手緊握在腿上,等我坐到她身旁便告訴我一切。從大學生活的開心放縱,交了男朋友的幸福,還有工作、打拼,作息不正常,幸虧為了結婚而去體檢,得知自己身染早期癌症。一開始治療後男朋友就跑路了,復健路程困難重重,又得為了生活而持續打拼。
她說小感冒,確實沒錯。因為她現在回到家鄉,身體卻不適應自家鄉的氣候。綾的身體被這麼多事情重壓、耗費燃盡,不禁令她想道⋯⋯自己這樣努力,想要工作,想要結婚,想要幸福,但這世上有什麼值得讓她,自己繼續活下去的事物嗎?
「我原本還想著,至少我還有海。」
「沒有海了,但還有寒緋。」我想不出什麼詩意的話語來安慰她。
「不行啦。我走不動了,就連現在說話,也太⋯⋯太疲倦了。」
「不,妳能繼續走下去。妳這麼虛弱,卻都來這裡了,只要再走一點路就能到海邊⋯⋯妳不就是想死在,自己喜歡的海裡嗎?那麼,就更不能死在這裡、這種不堪入目的水泥公園了吧?」
綾沒有說話。她雙腿緊靠,握著的雙手微微顫抖。我將手,蓋上她的手。讓腹腔附近的極暖隱隱睛光,燒灼過我內臟的黑暗陰影而傳遞上指尖,睛光便像水滴滴落海綿般消失。
『妳依舊能繼續光彩彩奪目。』
她的身體順暢吸收睛光。這的結果正如我所想,但還是十分令我意外。我瞄了眼手錶,錶面少一根指針。我八成,還剩十五小時能用。
「這麼多年,你還是沒練好說甜言蜜語的能耐啊?怎麼忽然這麼俗濫?」
綾的神情裡的絕望稍微淡了些,但她看起來依然,有著重病的慘淡枯槁神色。至少,能笑出來了。
「妳是想死在海中,或是死在寒緋落花的水面上吧?」我看著她沈默下來,盯著我的手錶但雙眼焦點卻彷彿看穿錶面、注視著我的手。「我沒猜錯?」
「如果我說對,那又怎麼樣?」
綾閉起眼,深深吸了口氣,但我搶在她之前說:「我不會阻止妳的。」
畢竟,我都能順利在這座巨大的死城——在這永遠不會停歇、冰冷的工業製造結構裡——找出舒適生活的方法。這片大地,這曾屬於萬靈眾生棲息的空間,每一寸平面皆被工廠覆蓋——滿滿的,全都是水道、走道、污水或資源或產品或人力的運送處理管線。整座城市無盡烈燃。所有人,正如字面上地,被壓在工廠下。
你若想在這重壓下解放、自由行走,就得來到室外人行道的水泥磚路。你的頭頂是被擠壓的長條天空⋯⋯當然,你得在叢叢濃煙與水氣交疊時,能看見天空呢。
《貸睛行》這儀式雖能幫忙維護城市的生命力——將「產品」所沾黏、吸引人們的注意力的那些「光彩」,借送至城裡最崩壞、荒棄之處——卻是勉強使米林閣拉市的內部靈魂得以順暢流轉。然而,從我利用《貸睛行》中「施行者約有兩日時間能行動至完成儀式,儀式間,其行將不會受到任何阻礙」這條規則的經驗來看,「睛光」這東西只是儀式的一部份,目的是要吸引他人——藝術家,或某個願意用生命燃燒熱情的人——與睛光共鳴,使他或她以生命復甦城市荒蕪之處。
《貸睛行》不斷進行,我就不需要吃、喝、拉、撒、睡——但滿足「正常」生理需求,會使我感覺像普通人類,也會對儀式進行有所幫助。我試錯了好一陣子,才理解這個儀式有多異常。睛光竟能被給予綾這種,近乎瀕死之人,我是現在才知道⋯⋯若讓她也參與《貸睛行》,會不會也消弭她的病痛呢?
「我剛說過,我成為米林閣拉市的守護者。其實啊,當守護者不需要睡覺,在城裡四處逛逛巡邏時,也能順便用隨身聲寫器。邊走,邊寫點東西,走著走著就不會累了。妳能在我們走去上游時,和我聊天,效果也差不多吧?」
「如果你真的是魔法師,為什麼不直接給我施點法術?」
「我只能讓這座城市看起來不會那樣衰殘而已,還有外加,只要我繼續散步就不會疲倦,也不會需要睡眠。」
「如果我也成為守護者,這樣健走,就會更健康了嗎?」
「大概不會吧。」我將手收回。綾雙手稍微暖了起來,已不再顫抖。她的疑問也讓我不禁納悶,我上次睡覺是什麼時候的事情了?「妳現在看起來最需要的,應該是休息吧?而且,若無法完成儀式,就會有懲罰喔。」
「懲罰是什麼?不太激烈的話也許我能試試看。」綾眨眨眼,雙膝朝我靠攏。
「儀式是要平均分佈城市的生命力,得用雙腳走路、不能使用工具代步,從商品四周一直走到城裡某些被遺忘、被遺棄,衰殘、衰敗之處。弱勢失敗,就會變成活生生的雕像,無法死去也無法行動,看著米林閣拉市慢慢走向衰亡。」
「那還是算了吧。你以前想像力和唬爛腔有這麼厲害嗎?」
「那不是重點吧。重點是,我知道要怎樣才能走到寒緋那邊,現在已經這麼晚了⋯⋯」我看向手錶,假裝時間對我而言還有普通意義。「如果妳想要的話,我可以陪妳走過去。」
「你不用回家?」
「剛就說了,這是我的夜間散步時間。說起來,那裡也沒有連接上行人帶,因為那裡的公寓沒多少人住了。」
綾深深呼吸一口氣,非常習慣性托起手肘,讓自己左手食指中指能按著喉嚨氣管旁、測量心跳。「也許,可以走走看吧?」
落日彩霞短瞬的絢彩後,整個夜空會變成灰暗壓頂,然而,各個繭型巨大建築窗口和煙囪所噴射出的光害,使天空有如淺紅的眼珠,沒有任何瞳孔、更不會眨動,而是單純、不斷盯向地面。
我和綾走上蜿蜒小道。這裏和剛才一路下坡的筆直路線不同。我說,這些高聳肥胖的建築,就算按照建造的年代來看,外觀也不會有任何設計變化——工廠的本體外側都會有層石磚外壁,外壁上都會塗水泥漆。隨時間推移,水泥漆會先剝落,石磚暴露在外的話也會被煙氣腐蝕,之後,就可能會讓建築的鋼筋本體凸出殘垣,所以大多數工廠建築管理人都會不斷更新水泥漆。至於那些殘破不堪的建築,則可能是因為,工廠本身已經沒在運作,自然而然,不會有人繼續想住在那些工廠底下的公寓區,然後管理人就不會有錢維護工廠。或者,根本就不會有管理人了。
「工廠為什麼要運轉呢?」
「不就是因為即使入夜了,還是需要工作啊。世界這麼大,就算米林閣拉市入夜,其他還是白天的地方就得要工作吧。」
綾說,她從來都沒有聽說過米林閣拉的遠洋貿易、物資流動之類的新聞,就算米林閣拉的工業產品都以海外輸出為主,而我們小時候到港口看風景,已經是數年前的事,在她的模糊記憶中也從不曾看過貨櫃船出海、入港。綾繼續說著話,我沒想回答,不是因為我沒辦法清楚說出我公司的那些客戶與廠商到底是誰、住在哪裡、有什麼樣的故事、為什麼需要我們的特製螺絲⋯⋯我沉陷在思考之中,是因為腦子糾結著、想不出「生活一直以來,都是如此」以外的答案。
綾講著她的天馬行空,我則分享我的廢墟探險,還有我所見過的許多奇異社區復甦計畫,或藝術創作,就像,之前那在工業城市裡誕生的原始林。《貸睛行》不曾向我展示城市某處為何死去,但《貸睛行》出現到我面前——我到現在依然記得幾年前,拜訪一家因店主過世而大批清倉的二手書店,在一本厚重、皮革書裡,拿到《貸睛行》規則的字條。
除了那小張字條,我完全讀不了那本書的潦草文字。而只要儀式不斷進行,我就不必擔心⋯⋯任何事情了,因為所有生理需求都被儀式滿足。我在心中也跟著想道:「為什麼這座城市——或城裡的某人——會希望米林閣拉的生命繼續流轉存續呢?」說不定,頭頂上那如同紅眼珠的雲朵與米林閣拉幢幢巨大工廠的束束煙囪,全都是「魔法陣」之類的東西,但這依舊沒辦法解答為何《貸睛行》會存在⋯⋯而經受癌症苦煉的綾,她那不想繼續奮鬥的心情,到底該怎麼辦才好呢。
水道旁的小販愈走道上游,便愈常出現。綾現在才發覺,原來有人真的會在水道上開船,將一些被認定為淘汰品的食物,拿到街上來賣——沒有多少人會走在人行道上,但還有些老人們依然記得往昔的生活方式。人們在路邊買菜,買水果、雜貨等等日常生活所需。上游的農場牧場自然沒辦法和市中心的工業化食品廠競爭——如果真的有那種工廠存在的話——但,淘汰品不賣白不賣,也能便宜回饋上游稀疏散居的鄉里老人們。
我為自己和綾,一路上拿過蕉糜雪球、鹹醬烤甜肉、綜合調果汁等小吃,間間斷斷走走停停,獎勵她的額外運動,也讓我聽聽她在南國的趣事。最後,我們就單純聊起了各式各樣的事。
綾她在南國的職場經常會舉辦聯誼,但她說,那與大學時挑對象續攤的聯誼不同,就是一群人聚集,一起玩耍罷了。
「貿易這行業裡,大家興趣都差不多。」她如此說。有些時候他們會找些自己認識,但不怎麼熟的人一起聊天。聚會組成就只有幾個選項,非常偶爾,才會有認識新朋友的機會。她是在某次登山時,碰見一個自己很喜歡的男孩子——一位小綾兩歲、與她同部門但不同小組的後輩。
隨著水道愈發窄小,也愈來愈多人出現在人行道上。有人在水道旁邊坐著,釣著魚;有人自己搬了椅子,人多了就拿出隨身桌與棋盤,下起棋。他們大都是長者,大多數人的穿著也十分隨意,像在自己家裡。水道漸漸在好幾處支岔的上游轉彎後,就變成路旁的小水溝。
我和綾都走在最大的水道——那裡一直都有至少十公尺寬,水深也至少有約略五公尺。一路上,都能看到稀疏的小販賣著不同東西,還有人在路邊拉著琴唱藝。綾十分好奇地遙望著那彷彿披著黑色長長僧袍的拉琴老人,轉頭看著我。
「要不要休息一下呢?」
「好啊⋯⋯感謝。」氣息在我開口說話時一洩全失,我在這條路上吃了這麼多東西,卻完全沒感覺身體攝入的營養有任何丁點效果。
「你的體力也沒多好呢。是不是常常來這裡玩,就會變得像老人了?」
「才沒有啦!之前根本不會這樣的。」我看了下手錶,第二根指針的色彩與陰影黯淡到我必須瞇起眼睛,才能看清楚。我有將睛光分派出去嗎?難道⋯⋯我想著:和綾接觸後,儀式將睛光視為我的生命⋯⋯這樣想,不會有錯吧?
那老人注意到我倆,誇獎著綾的貌美,想以此獻上一曲,送給揮撒青春的小倆口。綾沒有糾正他,她相當歡欣地拍手喝采,享受著老人的誇讚與欣賞。
《貸睛行》正在進行。我如此想著。
我趁著綾不注意拿出皮夾,裡面只有一張塞著的紙條,和充值到最高額度、以防萬一的行人帶通行卡。我快速掃過紙條上,我凌亂字跡抄寫的儀式規則。我早已將儀式的所有內容銘記在心,但還是想著,說不定、有可能現在,立刻想出規避儀式規則的方法⋯⋯《貸睛行》不會直接將生命力注入頹廢處,而是汲取那些,受睛光吸引的人的生命力。
綾在老人演奏完後開心拍著手。我,也跟著拍手,腦袋一片空白。晨光鑽入巨型建築間的夾縫,灑在鞠躬收場的老人臉上——他滿足的神情與臉上深刻皺紋,感覺有如一座,失卻了生命力的雕像。
「已經到早上了。」我看了下手錶,錶面只剩一根指針。
綾跟上我的腳步,邊走著,邊回頭望向我們一路爬上來的緩坡,與工廠的巨大影子:「落日和日出根本一樣啊。」
「妳是想說,日出和日落一樣,正如死與生?」
「怎麼可能,又不是中學生了。」綾擔憂低皺眉,想開玩笑似地笑起來,微笑的嘴角卻垂下:「用這樣的情感來看日出或看日落,不會很做作嗎?」
「那看寒緋花,不也一樣嗎?」
「才不一樣呢。寒緋就算死了,還是很美啊。」
「如果有機會活下去,就算痛苦,也是機會,因為如果死了,就連自己美不美也都完全無法知道了。再說,既已降生於世,活著的掙扎不也是美的一種嗎?」我感覺自己已經語無倫次,但臉頰的麻痺感使我如此回話。
「可是如果你這麼說,就好像⋯⋯活著時,只有繼續活下去的選項。你會認為這種不自由,很美嗎?」
我想回答:沒錯,因為展覽品若被放在玻璃盒內,就會有更強烈的睛光、吸引更多人觀看。綾說著自己想要美麗,想要繼續燦爛,即使只能再真正燦爛一次⋯⋯而我成為了,陪伴她一路走上緩坡濃密花林的見證人。我搖搖頭,不想如此相信。
「不,妳只是想要沒有痛苦的自由。不希望痛苦剝奪自己的自由。」我一說出口,不禁想到:綾一直都是我的朋友、我的青梅竹馬,但我真的,想為她而死嗎?是我願意為她犧牲,還是《貸睛行》要我為她犧牲呢?
綾沒有注意到我的沈思:「難道,你不是因為愛情才想說服我不要自殺嗎?」
我沒有反駁,而是沈默,整理思緒,才開口道:「如果有個方法能讓妳健康活下去,妳願意嘗試嗎?」
「對緋花來說,墜落才是健康的吧?因為花朵沒辦法像葉子一樣呼吸,而在米林閣拉的空氣裡,空間又那麼狹窄⋯⋯這難道,不就是更健康的選擇嗎?」
我們已能望見遠處水道旁,在龜裂的磚面裡有一棵顆粗大的漆黑樹幹,以及叢叢粗枝刺出的鮮紅花團,朵朵花瓣已隨著微風飄落。這邊的上游水道周圍,有不少人在舉辦賞花會,小販們推出數種寒緋相關產品,幾群老人坐在自己的毯子上、賞著花。
我們倆各喝起小杯花釀甜酒,四處走走停停、凝望這諧和而頗有詩意的風景,幾乎讓人忘卻了我們仍身處工業都市米林閣拉。
愈往上游走,樹林就愈發密集。崎嶇樹根猛突出走道,使老人們不再前行。我們最後來到,連欄杆也徹底腐朽、不留殘跡的水泥平台上,佇立在寒緋密林中。
我還記得自己來回多趟,才給這地方注入夠多睛光,讓這片區域勉強能允許人類行走。
「謝謝你的導覽,還有,那⋯⋯謝謝你陪我走來這裡。」綾說著,雙手緊緊抓住我扶持的手,但她已經擠不出更多力氣了。
我在她在踩入水下階梯時,幫綾穩住身子,直到我們半腰都滲入水中。綾漂在水面上,我從水泥平台上撈起幾把花瓣,灑在她周圍,遮掩她的身影,但其實在推走綾後幾秒鐘,落花便已幾乎要淹過她了。
我小跑步追著綾,閃過好幾個拄著枴杖漫步的人,避開那些與酒友一起坐在地上賞花擋路的人。花瓣愈疊愈多,似乎減緩了她飄動的速度。我能感覺到,她身上的睛光正在迅速消失——《貸睛行》的儀式效力不斷減弱。我一陣暈眩、眼睛忍不住重重一眨。
對呢。
這就是,疲倦感應有的樣子。
我心臟狂跳,鞋子在腳步下濕黏地啪嘰啪嘰響——這又使我更加煩躁。
我到底該怎麼辦?我怎麼可能會知道這種事該怎麼呢?下坡的急奔頂撞,使我雙腳痠痛不已、喘氣到喉頭乾燥而近乎冰冷,我不得不停下來時,雙腿一軟而不穩,使我摔在地上、劃破了無力顫抖的手掌。
鮮血留下手掌邊緣,滴落地面。啪嗒,摔散。「所以這就是想阻擋死亡的心情嗎?」我幾乎破聲大笑,大口呼吸後感覺心臟有如墜落腹腔。
我咬破手指,劇痛抽竄上我的手臂。我咬緊牙關忍著痛楚,口中的鐵鏽味與血腥味散開。簡單的圓,由我的全心全意所勾勒。然後,另一隻手顫抖、抽出皮夾,但軟弱無力的手沒拿好,皮夾翻落到血圈上,儀式的字條掉出,沾上血液。
「我希望,能讓她——讓綾——繼續行走,繼續愛著她所離開的家鄉。」我吞了口氣,眼前已經是一片昏暗:「我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做才好,所以,全部都獻給綾吧⋯⋯」
一股強風灌注綾的胸口,她嚇了一跳而背脊重重撞上某個堅硬的平面。
綾慌張睜眼,發現自己躺在血紅的複雜方陣之中。她坐前身,感覺自己的動作迅速得,使她些微頭昏。綾轉頭望向四周、發現自己在岸上時,卻缺乏了時時遮隱住她的思緒的感冒暈眩。
而那陪她走了整夜的男孩,猶如垃圾般、沈浮在水面下,順著水流花叢飄至遠處的水道口。他前方不遠處有個排水孔打開,噴出烏褐色的猛束水柱,淹過他、完全遮掩住那死寂於水道裡的身影。
綾撿起身旁一張紙條,發現了男孩的字跡與血跡。綾感到胸口緊緊一揪,但那與她如玻璃崩裂的沈痛不同。
而在她抬手輕觸自己胸膛時,綾不明白自己的身體不適到底為何消失。她滿是淚水、花和水的雙眼眼眶向下一望,發現左胸前,多了一隻閉起的眼睛。
ns3.23.102.192d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