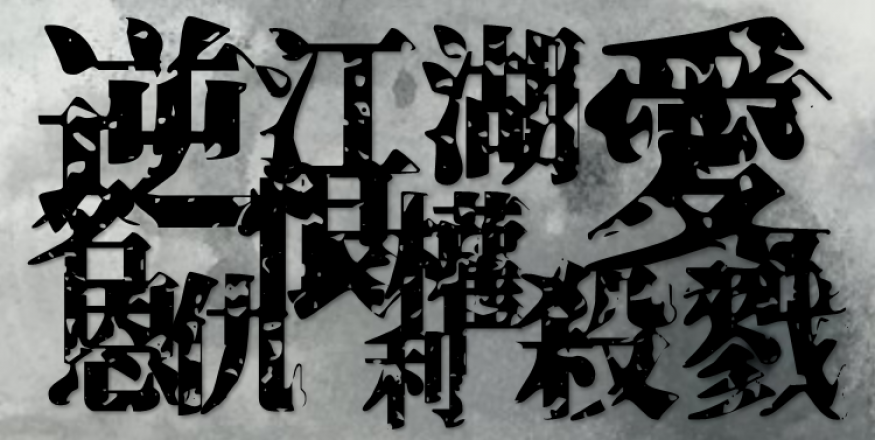「三両,這是好事嗎?」蔡老爹憂心忡忡,在兒子表明離家之意前,已再三詢問。
蔡三両整理好行藏包袱,眼神展現堅定意志,應道:「當然是好事啦!爹,我今年已經十七歲了,我不想再在這種小鄉村浪費一生,我要去名門大派學武,然後闖蕩江湖,幹一番大事業!」
蔡老爹搖頭嘆氣:「安安穩穩不好嗎?外頭是很危險的,一不小心,就會丟了性命。」
蔡三両笑道:「哈,爹你以為我會怕死嗎?即使要死,也要死得有意義,而且我不覺得自己會死,在我成為名滿天下的大俠之前,我一定不會死!」
蔡老爹深知兒子不甘困於這小小茅屋,既然去意已決,身為父親也只好低頭不語。
蔡三両輕拍父親肩膀,道:「爹,你放心吧,我一定會回來的。」
目送兒子遠去,蔡老爹心中一陣刺痛,他不求兒子成為甚麼響噹噹的大人物,只望這唯一親人當真實踐承諾,回家相聚。
時光飛逝,轉瞬三年,因為蔡老爹目不識丁,故蔡三両從沒寄書信回來,只會寄來一些新衣物,好等父親知悉自己安然無恙。
蔡老爹生活如常,在屋前小田務農,每日抬頭望天,祈盼兒子早日歸來。
這年初春,祈盼成真,蔡三両當真守諾回家,但蔡老爹倒不太認得兒子。
「三両,怎麼你當了和尚?」蔡老爹還希望兒子會娶妻成家,望向兒子身穿金色僧服,還有那剃得光溜溜的頭頂,希望頓然粉碎。
蔡三両摸摸自己的禿頭,道:「爹你有所不知了,我這幾年來排除萬難,吃了很多苦頭,才能夠加入金林派,成為登堂弟子,金林派是『翹楚六派』之一,在武林中可是鼎鼎有名的佛門大派哩。」
蔡老爹不懂甚麼武林、江湖,甚麼六派他更是聽得一頭霧水,只能問一句:「三両,這是好事嗎?」
「當然是好事啦!爹你不懂武林的事也不要緊,你只要知道,你兒子我成為了很利害的武僧,以後無人可以欺負我、看輕我,這就足夠了。」
蔡老爹仍是一臉憂心,道:「但是,你想當一輩子和尚嗎?無妻無兒又好像……」
蔡三両如夢初醒,始明白父親所憂為何,便道:「哈哈哈哈,原來爹你是擔心這件事,爹你有所不知了,金林派不同其他佛門,雖然當了和尚,但我們登堂弟子仍可娶妻生兒,也不用守甚麼清規戒律,方丈常說『佛在心中,不在戒中』,所以爹你大可放心,我定會討個好老婆,生十個八個兒子的。」
和尚可娶妻生子?倒是聞所未聞,但管他的,蔡老爹得知希望沒有消失,憂慮立即消散。
「爹,我買了些酒肉回來,今晚陪你好好吃一頓,明早就要回去了。」
蔡老爹有些驚訝,道:「你才剛回來不久,這麼快就要走?」
蔡三両解釋:「武林規矩是這樣的,每派登堂弟子必須留守派中,隨時聽令,如有私事外出,必須先得師門允許,且在預定限期前回去,否則必受處罰。」
蔡老爹詫異道:「啊,這樣你要趕緊回去了,千萬不要受罰。」
父子倆歡聚一夜,翌日早上,蔡老爹再次目送兒子遠去,但今次蔡老爹再沒感到心頭刺痛,他深信兒子必會再度歸家。
日月輪替,又過五年,期間蔡老爹收到兒子寄來愈來愈多新衣物,有些質料上乘,明顯價值不菲。
蔡老爹感嘆外頭真是超乎想像,當個和尚也賺得了大錢,當日兒子堅持外闖,回想起來是相當正確。
這年炎夏,蔡三両再度回家,但蔡老爹看到兒子,又是大吃一驚。
「三両,怎麼你會還俗了?」蔡老爹倒不是希望兒子當和尚,但見兒子長回頭髮,身穿奇異服裝,頓感莫名其妙。
蔡三両咧嘴笑道:「哈哈哈,爹,我不只還了俗,還當了官呢,你看我這身官服,威風嗎?」
「官服?你不是去當金甚麼武僧嗎?怎會由和尚變了官的?」蔡老爹如陷五里霧中。
蔡三両道:「是金林派武僧,不過已經不重要了,甚麼武林門派現在對我來說,都再沒有任何意義,這幾年我想通想透了,人生在世,還是權勢要緊,武功甚麼的有個屁用,我有幸結識到一位達官貴人,多得他引薦我加入禁廠,令我安心叛出金林派。」
「禁廠?你是說那個特務組織嗎?聽說他們權勢很大,當今皇帝也很器重他們。」蔡老爹雖不懂武林之事,但權傾天下的禁廠大名,連他這種鄉下人亦有所聽聞。
蔡三両滿臉得意道:「就是那個禁廠,哈哈哈,爹你不認識金林派,反而認識禁廠?這證明我的想法沒錯,在武林中打滾,假如不能晉身為入室弟子,終究不能出人頭地,倒不如改投朝廷,替朝廷幹些粗活,還有更多榮華富貴在等我呢。」
蔡老爹認識禁廠之名,只因禁廠名聲太壞,當今世道,無人不知朝政腐敗,即使是鄉間農人,也曾聽聞禁廠如何濫權自肥、殘害忠良,但見兒子說得眉飛色舞,蔡老爹亦不好說出心底話。
蔡三両說到高興處,在腰間取出一塊令牌,上面刻有一個禁字,說道:「爹你看看這塊令牌,加入禁廠,成為八目禁衛之後,我就得到這身官服及令牌,任何人見到都要退讓三分,是不是很威風?」
威風與否,蔡老爹實在不敢回答,只能問一句:「三両,這是好事嗎?」
「唉,爹你真是的,這怎會不是好事,你知道嗎?按照武林規矩,我叛派出逃,就是淪為叛派弟子,一般來說,金林派是會派人捉我回去審問,最嚴重是會廢去我全身武功,要我變成廢人。」
蔡老爹一聽「變成廢人」四字,不禁臉色大變,道:「這這這……這該怎樣辦?三両你不能變成廢人呀。」
但蔡三両顯然毫無懼色,道:「爹你放一萬個心吧,我剛才都說是『一般來說』,但你兒子我當了八目禁衛,就不是一般人了,金林派根本不敢追究禁廠中人,何況,那群賊和尚都是貪財如命,當日我親自奉上一疊銀票送給方丈,他們自然不當我叛派是甚麼一回事,甚至替我舉辦退門禮,正式視我為榮休弟子,脫離門人限制。」
蔡老爹聽兒子說得信心十足,彷彿所有麻煩事都已經擺平了,心裏不禁抹一把冷汗。
「爹你想想,我如今只是禁廠內一個下級小官,那些武林中人已經忌我三分,他日我成為大官,甚麼絕頂高手、一代大俠,看到我都只會逢迎諂媚,這是多麼痛快的一回事。」
整整一夜,蔡三両都在訴說他的鴻圖大計,愈說愈是高興,又說只要討得督主歡心,自然大權在握,飛黃騰達。
蔡老爹感到兒子有些改變,但他是個鄉間農人,哪懂甚麼朝廷大事,兒子加入禁廠是好是壞,他實在不懂分辨,反正兒子高興就好。
數日之後,蔡三両接到快馬傳訊,需要趕回禁廠覆命,他曾勸說蔡老爹不如隨他同行,他新購的宅院也不算小,父親大可與他同住。
但蔡老爹堅決不從,始終這小小茅屋,是由蔡老爹與亡妻共建,充滿多年回憶,而且他不願為兒子帶來任何不便。
最終,蔡三両明白父親想法,就不再勉強,並策馬離去,蔡老爹第三次目送兒子,這次感到兒子已經長大,應可照料自己,但人人皆說官場兇險,心底不禁仍有一絲憂慮,不知他下次回來,會在何年何月?
斗轉星移,再過七年,期間蔡三両一直沒有回家,但卻派來一名部下,每隔數月探望蔡老爹一次。
據此人說,蔡三両受禁廠督主器重,常常委以重任,故難以抽空回來探望父親,故命人前來替父親修葺茅屋破爛處,並送上各式名貴補品,以盡孝道。
蔡老爹多年來習慣粗茶淡飯,倒不喜好吃甚麼補品,故兒子所贈之物,他都只是屯積家中一角,他心中所望,絕非任何名貴物品,而是能夠再見兒子。
這年深秋,蔡三両終於回家,這次不再是他獨自一人,而是兩個人,另一人正是蔡三両未過門的妻子。
這名女子相貌娟秀,而且舉止充滿儀態,似非布衣人家,她陪伴蔡三両到茅屋拜會蔡老爹後,蔡三両便命人先送她回客棧休息。
「三両,怎麼你想成家立室,也不早點找人告訴爹呀?」一直期盼兒子娶妻,蔡老爹當然希望儘早得知。
穿上華美官服的蔡三両應道:「這麼重要的事,我當然要親自告訴你,怎可能假手於人?」
不管如何,兒子快要成親,蔡老爹當然高興,只是有一事情,實在不吐不快:「對了,剛才未來媳婦……她只是陪你進來,向我說了幾句問候說話,便匆匆離去,她是否嫌棄阿爹和這裏?」
蔡三両急忙搖頭道:「當然不會,爹你別亂想,她只是不慣遠行,這幾日來舟車勞頓,她剛好有些不適而已。」
蔡老爹狐疑道:「……真的嗎?」
蔡三両舉起右拳作勢道:「哼,她敢嫌棄你的話,我便一拳送她往閻王殿報到,所以爹你就別多疑了,好好準備,下月初一來看我拜堂成親吧。」
不想兒子為難,蔡老爹亦不再追問下去,反而想知道兒子近況:「這七年來,你過得怎樣?」
蔡三両沉默半响,緩緩應道:「我已經晉升為禁廠八組其中一組的組長,這七年來,我做了很多事,樹了很多敵,賺了很多錢,得了很多權……」
看見兒子一臉沉鬱,蔡三両一如既往,問道:「三両,這是好事嗎?」
蔡三両緊閉雙眼,然後猛然睜開,微笑道:「好事,當然是好事,我確實做過很多好事,我問心無愧。」
蔡老爹輕拍兒子肩膀,道:「嗯,這樣就好。」
蔡三両忽然站起來,然後命人拿更多名貴珍品入屋,並道:「爹,最近我們換了一位年輕的新督主,這位招大人……唉,說來話長,總而言之,我要花更多力氣服侍他,或許,將來會更少回來了,這些東西,你慢慢用、慢慢吃,不夠的話,找人通知我再送過來,好嗎?」
蔡老爹明白兒子心意,雖然他對這些東西完全不感興趣,但仍頻頻點頭,表示滿意兒子所贈之物。
是夜,蔡三両並沒留下,而是返回客棧陪伴未過門妻子,蔡老爹沒有怪責兒子,只望二人感情和睦,即使不管他這老頭亦可,當他第四次目送兒子,所見那遠去的身影,就像一頭帶傷的野獸,步步躊躇,似是不知該往何方是好。
年復一年,已過三載,自從辦完喜酒,蔡老爹就再沒見過兒子,期間只得蔡三両派人報訊,說他喜得龍鳳胎,蔡老爹已當上爺爺。
蔡老爹雖然滿心歡喜,但仍不敢遠赴兒子家中打擾,雖然兒子一直替媳婦說好話,但從喜宴當晚媳婦對待自己的態度,可知她絕不情願再看見這個糟老頭。
縱使希望一睹兩位孫兒容貌,好好抱起他們,蔡老爹仍牢牢克制自己,只盼有朝一日,蔡三両會攜帶兩個小寶貝回來探望爺爺,他就於願足矣。
這年寒冬,蔡三両沒有回家,但卻有一人不請自來。
當晚該是全年最冷一夜,寒風凜冽,雨雪同降,如此天氣,像這種環境惡劣的鄉間小村,理應不會有外人到訪。
但一個陌生男人,卻輕敲蔡老爹的家門,意圖入內,蔡老爹最初不願,但此人說自己只為避寒而來,並無惡意,蔡老爹從門縫見他渾身濕透,也不好意思拒絕,唯有開門接待。
此人滿面鬍子,背負一個如人般巨型的大竹桶,蔡老爹總覺得此人十分古怪,但過門也是客,蔡老爹亦奉上一碗熱茶,以助此人驅寒。
蔡老爹見他坐下,喝了一口茶後,便沉默不語,整個人像靜止下來。
屋內一片寂靜無聲,屋外風聲呼呼作響,蔡老爹感到有些不安,故主動攀談:「這位大爺,這麼晚了,又是天寒地凍,你怎麼還在這種地方,是趕路嗎?」
陌生男人放下背上大竹桶,道:「沒錯,我在趕路,只為遵守一個承諾,我有為老丈你帶來麻煩嗎?」
蔡老爹見他有所回應,稍為放心,續道:「沒有沒有,我一人獨居,見田比見人多,在這種又寒又冷的晚上,突然有人來給我作個伴,或許是一件好事也說不定。」
陌生男人問道:「好事嗎……對了,老丈你一人獨居,那你的家人呢?」
蔡老爹苦笑應道:「他們住在很遠的地方,我也不好意思打擾他們,你看看我這副模樣,出外只會丟人現眼,那大爺你呢?你的家人也在很遠的地方嗎?」
陌生男人低頭道:「是,他們在很遠很遠很遠的地方,恐怕今生亦難以相見。」
蔡老爹聽他聲音有些凄苦,似是暗藏悲痛之事,故不敢再問。
陌生男人抬頭問:「老丈,你為何不問下去,為何我的家人住在那麼遠,有甚麼原因?」
「呃……這……這個……」蔡老爹見他神情肅穆,一時之間,不知如何回應。
陌生男人沒有理會蔡老爹,繼續說道:「因為一個惡人,令我和家人陰陽相隔,今生今世不得再見,老丈,你說世上有比地府更遙遠的地方嗎?」
「應該……沒有吧?」越聽越古怪,蔡老爹不敢不回應,但也不敢回應太多,生怕說錯半句,會惹怒此人。
陌生男人突然站起來,從大竹桶內拿出一袋小包袱,問道:「老丈你知不知道,那惡人叫甚麼名字?」
蔡老爹不斷搖頭,他心底感到極為不妥,頭上冷汗直冒,心底不斷自問這男人是誰。
陌生男人將小包袱掉到桌面,布塊散開,一個熟悉面孔收入蔡老爹目光中,他自然回答了陌生男人的疑問:「三、三両?」
蔡三両的人頭,如今就在桌上!
那毫無生氣的雙眼,正望向父親,日夜期盼的再會,可沒預計以這種方式出現,蔡老爹已嚇得目瞪口呆。
一個怎麼夠?陌生男人從大竹桶拿出一個又一個小包袱,逐個掉落桌面,有些則滾到地上。
雖然只見過兩次,但蔡老爹清楚認得,其中一個女人頭顱,正是那一臉高傲的媳婦!
還有,蔡老爹認出,很多是喜宴當晚所遇之人,都是媳婦的家人,一個又一個人頭,散落茅屋四周。
「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蔡老爹嚇得跌倒地上,難以相信眼前所見。
陌生男人臉如死灰,問道:「他們是你家人吧?」
蔡老爹沒有回應,只顧不斷搖頭,重覆同一句話:「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剛才你說,容我進來是一件好事?哼,你知不知道,你兒子才是好事多為,對了,還有這兩個,也送給你。」
陌生男人拋出兩個小圓球至蔡老爹身上,但他沒有接應,只等兩個小球撞到其身,反彈落地。
蔡老爹望向兩個小圓球……或許,應該說是兩個小人頭──龍鳳胎的人頭!
蔡老爹雙眼,差不多凸出至跌出眼眶,嘴巴完全合不起來,亦發不出任何聲音,腦中剩下一片空白。
男人從大竹桶取出一柄斧頭,道:「老丈,你別怪我,我曾在我一家十八口墳前起誓,一定要他全家填命,現在,只欠一個而已。」
蔡老爹完全弄不清,到底眼前發生何事,只見斧頭反映的燭光,正照向自己的老臉,他不用再問兒子,也大概知道,這不是甚麼好事。
茅屋之外,風聲仍是呼呼作響,不論好事壞事,似乎再無人可知。
ns 15.158.61.20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