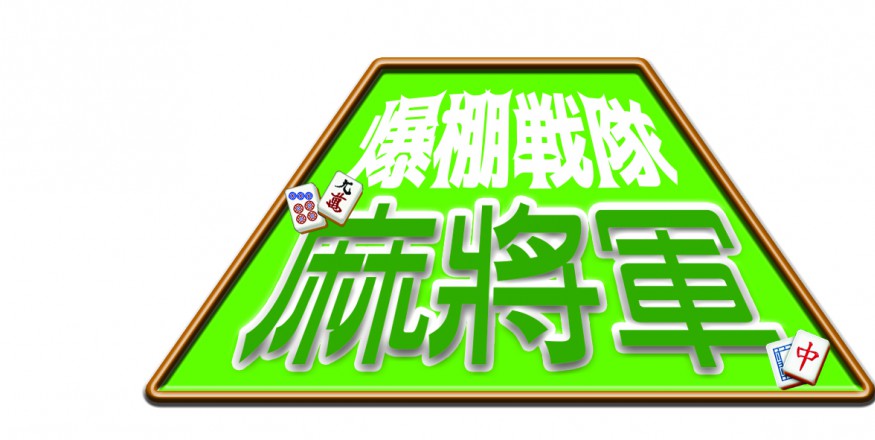之後一天,洪萬被那老人叫了去他家裡。面對著一大堆問號的洪萬,雖然有點心不甘情不願,仍然到達了那人所住的地方。
那人自稱林岭六,他所住的地方是在金港的舊區中一個寮屋區,他在那寮屋區的入口帶了洪萬入去。洪萬家住政府廉租「公屋」,雖然地方也很不堪,但他萬料不到林岭六所住的地方更差,只有他家的四份一地方,廁所和洗澡間也要和人共用,更重要是沒有冷氣,在這暑熱的夏天簡直是要命!林岭六把他的屋頂的一塊鐵皮拿了下來,讓空氣可以進入到屋內,但是幫助不大。洪萬已經汗流浹背了。
「好了,」林岭六說:「再一次自我介紹,我係林岭六博士,你可以叫我林博士。」
說著把一張印刷倒也精美的卡片交了給洪萬,上面寫著「金港大學 考古學系教授 林岭六博士PhD」。
洪萬心想:「係唔係呀你,金大?」金港大學 Kam Kong University 是全港數一數二的大學。
林岭六好像看穿了洪萬的心思,說:「響果度仆心仆命的做研究,政府一聲多謝都無就把我的研究成果就拿走了。還說我是精神病,把我趕了出來。」
洪萬心中滴沽。
林岭六搖了一搖頭:「唔好講我的事了,講返呢個娜馬吊的事。」說著把另外幾隻和洪萬持有的麻雀一樣的牌出來,一樣的異光閃現,卻是三索,七索,和五筒,六筒的牌。
他說:「呢D娜馬吊是上古傳下來的神物,具體已經難已考究,關於它的傳說亦有很多,但最可信的,仍然是說這是女媧補天之後用剩了一塊彩石,於是被人把它用來製造了一套馬吊,亦即是麻雀出來,具有神力,能以之對抗邪魔。」
說著把這些牌交給洪萬:「你攞住睇下。」
洪萬拿著這些牌,立刻覺得感覺無比暢快,連暑熱也感覺不到了,不過其反應卻不像是那天那麼強烈。
「咦,感覺好像有些不同。」
「果然是,」林岭六說:「雖然都是同一套的麻雀,但係每一隻所含的能量也有所不同, 唔係每個人都能用得對頭,好像我這般,我就每一隻都只能感應到能量,而不能像你那樣使用出來。」
「不然我早就把那些怪物打走了。」說著乾笑了一聲,好像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所說的一樣。
洪萬覺得這個人很奇妙,一時說的很有道理,一時又有點奇怪的舉動,不過他現在確信這個人倒也不未至於是神經病的,只是有點古怪就是,大概是讀書讀到傻了。這是他對一般「讀書人」的感覺,就是讀書會讀到傻的。
洪萬說:「講起唻,隻怪物又是什麼一回事?」
林岭六說:「果個人係被妖魔組織『惡牌黨』所操縱左,佢地某程度上都係受害者來的。」
他停了一停,又說:「至於『惡牌黨』的來歷亦都不明不白,我研究了這方面的資料有好幾年,這似乎是近幾年才突然出現的組織。我亦未摸清他們的底蘊,只知道佢地一樣在搜集娜馬吊,進行邪惡活動。就如果日果隻雞妖就係一個好例子,佢就係被人以娜馬吊既力量加上妖法控制心智,於是變成一隻怪物。」
洪萬回想起那天那隻雞妖回復成人時,然後新聞報導說他是虧空公款四處躲避的銀行高層,夾雜了多個罪名後於是在麻雀館躲避,被人發現出千之後一時崩潰,不知為何變成了妖物。
「而我想你幫我做的,就係要搵出呢些娜馬吊,免於落入惡牌黨手中。與此同時,都希望你可以幫我搵到可以使用娜馬吊力量既人。」
其實洪萬都已經知道大概是要這樣。他也有看過漫畫,卡通等的,情節不外乎是這樣子。所以他也不怎麼震驚,說:「咁要點做?」
林岭六對他的不震驚也並不震驚,淡然的說道:「一般來說,娜馬吊比較容易出現於有麻雀打的地方出沒,使用既人亦然,都比較容易係會打麻雀既人。所以我才會在鴨記找到你,而且在眾多麻雀高手當中,娜馬吊也對你的反應比較大,所以我才會找到你。」
洪萬想想也很合理,說:「但係咪我地去麻雀館就可以?昨天被那雞妖所弄消失的麻雀和麻雀枱都沒有變回來,我還以為只要把那雞妖收拾便會令麻雀枱變回來,今天舖頭也沒開門。」
林岭六解釋說:「咁係因為那些妖力既主人並非果隻雞妖,而係背後既幕後黑手,亦即是惡牌黨既首領級人馬。要將佢收拾左才能把麻雀變回來。」
洪萬說:「豈有此理,咁咪即係話我地舖頭無得再開門?」
林岭六一聽此言,立即說到:「對極對極,這可是關乎到你的生計的,你會幫我個呵?」
洪萬感覺到這番言語中的一點虛偽,說:「你只係想找人幫你吧了對不對?」
林岭六說:「反正舖頭不開你也沒事做對吧。」
洪萬沒他好氣,正好有事,離開了那爛鐵皮屋。
他平常不上工就會去練拳,於是回到去他所屬的「田岸天」武館去,他對練習武學倒也不疏懶。他和一些師兄弟練了一下套拳,便和平時一般打算離去。就在這時,一把聲音叫住了他。
「喂,洪萬,又去做老千了嗎?」一把清脆但略帶粗魯的聲音說。
回頭一看,原來是陸素玲,學生時代已經是他的死對頭,陸素玲花名「陸索」,每年都做班長,洪萬則是班上的茲事份子。兩個人不止住在同一個屋邨,洪萬為練武而上了這所武館,偏偏是陸索的親戚所開的。甚至自學校畢業後,洪萬繼續做些偏門工作,陸索卻上了大學,更考上了警察。
「小心啦,總有一日拉你去坐花廳。」陸素玲說。
洪萬正不是這個心情,沒有理她的單打。只說:「多得你唔少啦,而家無得做啦。」說著便走了。
陸素玲也沒有理他,逕自繼續練習。素玲自少已在這男性為主的拳館中練拳,所以亦較男仔頭。
素玲雖然陽剛氣頗重,但五官端正,明眸似星,加上整天練武運動所練出的美好身段,古銅色皮膚,亦不失為一位美人。某些同袍和這兒練拳眾也經常對她示好。
對於這些好意,素玲沒有什麼興趣,一律婉拒,日子長了,一點點煩厭卻是一定會有的。可是陸索有留在「田岸天」的理由。因為這是她爸爸的朋友田殷明所開的武館,而且有幾個同袍也在此練習。叔叔很照顧她,和同袍一起練習也有助工作關係,所以也令她亦很常在此練習。
今天是她的休息日,練了好不長的時間,忽然電話響起,是她媽媽打來的,說:「你婆婆又發作啦,妳快D返嚟啦。」
陸索立時衣服也不換,拿起手提包就快步衝回出武館回家。因為武館在街頭,而她的家就在街尾。平常她也是回家才梳洗的。
一回到家中,一張麻雀枱已開好了在等待素玲。沒錯,婆婆是麻雀癮又發作了,所以素玲要立刻回去。醫生說婆婆患上了非常旱有的一種老人痴呆,癮起了不打麻雀就會鬧情緒,開始亂丢家中的物件。媽媽和婆婆,還有鄰居的黃師奶已經在等了。黃師奶平常也常過來幫忙打牌,素玲和媽媽也很感激她,因為其他的鄰居都被婆婆偶爾發瘋嚇怕了。
素玲立刻便坐下開局。打了不一會,素玲發覺黃師奶今天老盯著她看。媽媽也察覺到了,見素玲身上還是那套練拳服,只有一條短褲和運動用胸罩,雖已穿上了外套,但依然不太得體,便說:「女呀,妳成身汗咁,去換過件衫先啦,冚牌先。」素玲本身不太在乎這些,但媽媽叫她也會聽的,便站起來回房間。豈料黃師奶卻說:「咪係,女仔人家,成日著到咁少布響條街跑來跑去,都唔知搏乜。」
黃師奶偶爾也會有些這樣的說話,不過素玲知她人是沒什麼的,偶爾是會有點說過份,但素玲都習慣了,所以素玲笑一笑就入房間換衫了。不過在房間換衫中,卻聽到黃師奶向她媽媽抱怨說:「成日都叫你要教下個女架啦,成日著到坦胸露臂在男人堆入面,話就話練拳喎,響裡面依依泣泣都無人知架啦。唉,無老豆教就係咁架啦!」
這句說話觸動了素玲的神經,她怒火衝冠,直衝到來黃師奶的前面,喊說:「我有無老豆關你咩事呀,呢D係我家事,唔駛外人操心!」可能是她的職業習慣,她說這些話的同時,把身軀靠得很近,居高臨下的看著黃師奶,而黃師奶的面前正對著她的胸口,她說:「做咩呀,而家胸大大晒呀!?」素玲本身已怒氣騰騰的,說話也失去分寸:「難道似你白板咁平又好嗎?」
黃師奶一聽這句話,大受打擊,一眶眼淚隨即湧出……說:「嗚呀,你地個個都只識睇外在。我憎你地!」說著她一怒把麻雀枱打翻,而這些麻雀和枱竟然憑空消失了。她的身體也驚現恐怖的變化,她的身體變得儼如一個卡通人物一般,不過毫不生動,像個紙樣一樣平。她的四肢和頭髮等都變成了大少不同的紙條。
媽媽十分恐懼地攬著婆婆退避開去,素玲也是不知所措,但是黃師奶…不,這隻紙妖,已經向她攻過來了。由於紙妖現在輕得緊要,所以她的觸手過來的速度快了不少。她圍著素玲飛了幾轉,立時把她的衣服和皮膚都割破。
素玲一時也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不過見這紙妖只圍著她飛,而家裡又有婆婆和媽媽,靈光一閃就衝出門外,那婆婆和媽媽就會安全了。
她住的是一種四方型的大廈,中心是空的,住宅單位分佈在四邊,而樓梯和升降機則分別在兩個對角。她衝出門口,紙妖正跟著她。這大廈她從少就在這裡居住,知道不少秘道,她衝到附近李師奶的單位的門外,有條繩子綑在外面的欄杆,是街坊們用來晾大被的,素玲拉了幾拉覺得穩陣,於是拿著繩子的一頭一躍而下。她藝高人膽大,從七樓一躍而下到四樓,卻一點退縮也沒有。她在四樓剛好找到另一條晾衣縄,一個翻身再落到一樓才著地,然後就一直跑到地下跑出這大廈外去了。
她看到紙妖想隨著她一跳下來,但由於它的身體是一片紙,所以在高處飛出來反而真的像隻紙鳶一樣在空中飄著。正好給了素玲少許的時間去回氣和想辦法。
她回想了今天早上說麻雀館有怪人搗亂,所有麻雀離奇消失了。但她當時不以為意,以為只是幫派衝突。最後聽說在場人事說有一個穿紅色緊身衣的傢伙出來打倒了妖怪,都不大相信,但是現在想起來,就不由得她不信了。於是,她想到了洪萬這小子。
她於是奔跑到那小子住的那棟樓去,奇就奇在,正當她跑過去,洪萬竟然就跑出來了。洪萬看了她一眼,她還來不及發聲,逕自跑往她住的那棟樓的位置。她也搞不清楚是什麼一回事,唯有追著他跑回去。
ns 15.158.61.17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