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暗的白色大床上,傳來少年苦悶的啜泣與喘息。
縱然已經經過兩、三個小時的蹂躪,壓在他身上的男人興致卻未見消退。潔白的床單上此時沾滿了雄性氣息濃烈的體液,間或夾雜著鮮血的殷紅,而少年剛才噴薄的欲望再一次覆蓋上舊的殘跡,此刻已十分虛弱與稀薄。
少年並非渾身赤裸,他的上半身穿著不合身的寬大襯衫,被疼痛的冷汗浸得溼透,少年纖瘦而骨感的身軀透過單薄的布料,完全曝露在男人露骨的欲望下。
男人和少年的下體還相連著,男人巨大的肉楔侵占著明顯不合尺寸的穴口,異常的紅腫和撕裂傷滿布著少年最私密的部位。然而這幅淒慘的景象似乎激不起男人的半點憐憫。少年只來得及低低地嗚咽聲「不要了」,單薄的肩膀再次被男人抓起,這回整個人被翻過來,正面朝上,被迫面對著囚禁他已多年的男子。
男子俯下身來,隔著衣料親吻他的乳尖,鬍鬚粗糙的觸感刺激著少年脆弱的神經,少年痛苦地張口喘息,但唇瓣很快也被奪去自由,被男人的舌頭禁錮住。
男人再一次挺腰,折磨少年許久的東西再一次深深埋入尚未成長完全的身體。少年咬住牙關,緊閉著眼睛,想藉此來減緩異物深入體內的痛苦,但無濟於事。男人的硬熱毫不留情地撐開少年的內壁,折磨著少年最脆弱的神經,每一次都進到最深處,深到少年有種自己被活生生撕裂的錯覺。
「不……先生……別再……」
即使被這樣折辱,少年也沒有任何逃脫退避的空間。少年的雙手被既有的黑色鐐銬綑綁,鐵鍊一路延伸到床柱上。本來那些鍊子可以隨著少年的動作伸縮,讓他能夠在整間房間裡行走,但如今卻被鎖死,讓少年的雙手只能無力地擱在額上,隨著男人一波比一波猛烈的衝刺顫抖。
而兩腿上亦同,少年屈起雙膝,由於腳踝的部分被同樣的鐐銬束縛住,少年連伸腿踢開侵犯他的人都做不到。男人重重頂了兩下,銬鍊發出脆響,男人用兩手扳開少年試圖合攏的膝蓋,盯著他胯間相仿的男性性徵,從喉底笑了聲。
「今天怎麼了,這麼沒有精神?」男人伸出手來,毫不避諱地握住少年尚自青澀的欲望。少年發出一聲嗚咽,男人便低下頭來吻他的頸子,舔拭他青澀的喉結,用舌苔撫摸他的第二性徵,讓他更無法忘懷他是個貨真價實的男人。
「先生,到此為止吧,今天……求你……」少年試著再一次求饒。只有在此時此刻,少年才會完全放下自尊,彷彿被揉碎一般低姿態地向他示弱,「我、我已經……」
冰山碎裂瞬間的脆響,無論聽幾次都無比悅耳。
「你沒有精神,我怎麼能停下來呢?」
男人的五指仍舊在少年疲軟的欲望上摩娑,由上至下,惹得少年全身一陣輕微的哆嗦,「畢竟今天是給你的『獎勵』,你無法享受的話,獎勵就不成立了。」
男人說著,抓緊少年瘦弱的小腿又狠狠進了兩次,少年被衝擊得腰肢微彎,疼得咬緊了牙關。男人發出一聲低沉的歎息,灼熱的感覺從內壁蔓延到整個腹腔,少年失神地看著天花板,知道男人在他體內射精了。
多餘的體液順著他的大腿內側,緩緩流淌到床單上,讓少年有種被淹沒的錯覺。
男人把發洩過的欲望從少年體內抽出來,這讓少年鬆口氣,以為漫長的一夜終於結束。然而男人用手背撫摸他失神的臉龐,忽然笑笑。
「總有一天,你會和女人上床吧,如果你能從這裡出去的話。」
少年喘息著,被疼痛折磨得模糊一片的腦子還無法辨識男人的話。男人的手若有似無地搓揉著少年的男根,彷彿孩童玩弄心愛的玩具。令少年絕望的是,即使經過這樣多次的凌辱,那個地方還是在男人技巧而反覆的喚醒下抬頭了。
「你總會遇上什麼人,一個我以外的人。以你的性子,經過我這樣侮辱你,你肯定不會再選擇男人。你會和女人結婚,讓她懷下你的孩子嗎?」
男人說著讓少年無法理解的話,「你會把這玩意兒,插進什麼人的身體裡,讓她接收你的所有,同時把你的一切也交出去嗎?」
少年聽不懂男人的囈語,但男人一邊說著,一邊又把他從床上摟直起來,在少年驚恐的目光下,讓他跨開雙腿,坐在自己的大腿上。男人彷彿從未疲軟過的硬挺再次對準他被蹂躪到紅腫靡爛的穴口,些微的碰觸便讓少年睜大了眼睛。
「先、先生,唔……!」
男人的熱燙再一次深深沒進少年的身體裡,而聲音亦同,他在少年失控的哭叫聲中低語。「你是我的,小知之。」他摟住少年的腰,唇再次掠奪著少年的唇,凶狠地宣示著,語氣卻和動作呈反比的溫柔。
「You're my boy, from now till forever…」
知之驚醒。
他在夢中就知道自己在作夢了。而惱人的是,這類的夢境即便知之心知肚明,他卻無法從夢中逃脫,他只能躺在那裡,彷彿那些鐐銬連他的靈魂也束縛住,茫然而無助地等到整個夢境結束。
儘管夢中的他早已不會疼了。痛的是過去的他,而那一切早已經結束。
知之打開房間的門,確認外頭早已沒半個人,從門後抽了浴巾,打開浴室的門,走進去打開了頭頂的蓮蓬頭。
他把浴室的門鎖死,動手褪去了全身上下的衣物。兩手貼在冰涼的磁磚上,任由冰涼的水滑過他形狀優美的背脊,滑過黏膩的大腿內側,沖刷在他不盈一握的腳踝上。
知之清楚感覺到胯間濃濁的液體被沖開,他咬住下唇,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因為夢到那時的情景而射精,然後在一片狼籍中清醒。
知之看著蓮蓬頭旁的落地鏡。鏡裡映照出他蒼白纖瘦的軀體。這五年和念長他們相處下來,知之已經明顯胖了很多,特別是拜前一陣子某個英國廚師之賜,知之身上著實長了不少肉。儘管就男人的標準仍是過於清瘦,但比五年前知之剛來到這間屋子時好上太多,念長常說知之那時候根本就是皮包骨。
他看著自己的胴體,粉色的乳尖因為冷水的刺激微微挺立,沒有一絲贅肉的小腹,細瘦而缺乏力道的手臂和大腿,還有向來稀疏的體毛。知之看不出來這樣的肉體是怎麼樣吸引到那個男人,讓他一次又一次對自己做出那種獸行。
他把可有可無的眼鏡也摘掉,順手扔到一旁衣堆裡。把頭壓進手臂之間,任由冷水淋溼他的短髮。冰涼的髮絲貼著他的面頰,讓他的慾火下降許多。
知之吐了口氣。他的身體最近如此異常,說實話和某個白目也有關。
自從那一天在星空下互相坦白之後,徐念長對他的動作就越來越大膽。知之明明記得自己清楚明白地說「只做朋友就好」,但白目顯然就是因為聽不懂別人的話才叫白目。
念長現在一逮著機會就牽他的手,或者偷攬他的背。送他去上班時,會若有似無地扶他下車,在替他關車門時托他的腰,甚至有天晚上知之到廚房去喝水,念長看見他就微微一笑,道晚安之餘竟然在他耳殼上補了個吻,讓知之差點沒把手上的水打翻。
知之曾經嚴詞抗議過,但念長的臉皮厚得像城牆,總是連聲說著「對不起、抱歉」之後,下次繼續依然故我。
果然還是應該搬出去才對的……知之絕望地想著。
雖然徐念長實際上也沒做什麼過分的事,真正踰矩的動作一個也沒有。他對念長那些碰觸也非全然沒有感覺,相反的,有時候念長不經意的一下摟腰,就能讓知之像被喚醒一般渾身起反應。這才是知之最困擾的。
知之透過濡溼的額髮再度看著鏡中的自己。他明白自己對那方面的事排斥得異乎尋常,因為對他來講,與性愛連結的向來就只有兩樣意象:疼痛和折磨。
他無法忘記第一次被人進侵時的景象,他的身體清楚地銘刻下每一分痛苦的記憶,那是知之第一次知道,原來光是痛,就能夠痛到讓人求死不能。
還有道具。知之閉上眼睛,男人對他的態度非常清楚,除了第一次侵犯他後有在他睡著的時候道歉,接下來知之的頑抗態度徹底激起男人的劣根。他告訴知之,無論如何他會做同樣的事情下去,只要他想,知之要嘛就接受,要嘛他會用暴力讓知之接受。
而男人也確實把他的話付諸於實行。知之在成年以前,幾乎沒有一次和男人的性愛是正常平順地進行,他見識過各式各樣的束縛道具,各種慘無人道的挑逗工具,而男人發現這樣玩弄他很有趣之後,即使知之像死魚一樣躺在床上消極不抵抗,男人也會使用那些東西,逼得知之不得不抵抗。
這讓知之的身體變得異常。知之心知肚明,對於男人的碰觸,他不是過於冷感,而是過於敏感。
他熟知每一種惹起人欲望的方法,不需要太過強烈的撫觸,就能讓他產生聯想。哪怕只是尋常朋友間的擁抱,也能讓知之全身起雞皮疙瘩。
知之張開眼睛,直起腰來撩起一絲鬢髮。冷水滑過他耳殼,一路淌下鎖骨,滴落他屬於男性的平坦胸膛,即使只是這樣的水流,知之絕望地發現,也足以讓他欲火燒身。
這是那個人在他身上鐫刻下的烙印。這些年來知之拚了命地擺脫男人對他情感上的束縛,他研究了許多心理學、看了不少書,說服自己對那個人每一絲好感都是出於某種心理機制下的錯覺。
但身體的部分卻沒有辦法,男人帶給他的每一絲痛苦和歡娛,都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記憶,他無法靠任何分析與理論消除。
他厭惡這樣的身體。
他厭惡這樣的身體,再被任何人輕易碰觸。
特別是那個白目。知之無法想像,念長的身體壓著他的身體,唇舌交纏著他的唇舌,對他做那些當年那個人對他做過的事,觸摸每一個那個人觸摸過的地方。知之光是想像,就覺得完全無法忍受。
無法……忍耐。
知之把額髮貼在潮溼的落地鏡上,絕望地合上眼睛。
蓮蓬頭的水滴落磁磚,滴滴答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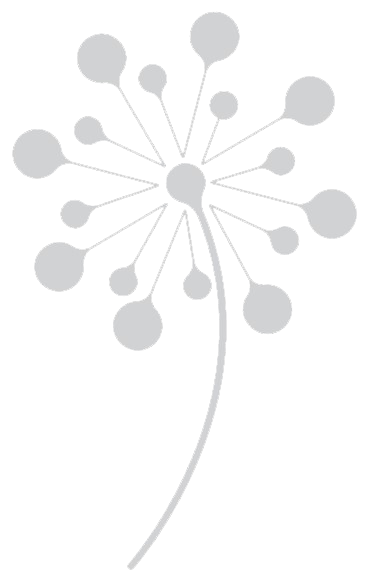
念長走到飯廳,把剛做好的清湯陽春麵放到餐桌上,解下圍裙。
他往客廳望去,善存正坐在沙發上,電視上播放著鄉土連續劇,那部戲念長有時也會跟著追,現在已經播到第一百零三集了,女配角正用力對著女主角尖叫著:『妳不配!妳不配!妳憑什麼……』然後對女主角猛搧巴掌。
而沙發的一角坐著一如往常冷若冰山的室友。知之拿著一本書,書名好像叫什麼《例外狀態批判與班雅明的思考本質》外加一大串英文,正戴著眼鏡一頁一頁翻看著,時不時偷眼看一下電視螢幕上的進度,一派從容悠閒。
念長看著眼前的日常景象,不由自主地揚了揚唇角。
自從英國的遠客夏洛克回國,到現在已經三個月了。
三個月來,屋子裡三個男人生活逐漸步回正軌,知之依然做他的各種研究,整天窩在房間裡不出來。而善存依舊過著一邊和他的英文老師周旋、一邊和他的搖滾樂團朋友廝混的生活。
而徐念長則是回到大多數時間枯燥無聊的法醫崗位上,和開不完的死亡證明書、看不完的相驗解剖圖奮鬥。偶爾和知之在深夜時喝點小酒,討論一下比較困難曲折的案情,這已經是這樣平靜生活中最大的波瀾了。
先前幾個月幾乎危及他們所有人性命的恐怖事件,現在變得像是從沒發生過一樣,連記憶都顯得淡泊了。
「小知、善存!晚餐好了,過來吃吧!」念長對著客廳喊道。
但還是有一些不同。念長想著,他的室友知之,從前幾乎連踏出那間房門門檻都不肯的,除了上班外都繭居在那間被電腦環繞的房間裡。但現在只要念長邀請,知之總會遲疑地開門出來,擺出一副勉為其難的樣子,陪他在逐漸變涼的秋夜裡散步一陣子。
而室友對待他的態度也微妙地改變了。像是偷牽手或是偷攬肩之類的,換做以往的知之肯定一腳把他踹飛出去。但現在,對於念長這些不自重的小動作,知之也只是露出困擾的表情,別過頭紅個臉便算了,最多只是輕輕掙開一下而已。
念長說實在有點迷惘。他不知道這樣的狀態是不是叫「小有進展」,甚至不知道是不是好的進展。
但至少現在室友還在他身邊。在他這樣不分青紅皂白的示愛之後,沒有嚇得逃走,也沒有消失不見,在他身邊安安穩穩地待了下來。念長便覺得目前為止這樣就夠了。
而這間屋子裡變化最明顯的,反而是他的小表弟。
自從在機場送走那位英國總裁後,剛開始善存還沒有什麼明顯的異狀,甚至還顯得很樂觀,照樣和他的死黨們到處出去玩,一如往常的活潑開朗。
夏洛克回英國沒多久就丟了善存的MSN報平安,在網路上也時有交流,兩人甚至會在半夜裡視訊談天。甚至在十一月中時,夏洛克還捎了一封長信來,內容是關於三個月前亞利斯事件的始末,善存也高高興興地接了,還卯起來寫了生平最長的一封回信。
但問題就在那之後,善存回信之後,夏洛克就忽然音訊全無了。不但完全沒有回信,就連網路上也跟著消聲匿跡。
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今年十二月,一直到最近,連知之都覺得有點不對勁了,幫著善存打越洋電話到英國的弗瑞泰宅邸。但不是沒有人接,就是僕人一類的人接的電話,說是弗瑞泰先生現在並不在家,留了電話請求對方回電,結果也毫無回應。
這讓他那個一向單純的表弟陷入茫然中。知之一開始還在旁邊冷嘲熱諷,說總裁多半是看上了新的對象,移情別戀改摧殘別家的美少年去了,這樣輕浮的花花公子本來就不足採信,還好善存早早就和他分開了之類的話。
但待看到善存是真的愁眉不展,知之又覺得不忍心了,改口說夏洛克只是之前玩得太荒唐,被家長揪回家去管訓中罷了,等哪天又想渡假了一定會回來等等。
「他不可能忘記你的,那個人說過記憶力是他為數僅有的優點之一。」知之還對善存說了句不知道算不算安慰的話。
念長也看得出來表弟異乎平常的落寞。就像現在,善存雖然坐在沙發上看節目,即使是女主角的八十五歲老母跪下來哭求女配角和男主角放過他們一家老小,不要再折磨他們家女兒的狗血劇情,善存平常都會跟著抽衛生紙哭的。
但現在,善存卻只是呆呆地坐著,眼睛盯著螢幕,心思卻已經明顯不在這裡了。
「下個月我有特休,怎麼樣,要不要一起去個什麼地方玩?」
念長坐在餐桌旁問兩個室友。夏洛克回家後,這個家的餐桌也回復了以往的水準。善存認分地扒著念長的樸素陽春麵。
以往一聽到念長說要去哪裡玩,善存總是最興奮的一個,如今卻只是抬起臉來,好奇地問:
「要去哪裡?會去很久嗎?」
「看你們要去哪裡,我想想……南投我們去過了,墾丁也去過兩次了,花蓮之前去臺東時也有經過。不如這次就去外島怎麼樣?像是澎湖或是金門。」
念長看著一如往常不輕易發表意見的知之,「小知,你覺得呢?有沒有特別想去的地方?」
知之捲了下手裡的麵條,「都可以。」他說,看了眼還有點閃神閃神的善存,「看愛蜜莉吧!去他想去的地方,不用顧慮我。反正我去哪裡都一樣。」
「善存,你想去哪?」念長於是問自家表弟。
善存抬起頭來,看著念長的眼神有幾分茫然,半晌他忽然開口,「倫敦……」
念長和知之都看著他,善存才發現自己囈語了什麼,忙搖手說,「呃,沒、沒有啦,我只是想問一下,倫敦是什麼樣的地方而已。我……我沒有真的要去。」
知之撇撇唇。「倫敦距離臺北市有半個地球之遙,是十八世紀起發展起來的都市,從前是大英帝國的繁華首都,但最近卻飽受歐洲特別是緊縮政策之苦,上萬人仰賴政府的救濟政策過活,晚景沒落。順帶一提它還是個雨都,臺北一年雨日超過一百五十日就已經很誇張了,倫敦的雨日動輒超過兩百日,十九世紀時放眼望去全是黑壓壓的傘,是個抑鬱無聊的都市。你不會想去那種地方的。」
念長聽著知之明顯充滿私心的介紹,忍不住苦笑。善存「唔」了聲,又問:「那去那個地方要很久嗎?我是說,搭飛機或是搭船的話。」
念長看知之吐了口氣,好像不想回答那樣,便說:「飛機的話差不多要十多個小時,從臺灣起飛一般會在香港轉機,加上轉機時間可能超過二十小時。海運的話要更久,以目前的遊輪速度可能要十幾二十天。」
善存的肩明顯微微垂下來,「那……要花很多錢嗎?」
念長思索著說:「歐洲的話,現在歐洲的物價漲很快,歐洲這麼遠,也不能說去就去說回來就回來,起碼要十天左右,這樣就算再節省,一個人十萬臺幣跑不掉。」
知之看見善存聽完臉色微白,隨即「喔」了一聲,恢復輕鬆的態度說:
「要去澎湖玩嗎?感覺很有趣呢,那是不是要準備暈船藥啊,念哥?」
知之和念長對看了一眼,彼此都在對方眼中看到擔憂。知之單手支著下頷,「倫敦很大的,不算外圍,光DownTown部分就有七到八個臺北市大小,要在這麼大的地方找一個人簡直大海撈針,更別說是路上偶然遇見了。」他說。
念長看善存扒著麵沒說話,用故作輕鬆的語氣說:「是說,夏洛克先生還是沒寫信來嗎?我記得以前他每週都會寫三、四封信給善存,有時還會附送小禮物。這麼久沒寄還滿稀奇的,會不會也跟家人到哪裡去玩了呢?」
此話一出,餐桌旁的兩個人都停下筷子抬起頭來。知之以一種「白目沒藥醫」的眼神瞪了念長一眼,接口說:「他應該忙得很吧?我上個月看非凡的財經新聞,他那頭鳥窩頭剪短了,人也瘦了一點。」
「咦,小克有上新聞嗎?」善存驚訝地問。知之聳聳肩,「他在十月的股東大會上又被選回Roman Knightly的執行總長,算是重新掌權,難怪當初他這麼急著回去。」
「那會不會是忙病了?要是可以打個電話關心他一下就好了……」念長說。
知之沒好氣地哼了聲,「我不認為他是那種會把自己忙病的人,那個人看似輕浮又不要臉,該釘睛的時候狡猾得像狐狸一樣。他很清楚自己要的東西是什麼,而且一看上了就會拚命去求取,沒達目的絕對不放手。」
他頓了下,又冷冷地別過頭,「某些方面來講,這也是我不喜歡他的地方。」
念長不由得笑起來,帶點苦意的,「聽起來小知非常了解他。」
知之的臉一下子漲紅起來,「我是在探勘敵情!誰像你一樣,自己的弟弟被人打包裝進行李箱,還傻呼呼地去機場送行。」
念長笑著沒和知之爭辯。這時善存倒是開口了,「小克他……會不會真的發生什麼事了呢……」他把筷子停在唇邊。
知之看了他一眼,雙手抱胸靠回椅背上。「你放心吧,他是堂堂弗瑞泰家族的繼承人,又是大公司的老闆,幾千人仰賴他而活,平常身邊跟的不是祕書就是大人物,他的一舉一動都被人注視著,會個情婦可能還會被狗仔隊偷拍。」
他又哼了聲,「他能出什麼事?總不可能在大街上被外星人綁架吧?」
『現在為您插播一則新聞,據The Sun今日晚間報導指出,英國第三大商屬企業聯盟Fretes Eco. Company,其旗下最大少女服飾公司Roman Knightly……』
開在客廳的電視傳出主播的聲音,餐桌旁三個人都豎起了耳朵,善存從餐桌旁站起來,一路跑到電視前,知之他們也跟在後面。
『該公司的現任執行長Sherlock Shaw Fretes,被譽為二十一世紀英國商界的貴公子之一,先前慈善酒會上尚與深受少女歡迎的威廉王子有過親密接觸,許多商界人士認為他是英國史上最年輕、外貌最理想的財團繼承人……』
畫面上打出夏洛克的照片時,知之等人都是一陣不安,畫面上的夏洛克穿著一襲黑色燕尾服,一頭燦金的頭髮尚未染黑,泛著耀目的光澤。知之看見善存臉色有點蒼白,似乎微微咬了下唇,而所有人都聽著主播平板的報導:
『……但如今該繼承人被家族證實,弗瑞泰先生自十月底執行長選舉股東大會後即因不明原因失蹤,目前仍下落不明。』
電視前的人都倒抽了口冷氣,而報導仍然繼續著。
『Roman Knightly聲明為免造成眾多投資人恐慌,才將消息隱而不報,並強調會完全掌握公司的營運,耶誕例會也會照常舉行。代理財團首長Ranlady夫人對外表示,他們強烈懷疑這是一起來自反對派股東的陰謀,企圖影響執行長選舉結果,並呼籲不法人士儘快釋放她的繼子。』
『而反對派股東聲明絕無此事,認為夏洛克.弗瑞泰先生應該是單純離家出走,先前該位執行長被短暫解職時,也曾因不明原因消失數月之久。反對派股東並指出弗瑞泰先生在外情婦眾多,私生活混亂,並譴責這種惡意曠職的行為……』
底下開始播報這位總裁大人的花邊新聞,客廳裡三個人呆呆地看著螢幕上為數驚人的各種俊男美女照片。報導上說夏洛克經常跟政商界人士傳緋聞,而且更驚人的是男女通吃,和年輕男性傳緋聞的次數還比女性多。
螢幕上打出不少金髮碧眼、看上去像洋娃娃一般的少年肖像,據說全是夏洛克傳緋聞的對象,還有狗仔拍到執行長和青年出入旅館的畫面。照片上的夏洛克裸露那身修長完美的背,和另一個少年蒼白的裸背重疊在一起,不用細看就知道他們在幹什麼。
知之邊看邊不屑地說:「愛蜜莉比他們好看多了。」但善存已經完全說不出話來了。
報導最後停在一張大約二十出頭的青年身上。青年有著一頭黑色的短髮,長相俊秀,身材精實,渾身上下一絲多餘的贅肉也無。善存一看到這人的照片就叫出聲。
「啊,是Lan先生……」他說。念長也點點頭,兩個人都看過這位夏洛克貼身祕書的本來模樣,新聞上的Lan照片似乎又比三個月前出現在他們面前的更年輕些,大概是剛來應徵時拍的,整個人散發出一種讓人不敢輕慢的銳利氣息。
『……這位夏洛克.弗瑞泰總裁的貼身祕書,全名是Albert Lan Dickinson,傳聞是弗瑞泰家族特地從M16最優秀的幹員中挖角來的,為了保護弗瑞泰先生的人身安危,換言之就是私人保鑣。這位貼身祕書的經歷也相當豐富,據說在當幹員前就是軍校出身,曾經加入英國海陸蛙人隊,但卻因為緋聞而被迫除役。那之後曾消失相當長一段時間,沒有人知道這位神祕的保鑣去了哪裡、又做過些什麼。』
屋子裡的三個人都靜靜地聽著,善存更是睜圓了眼。回想起那個包著繃帶、在廚房裡替自己切菜洗水果的青年,怎麼也想不到這樣的人竟然是這麼來歷驚人的人物。
『以Albert Lan的經歷而言,肯在一個普通少女服飾企業總裁身邊,當一個平凡的祕書,實在令人費解。』
『據可靠傳聞指出,弗瑞泰先生要求Albert Lan在許多私人及公開場合時,以女裝打扮出席各種例會。雖說Roman Knightly以他的女裝耶誕晚會聞名,但如此特異的要求讓人不禁猜測,弗瑞泰先生與他的私人祕書間,是否有公務外其他不可告人的關係。』
知之和念長都豎起耳朵聽著,不時注意善存的表情。善存大概是聽得似懂非懂,在電視前捏緊了十指,嘴巴也緊緊抿著。
『夏洛克.弗瑞泰總裁至今未婚,而他對同性特殊的執著與愛戀,在倫敦的政商名流間早已不是新聞。』
『夏洛克先生遊戲花叢,留下遺珠無數,想必也惹惱了不少落花有意的名門仕女。而夏洛克先生此次失蹤,他的祕書Albert Lan也一同失蹤,這讓弗瑞泰家族也開始懷疑,這是否是一樁感情糾紛導致的綁架事件。警場現正展開嚴密的調查中……』
新聞的畫面結束在那個金髮藍眼的夫人在記者會上嚴肅的神情中,知之他們都見過這個婦人一次,就是在這間屋子裡,當時夏洛克還殷勤地介紹善存給他的繼母認識。
客廳裡一片靜寂,知之和善存都說不出話來。念長怔怔盯著已經開始報導下一則新聞的主播,半晌才喃喃出口。
「剛剛那個夏洛克,是我們認識的那一個……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