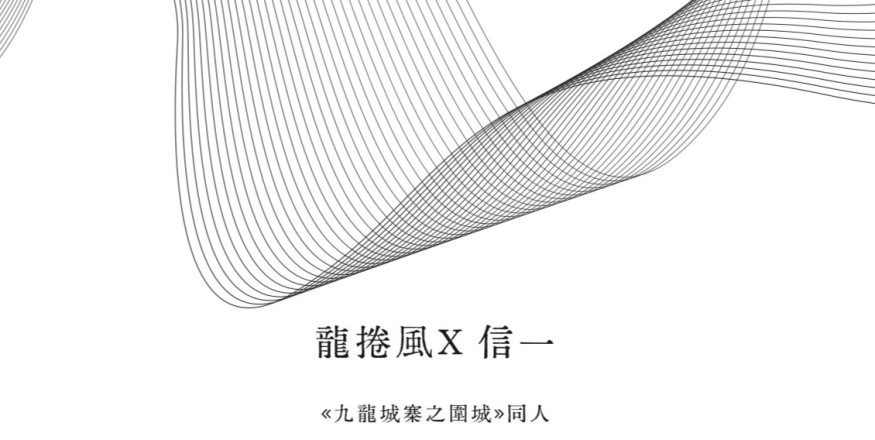【風信】卻問何時才看開
海浪翻波,鹹腥的風吹來一陣又一陣。
叼著煙的信一,側頭順著風勢攏攏頭髮,柔軟的捲髮纏上他的指間。劫後餘生,後腦勺長出的白髮,在髮絲間偶然冒頭,信一捨不得去拔。這頭捲髮在不知不覺間漸長,長度變了、蓬鬆也不再,原本時髦的捲髮只剩下一點弧度,被精心設計的髮型完全走樣。
從唇上下頷間冒出的鬍渣變成鬍鬚蓋在人中,扎著上唇,不修邊幅得就像想博來一聲笑罵,讓他可以嬉皮笑臉地半躺到理髮凳上,感受帶著綿密刮鬍膏的刷子撫過下半臉,然後乾燥的手指輕按到他的臉上,刀鋒輕柔地刮過皮膚;然而,信一卻又忍不住維持了最基本的儀容整潔,配搭衣著、整理頭髮……他的品味、他的穿衣喜好、他的髮型、他的習慣,全有著另一個人的影子。
這份微薄得難以向他人明言的、與對方的連繫,信一也不願拋棄,只能矛盾地帶著苦惱活著。既想放棄,卻又因為離他而去的人而繼續,生活如是、性命亦如是,矛盾至極。
沒了三根手指的手,尚且可以夾著香煙。捏著取了煙下來,信一長呼了一口氣,這時海風又吹來了,呼嘯著吞噬了白煙。
船屋外的椅子很硬,不好坐,但信一每天醒來,唯一願意做的只有坐到這把椅子上,呆望著海,靜看潮退潮漲、日出日落,直至飯點到來,同住的另外兩人拿著外套找來,要他回屋裏好好吃飯,他才會挪動僵硬的肢體。
起初他只坐著不抽煙,畢竟煙要麻煩別人買,他們還在躲風頭不好外出,而且老大的遺言要他活著,那他便想著趁機戒了吧,但有天,屢屢看著他欲言又止的四仔,終於忍不住跟他搭話。
他拉著另一把椅子,坐到信一身旁,視線同樣放在海面,靜靜坐了半晌後才開口:「你大佬有肺癌,情況好嚴重。」四仔的情緒很沉重,但用著醫者獨用的冷靜口吻,悶在繃帶下的嘴巴為話語平添了低沈。他說:「佢唔俾我同你哋任何一個人講,我諗佢自己都知,情況唔樂觀到已經時日無多,就算去醫院都無用。」
對方的本意應該是想告訴他,如龍捲風偶然夢囈時唸唸的「整撚定」,想說就算他的老大沒命喪在大老闆和王九手下,依他的病情也活不長。
活不長,龍捲風注定活不長、張少祖注定活不長,無論有沒有發生那些悲劇,對方都定必離自己而去,只不過是時間長短有異罷了。
人生必然會死。
得知這事的信一,先是怔著,然後捂著眼睛,深呼吸了幾下後,四仔看到他的嘴角彎起來,但手顫抖得厲害,搖著頭的信一霎時間也說不出話來,只能一昧搖頭,偶然又吐出幾聲像嘆氣似的輕笑。
最後他放下手時,四仔看著他的眼眶是紅的,連眼白都帶著血絲,但笑容滿面,像雨過天青的明朗晴空,還向四仔道謝。四仔以為他的兄弟終於走出來了,能看開了,卻沒想到對方的傷痛,如末期的癌細胞,在體內增生擴散,侵入器官,難以自控,無法割離。
自那天起,信一又重新開始抽煙,而且愈抽愈兇,一個上午就抽完一包雲絲頓。白煙總纏繞著信一,煙味薰進他的指頭與衣衫,與龍捲風同款的二手煙興許比尼古丁更讓信一上癮,但四仔和十二少每次看到信一抽煙,那落寞的神情和累積下來的煙霧,瀰漫得像在不斷向死人上香。
只不過就連信一都難以說清,他想、他要、他在做的,是悼念龍捲風本人,還是在憑弔曾有著龍捲風在旁的藍信一?
無根的白煙繼續在半空中飄蕩,問題仍然沒有答案。
喪親必然是痛的,同樣失去了摯愛的四仔明白,但他敏感地辨認出,信一的痛苦與他的是類似的。
信一和他老大之間有著什麼、有過什麼,四仔隱約猜得出來,只不過無意道破,畢竟他家就住在他們附近,夜深了憑窗眺望,不時可以看到大紅花籠裏,信一正倚在窗邊吐煙。那是龍捲風的家,深夜時分,哪怕是頭馬,在老大的家中抽煙仍然相當奇怪,更別說四仔有時看到,信一穿的是寬鬆的居家服,甚至是睡衣。有些事大家心照,街坊們無意挑起他們的活佛到燈下檢視,看看他的心放到哪裡去了。
四仔不曉得十二少又知道多少,才會與他一同,沒有出手,試圖制止信一的慢性自殺,但亦也許,只是因為他們都是住在海邊的泥菩薩,救不了自己,也難救別人。
信一的情況,如同地球沒了太陽,如同月球沒了地球,如同指南針沒了地磁,而他們還要求信一維持呼吸心跳,怕是已經強人所難。
他們能做的,只有在信一抽煙時,靜靜坐在他旁邊吸二手煙,或是伸手跟他討一根,就怕看漏了一眼,一下水聲響起來,坐在椅上的人終於回應大海的呼喚跳了下去。
信一的表情,哪怕是跟他兄弟多年,從小相識到大的十二少都未曾見過,只覺得好像一口氣用了一大堆鎮靜劑的癮君子,平靜安祥到空洞,但靈魂破碎,十二少都要懷疑起信一抽的是雲絲頓還是大麻煙。
一再轉動眼珠偷瞄身旁的人,拖著一條傷腿的十二少不喜歡待在潮濕的海風下,傷患會癢痛得像在蟲蟻鑽了進去,在骨骼間走動,但比戒毒時感覺到的蟲噬感輕鬆多了。十二少一再變換坐姿,但反觀信一,由早上到夜晚都幾乎沒動,只在點煙時有點變化。
每次信一丟下菸蒂踩滅時,十二少都覺得是個合適的時機,可以開口說點什麼,可是一時之間,總想不出來,於是嘴巴只能像離水的魚般張張合合;到他想好了,正欲開口時,四仔便會搭上他的肩,示意可以換班了,於是他又把那些問句憋了回去。
四仔本來就不是多話的人,甚至說得上沉默寡言,與十二少可謂兩個極端。他之前開口,本是安慰的話,卻讓信一撿回了煙癮,於是乎就更加沉默了,抿緊的嘴唇只在病發時張開,抱頭發出慘叫聲,再不然,就是信一抽得太兇了,一天三盒,才出聲勸勸。
勸的不是要他戒掉,因為四仔很清楚這不可能,而且要是抽煙能令信一繼續活著,不至於急著尋死到自刎或投海,那就讓他抽吧。也許香煙和他的面具是一樣的,也和此刻覆在他們三人身上的繃帶是一樣的。
摯愛離開的痛、親眼看著愛人被淩虐的恨,四仔至今都未能癒好傷口,又如何逼迫信一看開?大家都不過是海邊的泥菩薩,正被潮濕的海風逐漸磨蝕。
四仔坐到信一旁邊的椅子上,而對方並未向他投來目光,但四仔也不太在意,只自顧自地合上了眼。午後陽光照到他們身上,隔著眼皮使得視野透著肉紅;海風吹動四仔臉上披著的毛巾,拂過他祼露在衣服外的皮膚與疤痕,潮濕而鹹腥的海水味徘徊在感官過久,已經習慣到快聞不出來,但二手煙吸久了仍然辛辣刺鼻,也難怪信一的眼眶偶而會發紅泛霧。
又是一縷白煙,自信一半張的嘴唇間呼出。這時海風終於止了,讓四仔的目光可以追隨著這縷悠悠浮浮的煙,升至半空中,漸漸消去了形態,看似無痕,走得乾淨,但仍然殘留在空氣中、感官中、神經中、呼吸道中、血液中……
諸法空相,不生不滅。
9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TMKCV4Oa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