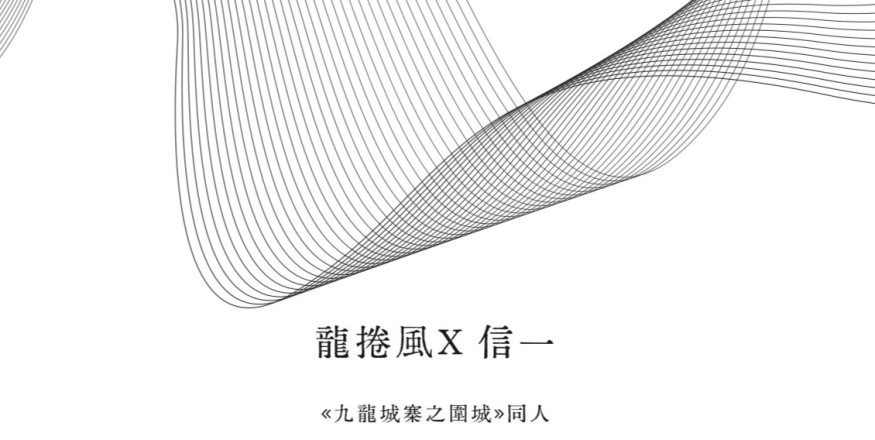入夜後的阿柒冰室相當涼爽,畢竟它的天花板早就不翼而飛,晚風總能跑進來,這點在夏天時蠻不錯的,冬天時冷得人不想久待又是另一回事了。
冰室在賣完招牌叉燒飯後,基本上就沒多少人光顧,因此總在入夜後沒多久便打烊。
收銀櫃檯後方的神像上裝了一盞日光燈管,燈光白得發藍,照得人鬼氣森森的,用來看帳簿倒是剛好。信一右手握著筆,左手飛快撥珠,清脆的噠噠聲響個不停,撥珠的手勢既輕快又穩妥;他的目光落在帳簿上,運算期間連看都不用看一眼算盤,專注地打著算盤計帳,最後才瞄瞄珠子分佈,動筆抄下結果到簿上。
架在牆角的電視正播著《六點半新聞報道》,新聞主播神色凝重地唸讀新聞稿。在打算盤的信一無法分神去聽,也不在乎城寨外發生的事,他的志願是當龍捲風的馬仔而他已經在當了,但作為他老大的龍捲風,關心的事自然比較多,也事事關心到變習慣了,眼下的他正仰頭看著新聞,表情跟新聞主播差不多一樣嚴肅。
為免影響阿柒清潔收鋪,他搬了塑膠椅去收銀櫃前坐,背靠在櫃壁上,手裏捧著一小碗街坊送的潮州炸花生。他吃得極慢,看完一節新聞才可能嗑上一兩顆,畢竟他其實不餓,咬咬花生不過是讓閑著沒抽煙的嘴巴沒那麼癢。
倖存的天花板吊著的電風扇,正搖頭晃腦的吹著微風,加快吹乾剛拖過的地板。叼著煙的阿柒向龍捲風點了點頭後,挑起水桶又拿著地拖,慢慢走到後巷倒水,然後到廚房繼續清潔,完成收鋪程序。
於是乎,打烊後的阿柒冰室,眼下只有信一和龍捲風兩人。
撥珠聲響個不停後又突然停下,喻意一個小結的計完。記錄下金額後,信一搖了搖筆桿,抬頭偷偷瞄了眼收銀台前的龍捲風,但只看到一截花白的頭頂,偶然被風拂亂幾縷。
這時,電視裏的新聞女主播在向觀眾們說「晚安」,於是乎,龍捲風丟下捏著的花生回碗裏,拍了拍褲管站起來,回身倚到收銀櫃上。「喂,計完未?」龍捲風低頭望向數簿,兩眼微瞇的,試圖去閱讀上下顛倒了的數字。
他噙著笑容問信一:「搞乜今晚計咁耐?阿柒佢賺咗好多咩?」
「就快計完喇,你等多陣啦!」信一皺著眉頭答道。他連忙低頭,清零了算盤重新撥珠,假裝是被打擾到了才停下的,而不是自己盯著人家發了一會呆。「你攰嘅話就返屋企先,我好快得。」信一說,又擺了擺握著筆桿的手。
「既然好快得,咁等多你一陣啦。」龍捲風應道,茶色墨鏡下的眼隱含笑意,眼尾的細紋都現了形,「等你計完,我哋再一齊返去。」
低頭打算盤的信一壓不住嘴角的偷偷上揚。
電視在播廣告,播來播去都是那些,龍捲風自然無興趣看,看他的門生計數還比較有趣,尤其是信一在打算盤時,嘴唇總會不自覺地噘著,眉間則是一如平日的習慣緊蹙。龍捲風幾乎可以預計,年老後的信一額頭肯定會積聚不少皺紋,眼尾和法令也是,畢竟這孩子其實很愛笑,只要生活沒壓垮他的嘴角。
感覺到對方的視線徘徊不走,信一便翹著兩側嘴角調侃問:「望咩啫,驚我穿櫃桶底啊?」
他在數簿上抄數字的同時,偷空瞄了眼對方,笑盈盈的眼睛微彎。
龍捲風失笑,抬抬下巴指向數簿,開玩笑說:「驚你計錯數咋!都唔知邊個啦,當年一加一寫等於四,激到先生死死下。」
「係囉,都唔知邊個,次次買碗七蚊嘅魚蛋粉都俾夠十蚊叫人跑腿,仲要人唔洗找錢囉。」信一淡淡然回道,清脆的噠噠算盤撥珠聲,聽起來就像當年揣在口袋裏的那三枚一元硬幣,隨走動叮噹作響。
龍捲風自然知信一說的是什麼,便笑著應:「個三蚊雞,咪當俾你買糖囉。」
「如果個陣個三蚊我拎晒去買糖,我變左做無牙仔十世嚕。」信一應道,說著說著,他都忍不住失笑,像想到自己掉光了牙齒的畫面,但又搖了搖頭。
在龍哥眼中,這些不過是小恩小惠,但對小時候的信一而言,絕對是救命之恩。這看似不算是多大金額的三元,可以救回幾近餓死的他和媽媽,可以讓他們再多捱幾天,直至那垃圾又找上他們倆母子,搶走他們的一切財產……天大的恩情,小時候的信一每次說「謝謝」時都總覺得不夠表達,更何況是事過境遷後的現在,現在要是開口講多謝,這輕飄飄的話既無用又矯情,還不如別講算了,省得對方笑呵呵地嫌肉麻,使得謝意好像沒傳到過去。
信一握著原子筆,飛快地在數簿裏寫下最後一個銀碼,然後合上硬皮記事簿,再拔下原子筆的筆蓋。「係呢,龍哥啊,最近我一直諗緊……」信一望著手上的筆,邊合上筆蓋邊說,講話難得吞吞吐吐,「諗緊……我應唔應該去紋身。」
龍捲風挑起一邊眉,訝異地反問:「紋身?好地地做咩諗紋身?」
「紋左身先似撈偏㗎嘛!」儘管回答的口吻和內容都略微天真,但信一滿臉認真,眉毛還微微蹙起,「我而家係龍城幫嘅人,你話我紋條『龍』好無啊?」他抬起眼皮,小心翼翼地瞄了眼龍哥,想看看對方的表情,可惜對方狡猾地偏過頭,刻意讓鏡片反光,白燦燦的一道光斜在鏡片上,遮去眼睛,讓信一瞧不清自己的眼神。
「哇……」龍捲風誇張地皺眉,搖頭晃腦的嚷嚷:「紋條龍?好老土喎!」
「唔、唔好咩?」信一的語氣隱隱有點失落,雙眼睜圓,直直盯著對方看,一雙眉毛被他扭得一高一低,表情可憐兮兮的,但龍捲風這時,忽然又對那碗潮州炸花生起了興趣,正低頭撥弄著花生粒,恰好與信一的目光錯開。
嘴巴翕張了幾下後,信一撐起笑容,從碗裏擇了一顆花生拋進嘴裏。
龍捲風佯怒斥責:「搞事啊你?咁夠膽連大佬嘅花生都偷!」語畢,他拍了下花生小偷的手背,但力度輕得皮膚連紅都沒紅一下,惹得信一笑了出聲。
信一托著臉頰,倚在收銀櫃枱面,腮幫子一鼓鼓的咀嚼著嘴裏的花生,眼睛從下而下地瞅著龍捲風,往上望的眼珠堆起本就深邃的眼皮褶子。龍捲風還在忙著挑花生粒,默默由著信一的目光停留在他身上,久久纏綿不願移開。
氣氛安寧祥和得溫馨,連風扇運作時發出細微吱啞聲都顯得悅耳。
好一會兒後,信一忽地開口,又重提起剛剛的話題,問:「咁……龍哥你覺得我紋咩好啊?」想了想後,他試著提議:「龍唔好咁……一係紋老虎?」
他總不好說要紋頭鳳,好跟對方湊一個龍鳳呈祥百年好合吧。
「乜信仔你轉左跟Tiger咩?」龍捲風淡淡然地反問,目光都沒分一個出來給信一,只專心地觀察手上捏著的、剛精挑細選出的花生粒。信一不知道這顆精挑出來的有何特別,除了長得特別圓潤特別靚以外。點點鹽粒黏在龍哥指頭,看得信一都渴了。
嚥了嚥口水,信一裝作若無其事,實質痴痴地盯著龍捲風移動手,把花生放進嘴裏,舌頭還飛快舔過嘴唇,收拾殘留的細細鹽粒。信一見狀,也舔了舔唇。
低咳了聲清清喉嚨,信一擺出一副興致勃勃的姿態,又提議道:「咁樣不如紋句『雞腸』吖!望落型呀!」信一說著,手指在櫃面上連劃了幾個圈,「呢,個啲潦草字呢!幾靚啊!」
老大不太會英文,而且還要用潦草字,他更加看不懂,任信一要紋他的名字、還是露骨的愛意誓言,他的老大都看不出來。
「你英文好叻咩?」龍捲風慢悠悠反問,墨鏡底下的眼睛睨了愛美的小孩一眼。他嚥掉了嚼爛了的花生後才說:「等等人地寫錯字你又唔知,咁咪柒囉。」
「又係嘅……」被連番反對提議的信一有點蔫巴巴起來,趴到收銀櫃上悶悶地說:「咁一係……紋觀音囉?無問題喇啩?咁常見。」話是這樣說,他其實不太想紋觀音,嫌土氣,又嫌沒有意思。
聞言,龍捲風一把捏住信一的臉頰,鄭重警告:「嗱!其實你紋咩我都無乜所謂,但真係唔該大佬你喇,咪撚同我紋觀音啊、佛祖啊、關二哥啊個啲上背脊同心口。」
信一眨了眨眼,沒想到自己這隨口一說,老大竟有如此大的反應,不由得好奇起原因來:「點解啊?」他又再眨眨眼,想起曾經聽過的紋身忌諱,於是湊近了對方,興味盎然地問:「因為會有報應?但唔係唔開眼就無問題㗎喇咩?」
「屌,關咩事。」龍捲風低罵了聲,用力把花生丟回碗裏,「仆你個街,你紋個觀音上身,你一除衫我就望住啊觀音大士,咁到時我係屌緊你,定屌緊觀音娘娘?」他瞪著朗聲大笑的信一,沒好氣地罵:「諗下個畫面都鳩縮……咁撚唔尊重實有報應呀衰仔!」
龍捲風語氣愈凝重,信一就笑得愈大聲,卻想起了城寨以前有位鳳姐很受歡迎,因為她背上紋了幅四色觀音坐蓮圖,當客人後入時,便彷彿進了蓮花裏滋擾著觀音……她的客人多到不可思議,本應很快就可以賺夠離場,然而隨著「好生意」而來的性病也帶走了她的生命。
如龍捲風所言,污穢神明定有報應。報應不爽,本就沒打算紋觀音的信一,自然打消了所有紋神明上身的念頭,畢竟他的心願是老大長命百歲千福萬安。
「好喇好喇,所有人物都唔放上身喇!咁唔洗鳩縮啦?」笑瞇瞇的信一趴在收銀櫃上,側著頭,柔聲問:「咁我紋咩好啊龍哥?」他由下而上仰望著龍哥,彎彎的嘴角,笑得狡黠狡黠的,很像雜貨店養來抓老鼠的貓。
「諗唔到咪唔好紋囉。」龍捲風淡淡應道,拿起碗,把所有花生都倒進嘴裏。
「唔紋唔似跟緊你吖嘛。」信一說,語氣刻意放得軟軟的。
「唔紋就唔似跟緊我㗎喇咩?邊個講㗎?咁低能嘅。」龍捲風的回應,隨意得像在搭理小孩子沒頭沒腦的說話,刻意不把對方的話當一回事。
「我講㗎。」信一答,收起了笑容,「你教我用刀、教我揸車,仲俾我做頭馬,但跟你咁耐,我做得最多嘅,都只係同你計數。」
信一知道,城寨內外都有人笑他不像「頭馬」,甚至不像黑道,像龍捲風的私生子,有些嘴巴髒的人,還在什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下,就嘲笑說是「一樹梨花壓海棠」,小情人被呵護得根本不會處理道上的事,看著也不太能打,哪怕天天拿著蝴蝶刀舞出花來,估計也打不過大老闆養的狗,要是哪天龍捲風下去賣鹹鴨蛋了,龍城幫肯定要倒。
想起這些說話,信一就忍不住暗地咬牙。
龍捲風盯著陷入了自己思緒中的信一,繼續四兩撥千斤:「計數唔好咩?」
「邊有撈偏嘅,日日淨係計數同幫師奶換燈膽㗎!」信一呶著嘴巴抱怨,抬抬下巴指向餐廳一角的燈,「揸螺絲批仲多過揸刀喇!」
聞言,龍捲風撐著收銀櫃靠近信一,忽地換上了冷硬的語氣,沉下聲詰問:「咁你想做咩?想賣粉?定想學人做埋製毒?撈埋蛇頭個範好無?」
信一立即怯了,知道對方真的有點生氣,於是收起了埋怨,弱弱地回應:「咁又唔係……」
掀起眼皮抬起目光,信一飛快地瞄了瞄龍哥的臉色,鞋尖踢了幾下地板,放在收銀櫃面的手握成了拳頭,本來抿住的嘴忍不住;信一邊看著對方的表情,邊小聲地解釋:「只係……只係想再幫龍哥你多啲啫。」
話音落下,信一聽到了一聲嘆息,夾雜了無奈、煩惱與憐愛。
「傻仔。」信一隱約聽到對方如此低喃。
「你幫得好夠㗎喇傻仔。」龍捲風搓了搓得意門生的頭髮,燙曲了的頭髮鬆鬆又軟軟的,不愧是自己燙的頭,燙得特別好。
見信一的嘴唇還是噘著的,龍捲風便笑了幾聲,笑聲從鼻尖哼出。他反問信一:「你估個個都幫到我睇住盤數咩?班友仔啊,五加五等於幾都要數手指,你又唔係唔知!」
信一也知道自家是什麼情況,也知道不少兄弟連字都沒認全,平常買汽水要算錢找續都要扳著指頭唸唸有詞,自然有點被說服了,但信一還是忍不住皺起眉頭,試圖做最後的掙扎:「咁紋……」
龍捲風抬手扶了扶茶色墨鏡,問:「信仔仲係好想紋身啊?」
「都……」信一支吾了一會後,還是老實地承認:「仲有啲咁啦……」
龍捲風嘆了口氣。
「如果聽日日光日白個陣,城寨無斷水斷電嘅話,我帶你去紋啦。」龍捲風這話才剛說完,信一便歡呼出聲,於是龍捲風便伸出食指,指著信一的鼻尖,警告兼恐嚇:「嗱,講明先,紋身好撚痛㗎!師傅會攞把刀仔𠝹落你皮膚度然後……」
「我唔怕!」信一這話說得擲地有聲。
他伸出手,比出的五字對住龍捲風,展示指掌間的疤痕,自豪地說:「刀傷咋嘛,我隻手練刀個陣都食唔少啦!」
教信一耍刀的是龍捲風,因此他指掌間的傷痕,也可以說是龍捲風給他的,因此為了對方而紋的刺青,不過是再多一道由對方送贈的刀痕,這次還鍍上墨水,以保永久。
信一的笑容實在壓不下來。
*
明天。
燦爛的太陽爬到天際的正中央,是城寨最為光猛的時間,在建築物之間狹小的縫隙裏,照出一道道亮光,撫過每一個剛好走在它底下的人。
信一的「信」字,是「言而有信」的「信」,「一」則是「一諾千金」的「一」,而他的老大,也同樣是言而有信又一諾千金的人。當日城寨既沒斷水,亦無斷電,龍捲風便在嘆了口氣後,帶了滿臉期待的信一去紋身檔。
紋身檔在城寨的一角,很小很小的一間店,在某大廈的最高層。天花板和許多城寨內的建築物一樣,破了個洞,照進來猛烈的陽光倒是確保了光源。店內充斥住奇怪的消毒藥水味,自一進門內便會聞到,而當信一坐到那張牙醫凳上時,怪味簡直把他包圍起來。
信一好奇地東張西望,又摸了摸身下的牙醫凳,而紋身師傅一見到是龍哥光臨,便立即低頭哈腰問安,並向他們遞來了一本厚厚的畫冊簿。簿裏面有很多圖案,全是紋身樣式,從動植物到神佛都有,還有些威風凜凜的兵器圖案,但信一才剛打開本子看了兩頁,龍捲風就從後把它抽走了。
省得這小孩看到心儀的圖案又蠢蠢欲動,拿自己的皮膚當畫紙亂紋一通。
那個年代,紋身和黑道在坊間眼中是劃上等號的,正派人士都不會紋,只有撈偏的特種行業人士才會,而龍和虎這種兇猛圖騰,更是只有黑道才會紋,還要講究樣式與意涵。
龍捲風不是不明白信一的心意,但他更加不想往身上烙了條龍的信一,未來就被自己局限住了,永遠都離不開龍城幫,哪怕有天城寨拆了,都得不到自由。他知道信一會說他不需要,但既把人當兒子疼、又把人當情人愛的龍捲風,無法不自以為是地,想要為信一留下更多選擇。
只不過他更清楚信一的脾性,愈是制止他,他就愈是會偷偷跑去做,說不定跑到不乾淨的地方去紋,那還不如由自己帶,還能封殺掉信一往自己身上紋奇怪東西的可能性。
站在牙醫凳旁,龍捲風按著信一的肩膀,把畫冊還回給紋身師傅,低聲吩咐:「麻煩師傅喺佢後腰紋個『龍』字。」
龍捲風比了個手勢,姆指和食指虛虛地夾著,中間大概有三個指節的距離。
他邊示意著邊說:「細細粒咁就得喇,至於粒字係咩樣式,師傅你揸主意啦。」
一直仰頭望著對方的信一,眨了眨眼,耳朵聽清楚龍捲風的話,腦袋又慢慢消化完意思後,他先是張圓了嘴巴,然後笑容浮上他的臉,愈浮就愈多,於是乎嘴角慢慢拉起,最後忍不住咧嘴笑了起來,笑容燦爛得連牙齒都露了出來。
只不過,這笑容沒維持很久,就在紋身刀扎進他皮膚的那一剎,便如雪進水一般,消失得無影無蹤。
紋身店內迴響著痛苦的喊叫。
ns13.59.77.29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