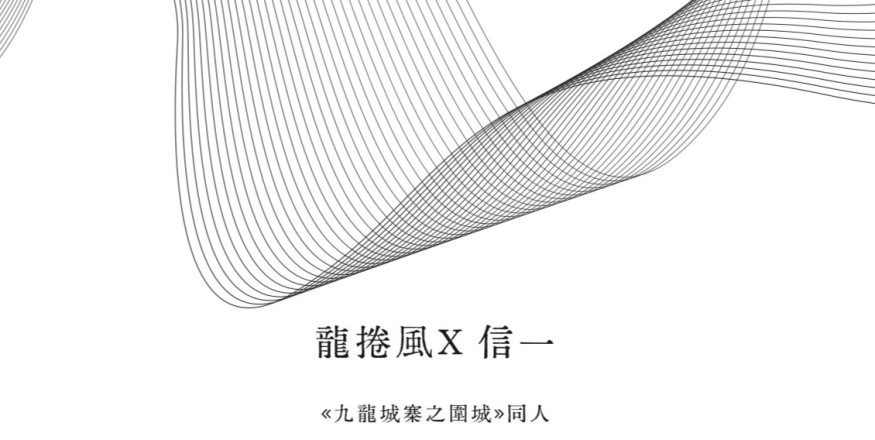銀剪開合,斷開的髮碎順著理髮袍滑落,無聲掉在花磚地上,繞著理髮凳灑下。鋒利的剪刀來到耳邊修剪兩鬢,細碎的喀嚓喀嚓聲響在耳邊,一隻溫暖的手掌輕輕按在額頭附近,伴隨一句湊得太近而像耳語似的叮嚀:「別動。」他說。
信一下意識屏住呼吸,閉上的眼睛又再用力了幾分。「麻煩龍哥了。」他說,聲量壓得太低而顯得乾啞。他藏在理髮袍底下的手,暗地握成拳頭,指甲捺在掌心,烙下四片半月,攥緊。
剪刀連續開合了數下,落下的髮碎擦過信一的臉頰,癢得不可思議,連心尖都一陣痙攣。
信一其實偏好短髮,畢竟夏天時城寨相當悶熱,就算搖著扇子都熱得受不了,要是還披著一把長髮,恐怕後頸都要捂出疹子來,更別說城寨常常斷水,連每天洗頭都難以做到。
那麼,為什麼信一的頭髮會愈留愈長呢?
閉上了雙眼的信一,聽覺變得更為敏銳,神經亦更加繃緊,光是龍哥擱下剪刀時那一下喀㗳聲,就讓信一忍不住抖了抖肩膀。
聳起的肩頭還未放下,就被對方搭著。信一感覺到對方捏了捏他,然後帶著笑意地問:「很緊張嗎?要你把頭交給我。」他撥了撥信一的瀏海、又順了順頭髮,用指尖梳理他剛完成的作品,嘆道:「我應該剪得還不錯吧,儘管可能不太跟到你們年輕人的潮流……唉,老喇老喇!」
聞言,信一連忙睜開眼,透過鏡子反射望向他的老大,慌忙否認:「龍哥剪的,就是剃光了我也喜歡!」說話時一雙濃眉緊緊糾到一起,緊張到喉嚨發緊,換來對方一聲輕笑。
意識到那老男人又在開玩笑,信一便抿抿嘴。他望向鏡裏的自己,掂起頰邊的頭髮,搓了搓尖尖的髮尾,心想這麼短的頭髮,要如何遮掩通紅的耳尖呢?以後還是留長一點吧,還要燙捲髮,燙得蓬蓬的,才能藏起動不動就發紅的耳朵。
按著扶手,信一矯了矯坐姿,翹起二郎腿又整了整髮袍,抖落一地髮屑。
信一的眼神游移著,轉了幾圈,才隔著鏡子偷看攪拌剃鬚膏的龍哥,用外人難以想像這會是出自信一嘴巴的語氣,怯生生地說:「我的鬍鬚其實也沒長多少,不剃……」龍捲風瞟了信一一眼,於是語句頓時變成了問句:「……不行嗎?」
「頭髮留著不剪,鬍鬚也蓄著不想剃,搞乜?」龍捲風擱下手上的剃鬚膏,走到信一身旁。他伸手,托起信一的下巴,姆指摩挲,指面被半長的鬍鬚扎著,「都長到快遮住嘴唇了,邋邋遢遢咁。」他說,眼睛睨著不知為何膽怯的門生,萬般不滿意一個年輕人搞得自己像個流浪漢似的,蓬頭垢面。
不理會靦腆得像突然回到小孩子似的信一,龍捲風倏地拉下理髮凳的拉扞令椅背猛地落下來,讓信一重心不穩往後倒。「乖,躺好。」龍捲風按著信一的肩,制止了對方的輕微的掙扎。他用的力度絕對不足以讓信一無法動彈,但渾身僵硬的年輕人,一向甘願作對方的俎上肉。
用熱毛巾敷過臉後,微涼的綿密剃鬚膏抹在信一的下巴,粗硬的刷子撓著他的皮膚。他又再閉上了眼,生怕看到站在斜後方的對方,向他投下專注的目光。
剃刀磨了磨後,貼到信一臉上,隨之而來的還有龍哥的手指。鬍鬚連同剃鬚膏,一點一點被刮去;龍捲風的姆指輕推著信一的下頜,拉直了他的喉嚨,然後刀鋒貼在頸側軟肉。「別動,不然一頸血時別怪我。」龍捲風習慣性低聲叮嚀,視線追著緩緩滑動的剃刀走,無比專注。
信一的睫毛忍不住顫抖,像要睜眼,但又不敢。龍哥靠得太近了了,信一可以感覺到對方在夏夜中散發的體溫,也嗅到了對方身上的煙臭、還有敷臉的熱毛巾在他指尖留下的花露水香,於是乎,他就連呼吸都要小心翼翼起來,生怕被對方發現自己有多貪戀這刻的空氣。
熱毛巾擦去殘留的泡沫與鬚屑,又解開了理髮袍的扣子。信一知道終於剃完了,於是睜開眼,撐著椅側想坐起來,沒想到肩膀又被按著。
信一瞠圓的雙眼,映著上下顛倒的龍哥的臉。
搭在肩膀上的手,拍了拍後,移到信一的下頜。龍捲風像在檢查剃得乾不乾淨般,姆指有一下沒一下地摩挲信一的頰側,動作有點像在摸養馴了的貓狗。龍捲風側頭,盯著他的門生。起先他沒有說話,拍了拍信一的臉頰後,他點了根煙,深深吸了口,呼出,讓白色的煙圈悠悠浮到半空了,才開口:「信仔,你很緊張?」他戳了戳信一的頸側。
緊張是理所當然的,一把由他人操持利刃貼在要害。
「啊?」信一眨了眨眼,心想這不是剛問過?怎麼又問了?難道龍哥終於開始耳背了嗎?於是稍稍提高了聲量回答:「不緊張啊,有什麼好緊張的。」
「那……」龍哥抖了抖煙灰後叼回嘴邊,然後一手按著信一的肩膀,一手拉起理髮袍的下擺。又輕又軟的理髮袍擦著信一的大腿往上挪,包在牛仔褲裏的雙腿下意識掙扎,於是搭在他肩膀的手,沿著胸腔往下撫至腰腹間按住。
「興奮嗎?」龍哥問,但語氣倒是帶著幾分篤定。
理髮袍被掀開了,信一翹著的二郎腿被龍哥推著,放了下來。整個人算是躺平在理髮凳上了,於是乎,凸起的牛仔褲褲襠便相當顯眼。信一低頭一看,耳朵立即紅得滴血,連忙夾起雙腿想要遮起來,但龍哥這時伸手,不輕不重的捏了捏帳篷的最頂端。
信一叫了出聲,半是嚇的。痛不怎麼痛,但拼命跳動的心臟倒是有點酸,酸到眼眶都跟著酸了。
被發現了。
會被趕出城寨嗎?信一絕望地想。
「剪個頭髮啫,你也太興奮了吧?扯晒旗喎信仔你。」龍哥邊抽著煙邊調侃,咬字含含糊糊的。手掌按著信一剛抬起的大腿,然後滑到內側,搭在褲襠的正中央。龍哥隨意地揉了幾把,隔著厚厚的牛仔布,但仍然換來對方幾聲嗚咽。
瞄了眼滿臉通紅的門生,龍哥勾了勾嘴角。「難怪一直不肯過來剪頭髮,又難怪之前竟然跑了出城寨外頭找別人剪……唉,傻仔。」他說著,搓揉的力度又加重了幾分。
信一仰起頭呻吟,後頸緊貼在皮革製的椅背上,體溫捂得皮革都不再冰涼。
寨外的不知道,但城寨裏的妓院都是龍捲風管的,哪個門生哪個手下跟哪一位妓女交易過,他通通都知道,所以龍捲風很清楚信一沒叫過雞,至少城寨裏沒有,而且跟在他身邊這麼多年,由未成年到毛都長齊,也沒見過這小孩牽過什麼女孩子的手……男孩子的也沒有。信一有過的唯一性經驗,恐怕都是從四仔的店裏看過的成人愛情動作片……龍捲風還記得,最初信一還不願踏入四仔的店,耳根紅透的小孩不曉得該把眼睛往哪放。
信一的眼睛很快就濕了,龍捲風猜他的內褲也一樣。兩三下解開皮帶扣,拉下牛仔褲到膝彎。內褲是白色的,純得有點可笑又有點符合期待;勃起的陰莖撐得連內褲都貼不住皮膚,頂端已經濕了,兩側橡膠圈隱隱露出底下的莖身或囊袋。
熱得滾燙的臉頰被輕輕扶著,腦內一團亂的信一,順從地跟隨力度,側過頭。信一先是抬起眼眸瞄瞄龍哥的表情,然後才把視線放回前方,看到逐漸撥開的皮帶扣、解開的鈕釦、拉開的褲鏈,脫下的內褲露出一根半勃的陽具。
信一下意識抿住嘴唇,臉頰又再紅了幾分;他抬眸瞄了瞄龍哥,然後才伸長脖子,拿嘴唇湊近紫紅的龜頭,學著從四仔店裏不經意間看到的影片,試圖含啜,但嘴巴張大到極限,都只叼得住前端。
罵人含撚罵過不少次,但真的含嘛,信一自然是第一次。他蹙起眉頭,有點不知道該如何伺候嘴裏的東西,躊躇了半晌,才試探性地捲了捲舌頭,抵著包皮繫帶來回地舔。
龍捲風又再呼了口煙,按捺住慾火,讓信一自行摸索過一輪,並再次向他望來,眼露求助,才按著信一的頸,帶著人往前挪了挪位置,令信一的頭懸到靠枕外。信一的視野頓時上下倒轉,讓本著暈呼呼的腦袋因充血而加倍混亂。他感覺到自己的臉頰被捏著,方才稍微往外退的陰莖又回到自己嘴裏,從前端流下的不知名液體抹在自己舌面,於是信一反射性吞嚥,喉頭肌肉擠夾龜頭。
香煙這時總算被丟下了,落在磚地上被一腳踩熄。
龍捲風扶著信一頭顱的兩側,順著因倒吊著而拉直了的喉管,一路把自己的陽具往內擠,堵滿了信一的嘴巴還往食道塞。
第一次口交……第一次性交就被抓著頭吹深喉,這恐怕有點殘忍吧?龍捲風邊擺著腰邊想,晃動的囊袋拍打信一的嘴唇,咕啾咕啾的抽插聲,伴隨信一哽到反胃咳嗽但又被捅得無法順利完成的乾嘔聲。
從龍捲風的角度,他看不到信一的臉,只看到被操得通紅的下嘴唇、與在捅到最深時凸起的喉嚨。缺氧令信一的胸膛都通紅起來,龍捲風隨意揪撥了幾下挺立的乳頭,換得對方緊抓住他的大腿,但用的是指頭肉。難受極了,還是沒用上指甲撓個一兩下來示威。
又再搓了搓信一的胸膛,龍捲風抓著信一的頸,一下挺跨壓到最深處,陰毛都磨在信一的嘴唇上,壓得像要把囊袋都塞進他嘴裏似的。龍捲風悶哼了聲,然後就停在這裡,靠著對方的咽反應來按摩陰莖。很快,呼吸困難的信一開始顫抖起來,想要咳嗽但咳不了、想要嘔吐又嘔不了,所有難受通通變成淚涕橫流,鼻子甚至吹出一個鼻涕泡來,然而他下身的勃起沒因此而消下去,還硬得更加痛受。
信一嗚咽著,自己把手放到下身,隔著內褲用力搓著自己的性器,搓到痛了,才撥它出來握在掌裏圈著套弄。從前端流下了透明的液體,流過指縫間,最後滴到皮凳上。
死於為暗戀的大哥吸屌至窒息,這樣也算是心想事成吧?眼珠不受控地往上翻的信一暗忖,自慰的動作逐漸慢下來,最後手無力地靠在大腿上,發黑的視野卻能看到斑斕的螢光流轉,不知不覺間泄出來的精液,奇怪地像漏尿一般慢慢流下來。
人在窒息時,總是會下意識掙扎,哪怕是自行上吊的人,也會在最後一刻反悔似的用力抓撓脖子,怪就怪在信一在意識渙散了,連腿都沒多蹬一下,馴得可怕。
龍捲風動了動手指,後悔起太早把煙丟了,發癢的喉頭需要熱辣的煙霧。捏著信一的臉頰,沒打算真的操死得意門生的龍捲風抽了出來,眼見信一還呆張著嘴巴未回神,便拍了拍小孩的臉頰,收力收得連一點紅痕都沒扇出來。
回到陽間的信一連忙抽氣,一抽便嗆到,於是捂著嘴巴按著胸口一頓狂咳,咳了半晌都理不順氣來,咳到喉嚨生痛發熱愈咳愈癢。「龍哥……咳咳咳……」信一啞著聲的低喚,為了順氣他翻過了身,正用手肘支撐的趴在理髮凳上,配上水跡未乾的通紅的臉、淩亂的頭髮,樣子好不可憐。
被抽出的紙巾擦過紙盒邊,窸窣作響。龍捲風把紙巾遞了給信一,說:「擦擦臉。」信一慌忙道謝接過。紙巾在臉上輕印,信一半斂著眼,在長長的睫毛掩飾下,眼珠子忍不住瞄了又瞄;龍哥那泛著水光的肉棒就在他的臉頰附近,正握在它的主人手上,隨意地套弄著。
下意識舔了舔唇,信一暗忖,原來剛剛在自己嘴巴裏的兇器長這模樣,怎麼自己卻沒有被那些盤糾的青筋壓過舌面的記憶。
信一盯得入神,目光痴痴的,惹得龍捲風都要為他臉紅。托著信一的下頷,龍捲風仔細觀察他向來細心培養的頭馬,得到的是兩汪仍然寫滿信賴的柔軟目光。信一側過頭,用臉頰蹭著龍捲風的手掌肉,練武人粗糙的掌繭刮著信一柔軟的皮膚。
抬起眼皮,信一由下而上仰望他的老大,嘴角一彎,笑得像頭貓似的,同時伸手,輕輕攏過龍捲風的陰莖,上下滑動著,還伸出了舌頭,用舌尖挑逗馬眼,勾著那小孔;他手口並用,服侍這根欲勢待發的硬棒。
龍捲風深呼吸了一口,猶豫了一會,才把手按到信一的髮頂。他沒有按下去再逼信一深喉一次,只是用堪稱溫柔的力度,撫摸著柔順的髮絲,並用比動作更溫柔的語氣問:「啱先唔痛咩?」他方才可是刻意收起了憐惜心。
「唔痛啊。」方才咳到肺都快吐出來的信一死撐,還裂嘴囂張一笑,露出尖尖的犬齒。他拿大姆指一抹老大的龜頭,笑容和口吻都得意洋洋地說:「我知你想嚇我啫,無咁易啊!」
語畢,他又繼續埋頭苦幹,盲無章法地亂舔一通,像條過分熱情的狗。
話說得自信,但信一的內心只有連連苦笑,心想搞基都算了,作為一介門生的他暗戀自己的老大,沒大沒小,就是真的被屌死都是自找的,沒被一拳打碎頭顱都要偷笑了,哪想到龍哥竟然真的肯碰他,現在還有幾分繾綣的樣子,簡直是美夢成真。
信一掌裏的陽具忽地跳了跳,來不及收回舌頭的他,被熱精澆了一臉,部分還淋到舌面去了,浸到味蕾上。陌生的腥臊味溢滿了嗅覺與味覺,信一怔在原地,等到神色赧然的龍捲風替他擦臉時,他才回過神來,並且反射性地收回舌頭進嘴裏。
咕嚕一聲,信一吞掉了他的老大的精液。
ns 15.158.61.40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