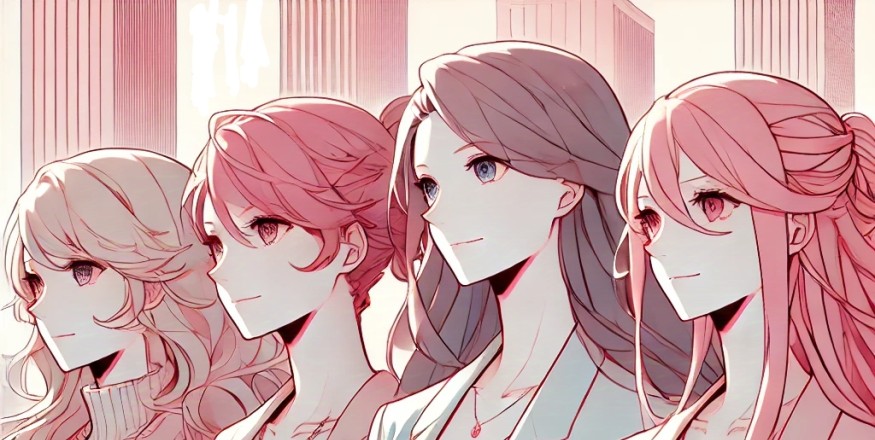冬天的寒風在大陸的鄉村裡呼嘯而過,樹葉早已隨著季節的變換凋零,只剩下光禿禿的枝頭在寒風中微微顫抖。十多歲的藝寶英坐在自家院子裡的小桌前,手裡握著一塊剛剛摘下的柿子,鮮紅的果皮在冬日的陽光下閃著光。她將柿子遞給身旁的母親,嘴角還帶著一抹天真的微笑。98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fhocqlzh2T
“娘,這柿子好甜。”寶英一邊咬著柿子,一邊笑著說。
藝母輕輕拍了拍她的頭,笑意盈盈地說:“你這孩子,總是知道挑最好的來吃。”
寶英的童年是無憂無慮的,家中雖不富貴,卻也算是小康之家,家裡有幾畝農田,偶爾還僱用傭工幫忙耕作。日子雖談不上奢華,卻總是平靜而舒心的。藝父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中年男子,沉穩寡言,對家裡的每個人都極其寬厚。這個家,曾是寶英心中最溫暖的港灣。
然而,這一切在那年冬天的某一天,隨著一陣暴風般的呼喊聲戛然而止。
那一天,寒風刺骨,空氣中瀰漫著一種異樣的緊張感。遠處的村口突然傳來一陣激昂的口號聲:“打倒資本主義,反對黑五類!”寶英猛然抬起頭,看到一群戴著紅領巾的青年,手持《毛主席語錄》,昂首挺胸地走向她們家。帶頭的是一個高大壯實的青年,神情嚴厲而冷酷,他的紅領巾在寒風中如同戰旗般飄揚。這個人名叫猛同志,是村裡新上任的革委會頭領。跟隨他的是兩個看似年輕的助手——昌同志和芸同志,兩人面無表情,手裡緊握著小紅書,眼神裡透著毫不掩飾的冷漠。
寶英愣在原地,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她的母親從屋裡衝了出來,站在她身旁,臉色蒼白,眼神裡滿是驚慌。她伸手將寶英拉到自己身後,低聲說:“寶英,快進屋去,不要出來。”
然而,就在她們即將關上門的一瞬間,猛同志已經帶著人沖進了她們的院子。他一把推開了藝父,冷笑道:“你這個地主的走狗,今天我們要來清算你這個資本主義的罪行!”
藝父猝不及防,被猛同志一推,身子便重重摔倒在地。他掙扎著爬起來,臉上滿是痛苦和屈辱,但還未開口辯解,昌同志和芸同志已經撲了過來,一邊高聲喊著“黑五類”的罪名,一邊將他按在地上,拳打腳踢。寶英站在一旁,驚慌失措,雙手顫抖著捂住了嘴,眼淚忍不住奪眶而出。她看著父親被打得毫無反抗之力,內心的恐懼像巨浪一樣席捲而來。
“毛主席萬歲!反對資本主義!”猛同志帶著一群青年,在院子裡肆無忌憚地喊著口號。他們將藝父拽到了屋前的空地上,強迫藝母和寶英也一同站在那裡,逼迫她們一起高喊“毛主席萬歲”。藝母眼中滿是無奈與痛苦,她緊握著寶英的手,眼淚在眼眶裡打轉,卻不敢反抗。
寶英的心裡充滿了無助,她看著父親那張被打得青紫的臉,心裡的恐懼與憤怒交織在一起,但她卻什麼也做不了。她只能跟著母親一遍遍地喊著“毛主席萬歲”,每一次喊出這句話,她的心就像被刀子割了一樣疼痛。
“這家地主剝削人民,囤積財產,我們要把他們的財產充公!”猛同志大聲喊道。他帶著人衝進了屋裡,翻箱倒櫃地搜刮著藝家的所有財物。每一件物品都被他們丟出屋外,像垃圾一樣堆在地上。藝母站在旁邊,無能為力,只能緊緊攥著寶英的手,顫抖著不敢作聲。
“這些都是人民的!”芸同志手裡抓著藝母珍藏的一些首飾,冷冷地說,“你們這些地主階級,罪該萬死!”
寶英的眼淚再也忍不住,一顆顆掉落在地上。她感覺到整個世界都在崩塌,曾經溫暖的家,如今被踐踏得一文不值。她無法理解,為什麼原本快樂的生活會在一夕之間變成這樣。
當天夜裡,藝父被革委會抓走,幾天後回到家時,已經是奄奄一息。他的身體瘦弱得不成樣子,臉色灰白,雙眼無神,顯然已經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幾個月後,他鬱鬱而終,帶著無盡的屈辱與不甘離開了這個世界。
藝母抱著藝父的遺體,哭得撕心裂肺,寶英則站在一旁,整個人仿佛被凍住了一樣,眼睛空洞無神。那一刻,她感覺到自己失去了所有的依靠,這個曾經溫暖的家,再也回不去了。
幾個月後,文革的風暴依舊席捲著大陸各地,藝母終於做出了艱難的決定。她用盡了自己偷偷藏下的一點錢,買了一張通往深圳的火車票,將寶英送上了前往深圳讓朋友帶領轉往香港的路途。她深知,這場政治風暴並不會很快結束,寶英留在這裡,只會跟著她一起遭殃。
“寶英,聽話,到香港去,這所有我都安排好了,到香港後找你母親的朋友幫助,她欠我人情…總會幫忙。”藝母的聲音裡帶著一絲顫抖,但她依然堅定,“在那裡,至少你能避開這場劫難。走吧!”
寶英望著母親那雙疲憊的眼睛,心裡湧起無盡的悲傷。她知道,這一去可能再也見不到母親了。她想拒絕,想留在母親身邊,可是母親堅決的眼神讓她無法說出任何反抗的話。
那一天,寶英帶著小小的行李袋,裝點衣物和金錢,和母親告別,踏上了前往深圳的火車。
火車轟鳴著駛入寒冷的夜色中,寶英透過窗戶,看著遠處的村莊漸漸消失在黑暗中。她心裡的孤獨感越來越強烈,淚水模糊了她的視線。那一晚,她無法入眠,思緒如同寒風一樣在她的心裡肆虐。
幾天後,寶英跟著母親指示在深圳邊界與幾個素末謀面的人攀山越嶺,當時香港實行的是「抵壘政策」,這是指大陸移民如果能成功越過邊境、到達香港市區,並且在政府清查前找到住所安頓,就可以申請香港身份證並獲得合法居留資格。只要能“抵壘”進入香港市區,成功定居,便可合法化身份。
輾轉她到達了香港,這個她從未踏足過的城市。
六十年代尾的油麻地仍在海旁,那是香港充滿煙火氣的老城區。狹窄的街道兩旁擠滿了各式小販攤位,賣著水果、蔬菜、魚肉,空氣中瀰漫著混合的潮濕海風和市井煙霧的氣味。老舊的樓房擁擠不堪,晾衣繩索衣竹在樓宇之間穿梭,像一張張凌亂的網。大排擋燈光昏黃,四周瀰漫著食物的香氣,燒烤的煙霧在空氣中氤氳。那些簡陋的木桌椅隨意擺放,帶著一種粗糙的實在感,彷彿不在意精緻,只求一個飽腹的去處。小販們穿著汗漬斑斑的圍裙,手上拿著熱騰騰的碗碟,來回穿梭在忙碌的攤檔間。人們一邊大聲談笑,一邊舉杯暢飲,嘈雜的聲音像是老香港這座城市的另一種脈動,熾烈而喧囂。摻雜著粵語的吆喝聲。街上的行人匆匆而過,忙碌的腳步似乎永遠不會停歇,整個區域流淌著城市的韻律。
對寶英而言,這裡充滿著一種她無法理解的市井味道,似乎每個人都在忙著自己的生活,沒有誰會注意到她這個孤單的女孩。燒肉的香氣在空氣中翻滾,然而對寶英來說,這香氣並不引起饑餓,反而讓她感到一絲惶恐。她不習慣這樣的喧鬧,這裡的每一張陌生的臉、每一句粵語的吆喝,都似乎在提醒著她,她已經不再是那個熟悉的家鄉女孩了。
街道上人來人往,繁忙的車流和熙熙攘攘的人群讓這座城市顯得喧囂而陌生。
就在寶英愣神之際,一聲粗獷的吆喝從身後傳來:“讓開𡃁妹!”她猛然回頭,只見一架滿載著貨物的木頭手推車直直朝她推過來,車後是一個赤裸上身、滿身汗水的大漢,粗壯的手臂正用力推著車,身上斑斑汗漬映著昏黃的燈光閃亮。寶英慌張地往旁邊一閃,整個人驚得手足無措,心跳如擂鼓般砰砰作響。那聲吆喝在她耳邊迴盪,像是這個城市粗魯而陌生的問候,而她,在這喧囂的人群中,忽然覺得自己無比渺小。
寶英提著行李袋,穿梭在廟街的街道上,四處張望著,眼神裡寫滿了迷茫與不安。她手裡緊緊攥著一張已經有些皺巴巴的紙條,上面寫著一個陌生的地址——廟街193號。街上的人來來往往,每個人都步伐匆匆,沒有人在意她這個小小的身影正在惆悵。
98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in3rmod63N
她鼓起勇氣,走上前問一個男人:“請問,怎麼去廟街193號?”她的聲音帶著濃重的鄉音,話音剛落,男人挑了挑眉,嘴角微微勾起,冷笑了一聲:“哎呀,大陸妹來嘍!不知!自己找!”他帶著一絲輕蔑轉身離開,寶英的臉瞬間漲紅,心裡滿是委屈。
98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2JG2mFbdJ2
接著,她又連續問了幾個路人,卻無一例外地遭到嘲笑。有人裝作聽不懂她的話,有人忍不住在她背後竊竊私語:“近來這麼多大陸妹,還一身臭味!”
98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6x41K8zfgB
正當寶英心裡越來越絕望的時候,一個熱心的嬸嬸走過來,拍了拍她的肩膀,笑著說:“哎呀,小姑娘,不用怕,我帶你去吧。”嬸嬸的聲音溫和,眼神裡透著慈祥。寶英點點頭,低聲道謝,心裡一塊石頭總算放下了一些。
98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O1B1YezGvc
她跟著嬸嬸,走過幾條狹窄的小巷,來到了那條有些昏暗的樓梯前。站在那黑黑的小門口前旁邊還掛滿了小信箱,門頂小牌寫著廟街193號,寶英仰望著這棟老舊的樓房,心裡不禁一陣緊張。她向嬸嬸道謝轉身深吸一口氣,走上那條又暗又窄的樓梯,每走過一層的門口都掛著一盞小紅燈,每一步似乎都在帶著她離開過去的生活。當她終於站在紙上所寫的門號前便輕說“就是這間”,輕輕敲了敲那扇木門,心跳得像是要從胸口跳出來。門裡傳來細微的腳步聲,寶英的手心已經被汗水浸濕,她不禁屏住了呼吸,等待著那扇門的開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