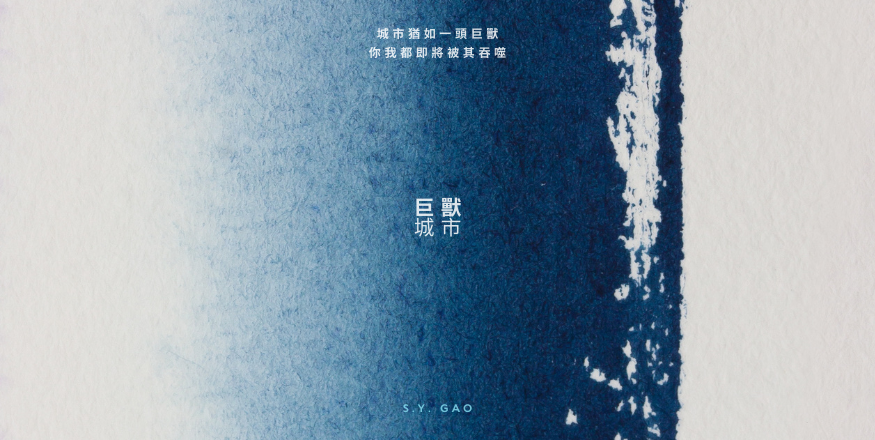疫情下的台北,唯一不變的就是雨天。若要說還有什麼,那就是飛出不去的台北人,讓城市變得更加擁擠了。
一年中,台北有近一半的時間陰雨連綿,整座城市浸泡在雨水中。越往北市的邊陲,木柵、景美;再擴及到大文山地區的新店,滴滴答答的程度更勝市區。積水的人行道雨坑、曬不乾的衣服,空氣中的陰溼像蠕蟲般鑽入五臟六腑,讓人白天夜晚都渾身不對勁。若是到了梅雨的季節,可能個把月都烏雲罩頂,看不見一縷陽光。
光對人類情緒影響的作用方式如下:當光線進入了視網膜,大腦會開始釋放血清素使交感神經處於活躍的狀態,進而讓人感覺活力充沛;接著,陽光會進一步的抑制大腦分泌一種使人昏昏欲睡的物質—褪黑激素。這種由大腦內松果體生成的荷爾蒙,當人體在接近入睡時便會開始分泌,並在深夜時分濃度達到高峰,隨著睡眠時間的拉長,直至早晨醒來前逐漸下降。
因此,長時間沒有接觸到陽光,容易讓人鬱鬱寡歡。
然而據研究顯示,接觸陽光的時間太長,造成褪黑激素的分泌不足,也會使人情緒焦躁。
當然,這只是其中一個造成台北人焦慮的原因。
台北的人口稠密度位居全台之冠。在這27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著兩百五十一萬人口。位於亞熱帶地區的台灣屬於海島型氣候,在六至十月的夏日,每口吐納間都是一股炙熱黏膩。方便的交通和生活,只是人們容忍自己棲身在這萬頭鑽動城市裡的唯一理由。日復一日緊湊的節奏、追趕不上的房價和物價、龐雜的交通和紊亂的市容,是刻印在居民心底,無數個深淺不一的溝壑,裡頭積滿了整個台北的雨水。而這座城市裡大小街巷的每一張面孔,不分晝夜、萬頭鑽動,冷漠疏離卻又充滿張力。
一早塞在車陣中,莫凡用手指敲擊著方向盤。川字型的紋路擠兌在她的眉宇之間,她已經看著前方黑色保時捷休旅的車牌好一陣子了,時間長到感覺那串數字已經深深地烙印在腦海中。6666,8888或是9999,差不多的排列組合,諧音是台灣人喜歡的音韻,透著吉祥富貴,展示著車主的身價不凡。
細密的雨珠啪嗒啪嗒的打在擋風玻璃上,被雨刷無情地抹去。但明朗的視線在轉瞬間又被不斷落下地雨花給淹浸成一團模糊。車內播放著Gnarls Barkley的〈Crazy〉,取代往常聽的FM99.7。那緊繃著肺腑力竭的嘶吼,讓她感覺自己好像也快被逼入了同樣瘋狂的絕境。她抬手關上了音響。
她是喜歡雨天的。然而情境卻該是在家裡,該是雨滴像吉他撥弦的那種節奏。她能沖上一杯飄著白煙的咖啡,放上Lo-fi曲風的音樂,再攤開一本書。能蜷著身子,將自己浸潤在那份愜意裡。外頭濕冷而室內溫暖乾爽,簡單微小的讓人五感饜足。若能隨心所欲的依著天氣好壞而選擇是否要外出,那陰雨的時節竟一點也不讓人感到煩悶。
因此上班時間的雨是全然相反的感受。因著雨天,塞車的情況更是雪上加霜。
手機響了。鈴聲穿插著雨滴淋瀝的聲音,看了眼來電顯示,她不耐的拾起電話,語氣不善。電話那頭的人語調卻是一派輕鬆。令人沒來由的感到更加惱怒。
「等等有沒有空?找妳拿上次忘在妳車上的電子菸。」
莫凡瞄著路口的警察,邊低頭滑著行事曆。通常她是不需要時常進辦公室的,更不會在周一的早晨出現在氣氛低迷的辦公空間之中。在一個短短的周末之後,連平常最親切的同事也顯得心事重重。一句簡單的早安都是氣猶若絲。彷彿被人拎著領口,卡的難受。今日難得一早出門打算進辦公室一趟,但那份心血來潮卻早已被細雨沖刷的一乾二淨。今日就不進去了。她心裡想著,邊和話筒裡的人約好了等會見面的地點。
「別遲到!」朝著話筒吼完,才發現電話早已掛斷。
路口的燈號已變換了三次,車子一寸都無法前進。她意識到自己已不再需要同一旁同樣動彈不得的車子一樣對眼前的號誌望眼欲穿,於是毫無眷戀的直接轉進旁邊的小巷調頭駛離。
不到九點就抵達了目的地。眼前的白色鐵柵門並未關牢,留下了一道小小的縫隙。莫凡伸手拉開了鐵柵門,拾級而下,推開了地下室的內門,立刻被撲鼻的甜香包裹住。
「哇,好香!你今天烤什麼?」莫凡朝著裡頭的人說。
「又翹班。」阿蘇站在烤箱前,頭也不回的說。
第一次踏進Chat,裏頭播著老鷹合唱團1977年演唱會版本的名曲〈Hotel California〉,間奏的獨奏分分鐘不停歇似乎旨在貫穿聽者的四肢百骸,打通阻塞已久的任督二脈。莫凡一直都喜愛這首歌所傳達的意念。直到她猛然回過神,才發現自己不合時宜地佔用了店內的一張四人桌,自顧自地陶醉在旋律裡,桌上空蕩蕩連個水杯都沒有。
她匆匆地走到櫃檯掏出了錢包,語帶歉意的向櫃檯的人要了菜單。
「Relax,」一雙清澈的眼睛對上了她的視線,阿蘇合起書站了起來,「You can check out any time you like, But you can never leave.」
10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rEHieSS33Y
人體的本身似乎會散發出一種奇妙的磁場或是能量。說來玄幻,因為摸不到觸不著,肉眼更是無法窺伺。這股若有似無的能量在不同的個體之間無形的淌流,逐漸擺動為調性相近的頻率。因此也許可以稍微解釋,為何人們會在初次見面就對某些對象立刻產生難以名狀的好感,相同的,也會對某些對象感到不由分說的厭惡。
不需要多餘的互動或言語,莫凡知道自己喜歡眼前的人。初次邂逅是順路經過,而接下來的每一次都猶如受花吸引的蜂蝶,目的地明確,毫無猶疑。小店沒有招牌,通往地下的樓梯狹小又短促,外觀難以判斷這空間的調性。門推開的第一個感官經驗即是咖啡的香氣混雜了曠野的氣息,明亮粗野的充盈了整個鼻腔。再注意到室內的陳設古舊性格,極具巧思,則是第二個感官饗宴。對莫凡來說,要不是氣味的分子通過了腦內的突觸經過杏仁核處理後,在海馬體內引起的一段晦暗卻溫暖的模糊記憶;和老鷹合唱團的歌曲搶先在她的瞳孔適應昏暗的光線之前就攫住了她的思緒,她會認為自己的出現既突兀又詭異,像是打亂了這個空間中某個恆久不變的定律和規則。
聽見阿蘇的話,莫凡咧著嘴笑,等同於默認。脫掉鞋子,隨意套上了一雙室內鞋,往老位子走去。
「中午有紅燒肉。昨天晚上燉好的。」阿蘇對料理食物自有一套堅持,他相信美食能化解生活中大部分令人著惱的事。
莫凡拉開吧台的椅子坐下,「先給我來杯咖啡吧。塞車塞的我真的暈頭轉向。」
「昨天叫了一批新豆,等晚點送來妳再喝。先喝我這壺茶。」阿蘇彎腰拿了個小巧的茶杯,斟了八分滿,端到莫凡眼前。
她低頭湊近嗅了嗅,茶香撲鼻,她嗜咖啡的癮頭轉眼間消散,立刻改口要了壺茶。
阿蘇拿出了一只陶壺,精準的秤了茶葉的量,蜷曲的茶葉輕輕脆脆的落在壺底,很是好聽。98度的熱水蒸氣裊裊,乾燥的葉片緩慢地在水中舒展開了,茶香四溢。淺淺的茶湯初飲有明顯柑橘香,而後帶著一股淡淡焦糖氣味,喉韻有力。她品著茶,突然想起從未看過阿蘇喝咖啡。
「苦。」阿蘇說著,抿了一口茶,「不過咖啡的香氣我倒很喜歡。」
「苦可以加糖呀!」莫凡忍不住笑了。
「同樣是要高溫沖煮,但是咖啡豆卻要先經過細細的研磨才能使用。還會因著研磨出來的粗細度,有不同的風味表現。」阿蘇邊說邊替自己和莫凡倒茶,「人啊,就像這一顆顆的咖啡豆,各自有著不同的形狀。有些比較圓潤、有些比較細長、有些大有些小,直到被生活磨碎、碾壓,變成細細的粉末。沖煮咖啡的熱水,就像是生活之中所遇到的各種困難和壓力。」他嘴邊帶著微笑,「沖咖啡是去蕪存菁的過程,沖煮出來的精華在別人鼻子前飄香,但喝下去的苦澀只有自己知道。」語畢,烤箱上的計時器響了,阿蘇轉頭檢查爐子裡的糕點。
莫凡覺得阿蘇的形容很有詩意。然而咖啡天生的苦味更彰顯那各種風味變化的價值所在。而加了糖之後,再怎麼苦的咖啡也都變甜了。若說人生像咖啡,那這些咖啡之中所帶著的花果香、蜜香,更是苦中帶樂的滋味。
而糖呢?那便是更加崇高的東西了。好比金錢,好比權力、好比地位名聲。總之加了糖的人生,也就不苦了。
「糖吃多了會得糖尿病。」阿蘇從烤箱拿出了剛烤好的戚風蛋糕,澎澎的蛋糕體,像雲朵一般。「糖對懂得品嚐咖啡的人來說並不是必須。」阿蘇將蛋糕倒扣過來,免得消風塌陷,「不過話又說回來,喝咖啡的人這麼多,真正懂得品味的人又有多少。」莫凡點點頭,聽著窗外淅瀝雨聲,沒再回話。
台北的雨,好像永遠下不完。
阿蘇回過頭打開了冰箱,裡頭整整齊齊的,所有的食材清清楚楚地依照種類放置在保鮮盒裡。
莫凡低頭看了下手機,發現公司的群組發來了好幾條訊息。點開本週最新業績進度,眼見自己的名字落在表格的最下排,難以釋懷的煩躁一湧而上,她索性將手機螢幕面朝下的蓋在了桌上,眼不見為淨。
「早餐吃了嗎?」阿蘇整著工作台面,方才烤蛋糕那柔柔軟軟的氣味鑽入莫凡的鼻子。
氣味是唯一能直接進入人類大腦掌管情感和記憶中心的物質。某些特定的氣味甚至能夠勾起那些早已散佚在腦海深處的回憶。但嗅覺的品嘗是最難以名狀的感官活動,正因為氣味難以精準的被記錄,也難以輕易複製。
她眼巴巴的看著阿蘇,然後搖了搖頭。早先原想到了辦公室再打算,沒料到雨天打亂了她整天的計畫。直到阿蘇問起,她才發現自己早已餓的胸貼背。
阿蘇再度打開冰箱,拿出了一條櫛瓜、幾尾蝦子、雞蛋、奶油、起司片和吐司。將平底鍋放在爐火上燒熱,放入了拇指般大小的奶油塊。冰涼的固體奶油被滾燙的鍋子給融化成了淡黃色的液體,濃郁的乳香四溢。阿蘇在鍋裡放入了蝦子,隨後流利的將櫛瓜切成了薄片放入鍋內,最後打了顆蛋進去。
莫凡隨手拿起了櫃檯前的菜單。菜單的第一頁只寫了兩句話:“善於等待的人,一切都會及時來到。”—巴爾札克;另一句則來自羅曼羅蘭:“尊重別人並不是圓滑,而是一個人應有的禮貌和謙虛的表現。”
「客人要求我的品質,我也能要求客人的素質。」某次莫凡好奇的詢問得到了這樣的答案。
「在我地盤這你就得聽我的。」阿蘇輕快地哼唱道。他的回應讓她意外的笑了出來。她認得那是周杰倫的歌。
「叔本華說:“世界在音樂中得到了完整的再現和表達。 它是各種藝術當中第一位,是帝王式的藝術。能夠成為音樂那樣,則是一切藝術的目的。”」他拿著手沖壺細細的在咖啡粉上畫著圓圈,「所以我什麼音樂都聽,就像我什麼書都看是一樣的。個人喜好是一回事,原因在於只要接觸夠多,才擁有分辨優劣的能力。」
不一會,一盤豐盛的早餐端到了莫凡眼前。她衝阿蘇咧了咧嘴,拿起叉子開始大快朵頤,滿足地點頭如搗蒜,彷彿盤裡裝的是什麼樣的稀世珍饈。
阿蘇轉身繼續整理他的檯面。他的身材修長,瞳孔的顏色很淡,不少女人都說他長得很好看,無害、優雅。她們語帶眷戀地說他眉宇間散發著的憂鬱氣息吸引著她們;但是她們又說,他太有距離感。總是若即若離。她們嘆著氣,眼神繾綣地卻離不開他。總歸的說,是那難以看透的神秘,讓她們總對他懷抱綺旎的幻想,想更近一步的親近他。
阿蘇習慣性的早起。通常在最後一滴露珠被陽光蒸乾之前,他已經完成了早晨的閱讀。有時他會很早就到店裡準備,但偶爾也會沒來由的店休;有時突如其來的營業到深夜,有時又心心念念的想起清早晨讀後續的章節,而早早打烊回家。他的客人早就明白了他的不按牌理出牌。從來不會因為這樣獨有的營業模式而有所不快。若真要說明那種感覺,應該說是帶著遺憾的殘念又混雜著些許的思念。
阿蘇喜歡眼前的女人,但不是那種男女之間的情愛。他喜歡她毫不矜持的作態和不加掩飾的個性。早晨的時光對來任何人來說都是私密的,甚至有些脆弱。這樣的狀態像處在一顆充滿空氣的泡泡,與現實世界只隔著一層由細小水分子鏈聚起來的薄弱屏障,霧裏看花,如夢似幻。在它破裂之前,意識都還能與夢境保留著一絲聯繫。因此消散時更令人感到無限惆悵。大部分人會被現實世界粗野的跩出泡泡之外,可能是走在馬路上趕時間的汽車鳴喇叭的聲響,或是捷運車廂關上前的蜂鳴聲。伴隨著“啵”的一聲,泡泡破裂。而裡頭的人全然赤裸,靈魂備感徬徨,猶如新生兒呱呱墜地時一樣無措。
阿蘇不喜歡這樣的時刻。而莫凡的出現卻從未令他因此感到不適。她輕飄飄的就走進了他的泡泡裡,往往讓阿蘇好一陣子才發現自己已經在泡泡之外。因此他欣然允許她時不時的突然闖入他寧靜的早晨。
他用修長的手指輕輕測試著蛋糕模外的溫度,還有些微燙。轉過頭,順手收走了桌上被掃空的盤子,放到了水槽清洗。
ns3.145.32.50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