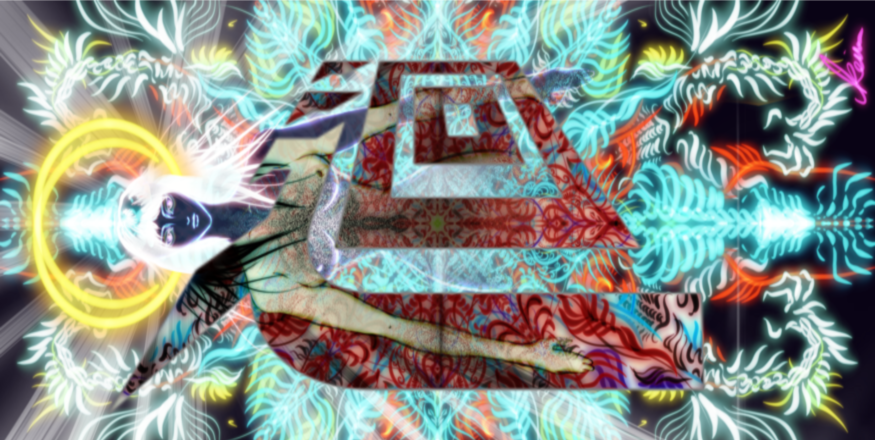第二天,我人到了學校,魂卻還留在那面長著黴斑青苔的牆面上的小窗窺視著。
以我射精為分界點,昨晚後半部的記憶完全一片空白,我怎麼回家的、幾點就寢的完全都沒印象,早晨醒來後忘在店裡的背包安然地被放在房間的門外。
在晨光中我把包包打開,將鑰匙及錢包擺到了抽屜上鎖好一陣子的書桌上,就在這當下我發現身體中心裡出現了個黑色的洞,那個洞以強大的吸力將四周的東西捲入其中,我注視著那個洞的深處,卻什麼也看不到。
中午吃飯時旺仔照例拿著福利社買的麵包坐到了我對面,他是同學中少數跟我說話時不會死盯或避開我眼睛的人。
「你今天怎麼一整天這張死人臉啊?」他咬著似乎很硬的排骨說。
「沒有啊。」
「該不會是在擔心世界末日來的時候還是處男吧?哈哈……」
因為正值世紀末的關係,各種關於世界末日的話題在媒體的炒作下正迅速地蔚為風潮,以聖經密碼、瑪雅預言、諾斯特拉達姆斯的《諸世紀》為主題穿鑿附會的書更是寧爛勿缺地佔據書店的熱銷區。最近還有什麼千禧蟲將會讓全世界電腦當機,文明整個倒退之類的。
不只是末日,也許是集體性的焦慮產生的歇斯底里,各種怪力亂神的都市傳奇及鬼故事也在短時間內暴增,第四台的靈異節目一台接著一台馬拉松式的播出,不論時段都有近十個頻道在播出各種湯藥都不換的靈異節目。
「末日時是處男並不可悲,可悲的是因為末日時因為身為處男而感到可悲的人。」我說,食不知味地咀嚼著黃色的醃蘿蔔,學校福利社的便當不知為何每天不管什麼菜色都要配一片這種黃蘿蔔。
對現在的我來說世界末日什麼的都無所謂了。
「你在說啥啊?裝什麼酷啦!」旺仔不屑地說。
「對了對了,你聽過了嗎?」他像是突然想到什麼壓低了音量。
「聽過什麼?」
「『多賀神社』的事啊!」
多賀神社是日據時代遺留下來的神社,位於市區中央的小丘陵的半山腰處,由於年代久遠,本身的結構已經接近半頹傾的狀態,但鑑於其具有歷史意義,鄉公所定時會進行維護,只是不知是預算有限還是官僚體系的問題,所謂的「維護」至多只是在破洞處以浪板補強,也因此使得其外觀變得更加寒愴畸形,退色的鳥居及神社境內靠左側姿態真實的銅馬配上四周荒草瀰漫與蒼鬱的樹林,就算是白天,整體還是透著幾分異於常世的荒蕪之氣息。
也因為如此,關於這看起來已不存在任何神明的破敗神社的怪談可以說我是從小聽到大,應該說住市區的小孩多少都聽過。
像是那隻側身畫著斑駁舍紋抬起左腳昂首的銅馬,據說一到半夜便會眼露紅光發出嘶嘶聲,甚至離開臺座在山林中奔跑,因為那隻銅馬裡面其實是一隻真正的馬,是被日本人抓去實驗作成銅像的。
還有離神社有些距離的那個積滿黑乎乎的髒水的防空洞,不但不時會傳來說話的聲音,還會閃現詭異的光。
當然不免俗地,這種地方一定會有日本軍人鬼魂在半夜行軍與被日軍砍頭四處找著頭顱的無頭孤魂等傳說。
連最近人氣極高搞得全國人心惶惶的紅衣小女孩都參了一腳,許多人都說在這間看起來欲倒欲塌的神社四周目擊到了她的倩影,還有幾個人因此喪生芸芸等虛實難分的傳言。
至於旺仔指到底的是哪一個我還真的不知道,而且這些故事大多都是以訛傳訛的無稽之談,於是我意興闌珊搖了搖頭。
「就是那個防空洞啊,聽說直通地獄喔!」
「爛死了,拜託,你都幾歲了還信這種鬼話。」
「是真的啦,隔壁班那個阿豪你知道吧?他說他哥跟朋友去那裏夜遊試膽,結果……看好多好多鬼從防空洞裡冒出來,根本是百鬼夜行,嚇得他們全部都要去收驚,然後那個倒是說那些鬼好像是在二戰時因為日本人的轟炸被悶死在裡面的老百姓……」
關於日本人在戰爭時到處轟炸的事也常常成為怪談的由來之一。
不等他說完我便起身將吃不到一半的便當倒掉走出了教室。
世界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變得這麼吵雜令人厭煩的?
5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9v7OYP9P2T
5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8LOz20SsyE
放學後我騎著腳踏車不斷在交錯的小徑與馬路間無意義地繞著,最後到了那座小丘陵,我將車停在了石頭階梯旁,踏上階梯往多賀神社走去。
今天是星期一,父親整天都在家,一想到必須與他獨處我總感覺快要窒息,完全不想回家,但又不知該去哪裡,之所以到多賀神社晃單純只是因為潛意識受到旺仔荒誕不經的故事影響,而且在這種冷風吹不停的時節,沒有比這個地方更適合現在的我獨處了。
我走上神社大殿,坐到殘破不堪積了層沙土與枯黃落葉的木階梯上。
開始轉暗的天空上方像是以堆疊法處理的油彩佈滿了厚重的灰雲,在風的撥動下大量的雲開始群聚,遠方聽得到微弱的雷鳴,搖擺的樹木沙沙地響著。
「嘿,你在這裡幹嘛?」
當我呆望著天上流轉著的雲時,旬的聲音從旁邊傳了過來。
我心跳在當下停了一拍。
旬從十一點鐘的方向走了過來,風吹亂了她像是小男生的短髮,她穿著貼身的黑色毛衣與刷白的牛仔褲。
「我剛剛去郵局,看到你的腳踏車所以就上來看看,沒想到你真的在這裡。」她說,手中提了個黑色旅行包。
不知為什麼看到她我感到了類似罪惡感的情緒,只好沉默地繼續望著天空。
她坐到了我旁邊,我們誰也沒說話,時間就這麼流逝著,烏雲終於完全佔據了天空,世界陷入了濃厚的昏黑。
「你長得跟Gibson真的很像,說你是外國人也不會有人懷疑吧?」她開口,提到了父親的名字。
我的右臉頰因為她的注視而有些發癢。
「你啊跟我是一樣的喔,是蝙蝠,有翅膀卻不是鳥類,長得像老鼠卻也不是獸類,什麼都像卻也什麼都不是。」
我有些疑惑地轉過頭去看她,她低著頭看著放在膝蓋上的修長手指,開始自顧自地說起她的身世:
「你知道嗎?我以前住在日本時只要在家跟母親都要用河洛話交談喔,她總是念茲在茲地告訴我她故鄉的一切,並且從小就教我說河洛話,由於河洛話跟日語發音方式很像,學起來並不困難。
我在潛移默化下曾經對沒見過的這片土地有份嚮往,但也許這只是逃避的反作用力,我以前在日本的學校時常被霸凌,也沒有朋友,總是一個人,雖然擁有二分之一的日本血統,但我總覺得自己不屬於那塊土地,我覺得我被日本排斥著。
而佔了我童年前半部分的英國也是如此,印象中我都是一個人在掛著白色窗簾的大房間裡玩著洋娃娃,窗戶外有著陽光與河流,還有其他小孩的歡樂笑聲,但母親從不讓我出去……我只能單獨在房裡跟叫Lily的洋娃娃玩著家家酒。
後來父母離婚時,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跟母親回來,但到了這裡之後後我才發覺自己也不屬於這裡,同學們因為我的名字對我抱以異樣的眼光,因為『松本旬』這樣的名字,有段時間不斷有人說我其實是拍AV的,而且還有語言的問題,雖然我本來就會一點國語但基本上還是河洛話說得比較好,但這塊土地的官方語言畢竟是國語,對於那時大多以河洛話跟大家交談的我,有人說我是日本來的假台妹,或說我根本是南部來的假日本人……我才發現這個世界不管到哪裡都一樣……」
她說話的同時,四周的風景之輪廓被蒙上了層深灰色調的薄膜瀰散在潮濕的空氣中。
「我之前一直以為『台灣』就跟『日本』或『美國』一樣是國家的名字,但後來發覺並不是這樣,台灣是地名,而這塊土地上的政權是『中華民國』。每個人似乎也對自己國族身分的認同存著相當大的差異,有人說自己是閩南人或客家人,也有人說自己是中國人,也有說是台灣人,還有外省人、原住民,然後原住民又分了許多族群,還有什麼平地山胞,不同區域的族群間也有許多難以理解的情結與對立存在,說真的我開始時真的完全進不了狀況,但現在也差不多,呵呵……
你知道台灣這名字的緣由是來自原住民語的『Taian』這個詞嗎?這是指外來者的意思,所以稱呼這塊土地為台灣其實挺諷刺卻又貼切呢!
我總覺得在你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你出生在台灣,卻擁有個洋人的外表……不算河洛人也不屬於日耳曼人的後裔……這樣的血緣其實痕『台灣』。」
說到這裡她突然靜了下來,而我則在聽了這番突如其來的身世告白後更加不知如何反應,那些糾結的語句在心中反覆輾轉著,並如寄生生物般啃蝕著臟器間的肉膜往深處爬去。
風越來越大了,緩步逼近的夜已經開始將一切往黑暗中收攏。
「你昨天在外面偷看吧!」旬說。
我吸了口空氣,寒冷的空氣帶著重量沉到了胃裡。
「你邊看著我邊自慰吧!」
風呼嘯在耳邊,我閉上了眼睛。
她對於我像個變態窺探著的行為生氣了是嗎?她是否會以激動的語氣指責我,或者告訴父親及阿雄呢?她抱持著什麼樣的情緒?丟臉?羞辱?厭惡還是……興奮?
而我又要抱持怎麼樣的情緒呢?
就在我陷入了某種自虐式的愉悅崩毀幻想時,旬冷不防地將手放到了我褲襠上,並用著適度的力道搓揉,我立刻起了反應。
我急忙地張開眼。
旬的臉在這瞬間佔滿了我的視線,天色明明已昏暗無比,但離我不到十五公分那張素淨又脫俗的臉卻發著幽微的白光,白光自光滑的肌膚內滲出,那光是那麼地神聖又皎潔,使得旬看起來彷彿充滿了神性像個女神。
「不要動!」她以溫柔卻又強硬的語調說,同時拉開我褲頭的拉鍊,緩慢而堅決。
5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rce2RkwnND
《維納斯的誕生》。
5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utjs54IJoT
拉鍊發出了喀拉喀拉的聲音彷彿透過了性能絕佳的擴音器般地響徹在這個被狂風與欲來的雨所包圍灰暗地世界中。
我硬挺的生殖器被旬柔軟的手握住,一種包含了脆弱與羞愧卻又迷人而讓人沉淪的情感衝擊著我的理智,她溫度熱燙的手掌濕濕滑滑地,彷彿那是她性器;那曾經接受了阿雄與父親的陽具的神祕場所延伸出的一部分……
她的唇也貼了過來,舌頭緩慢地堅決地撬開了我因緊張而死咬著的上下顎並探入了我的口腔,然後隨著手的動作在我的口腔內與我的舌頭交纏著。
雨終於落了下來,似有若無細如髮絲的雨點中我漸漸地失去了自我融化了。
時間的感覺從我身上被旬的舌頭與手給硬生生地剝離,不知過了多久微酸的快感凝聚在下半身後我射精了。
旬用舌頭舔了舔沾在她手上的精液,她的臉頰潮紅,但眼神卻有點落寞地看著我,本來散發著不屬於這世界上的光的臉龐黯淡了下來,只剩下模糊的輪廓與瞳孔裡白矮星般萎靡的微弱反射。
她從褲子的口袋裡拿出衛生紙擦掉沾染在我陽具上與她手上的精液,再細心地幫我拉上拉鍊又在我唇上輕吻了一下。
我們的身體都被雨點所打濕,皮膚的表面凝結著如朝露的小水珠。
「再見!」她將嘴靠在我耳邊說。
我這時才聞到一股淡淡的,漂白水般的味道。
等我回過神時她的身影已在細雨中消失了,只剩下微弱的漂白水味飄在鼻腔中……霧般的雨中迷離的景物讓剛剛的一切像是場曝光過度的照片,但殘留在我軟癱下體的微微痛麻感觸卻又甘甜得令人惆悵……
我站了起來望著旬消失的地方,卻只看到果凍狀黑暗中被風撥弄著的蒼鬱灰暗林影。
突然一陣劇烈的心悸襲來,太陽穴有種被什麼東西所瞪視著的刺痛感。
我轉過頭看向左手邊,在顏色不均的黝暗似乎有什麼潛藏著,那邊是一大片草叢,我記得再過去就是今天旺仔提到的……防空洞,被雜草埋沒失去作用與存在的理由,空虛地被深不見底的漆黑汙水佔據的舊時代裝置。
我瞇起眼往那邊看著,當然,除了及膝的草如剪影般稀疏的搖晃著外根本看不到那個因其特殊的歷史與地理位置而毫不意外地衍生了莫須有傳說的防空洞本體。
心悸越發強烈,奇怪的是我並不感到害怕,反而被熱烈的好奇心驅動著。
黑夜、狂風、細雨、破舊神社,要論氣氛的話十足到位。
我冷笑地想著,步下搖搖欲墜的階梯往防空洞方向走去。
就在我小心翼翼低著頭下階梯到地面上時,左手邊傳來了腳步聲與物體在草叢中移動地聲響。
本來不存在的寒意立即竄了上來將我那可說是過於驕傲自大的好奇心吞得一乾二淨。
我往聲音傳來的方向看去……
一陣奇怪的光芒從草叢深處閃過,光芒滅去後草叢多了一個東西。
原本空無一物的草叢多了個人影,高大的人影向這邊走了過來,步履有些蹣跚。
這時雨勢像是安排好似了變大了起來。
人影越來越近,我的腳卻像被濕濡的土壤吸住般無法動彈,視線也被無形的力道困住而無法移開逐漸逼近而越發巨大的人影。
之前聽過的,有關這裡的怪談一股腦地像是找到了施力點般從幽暗的記憶底層蜂擁而上……
終於人影離我不到兩公尺,但他的身影依舊籠罩在純粹的黑暗當中。
「啊啊啊啊……」人影發出了詭異的叫聲。
我不禁發起抖來,全身都嘩啦嘩啦地像是癲癇發作般痙攣地抽動著。
驀地,一道白燦的閃電劃過了天際消去了佔據四周的濃厚黑暗。
四處噴散的高光度白色不到一秒卻又被濃稠如瀝青的黑暗拖曳到了遠方並消滅。
我「哇」的慘叫了一聲,接著連滾帶爬地往山下衝去,但剛才所看到的,被強光從黑暗中強拉出的那雙看著我的眼睛卻深深地刻在腦中揮之不去。
那是雙茫然了無生氣的空虛雙眼,我甚至有種錯覺看到了映在那雙眼睛中的我自身的倒影。
但最讓我感到毛骨悚然的是……那雙眼睛內瞳孔的顏色,兩隻眼瞳的虹膜跟我一樣是一邊黑一邊藍,只是呈現的是如鏡像般左右不同……但雙眸主人的長相隨著滅去的強光在我心中消融沒有留下任何印象。
輪廓近乎被白光融蝕的超現實背景中捕捉到我的身影的那藍色的左眼與黑褐的右眼的畫面卻透過電光像是張負片般被執抝地刻印;並如同有了實體般嚙咬在我的腦中……
5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YnHV6Fs5Bz
5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KEk1BCe0KY
「你們在幹嗎?什麼味道這麼臭啊?」
母親略帶沙啞的嗓音震動了空氣,她略帶著不悅及煩躁的語調將我從記憶長廊中拉回了現實中。
此時此刻,父親與我正恍然若失地站在廚房,窗外是滂沱的大雨,我們的影子被身後帶著濁度的燈光向前拉長。
一隻如小貓大小,頭部變形扭曲冒著臭氣黑煙,醜陋如外星生物的東西陷入了種極大的苦難中正在我們前方顫動抽蓄著,牠張著皮毛捲曲焦黑的嘴露出尖銳黃齒發出著哀鳴……
咖哈咖哈咖哈哈哈……
像是在笑的垂死之聲。
充斥在空氣中的氣味與那聲音使得我胃液翻湧,酸氣從食道直竄上來,我吸了口氣壓抑想吐的衝動。
我轉過身去,母親就站在廚房的入口。
她雙手交錯在胸前,無框眼鏡後的眼神銳利地望向這邊,燈光映在她的臉上,並在眉間與上揚的下巴間拉出了道不深不淺的幽影,身上俐落的黑色套裝泛著絲質的光暈。
看到她那張塗著好似永遠不會脫落或退色的,如特製面具般總是完美呈現的彩妝的臉時,在《出埃及記》中讀過的句子浮現了腦中,只不過被置身事外的潛意識戲謔地篡改成了表達那死期將近的鼠的心聲之語句。
「你不能看見我的面,因為『鼠』見我的面不能存活。」
父親也轉了過來想解釋眼前荒謬的狀況之由來始末,但看來苦於找不到確切的詞語而嘴巴半張一臉呆然,像個做錯事的孩子卑微怯弱地看著母親。
母親先是望著我,然後像個視察著領土的郡主以冷冽的神色環視著眼前的事態,最後視點特別在父親手上的噴燈與黏鼠板上那隻大鼠轉了幾回。
接著她動作俐落地打開旁邊的抽屜拿出幾個桃紅色的中型垃圾袋,然後像是個芭蕾舞者動作優雅毫無多餘的舉止穿過父親與我用看起來如紙扁平還未撐開的袋子對折將聲息時強時弱的鼠覆蓋住。
完成以上的動作後─不到十秒─她推開了父親移動到了放置著噴燈的那個雜物櫃裡翻找著,終於,她找到了她要的東西。
那是個一體成形泛著金屬光澤的銀色器具,看起來像是鎚子,但又有些不同,「鎚」的部分是個扁平的正方形,兩側的面上佈滿了如鱗甲的小小錐狀物,是專門用來拍鬆肉片或排骨的工具。
母親拿著那工具走到了覆蓋著桃紅垃圾袋的鼠前蹲下,桃紅色的中央隆起看起來就像是什麼東西的繭或卵莢。
「阿愆,過來。」母親說。
有股不祥的預感,我不怎麼願意過去,但腳卻服從了母親的命令並自動蹲到她身邊。
「拿著。」
母親將拍肉用的工具遞給我,我的手也自動地聽從母親的命令伸了出去接過那閃著銀光的金屬器具,金屬特有的冰冷觸感握在手中像是塊冰,而且出乎意料的沉重,那是某種超越物理性質的重量。
「來,打死它。」
母親平靜的聲音夾雜著雨的聲音滑入了耳裡,就算有一定程度上的預感,但真的聽到她這麼說依然令我感到駭然。
她毫無給我任何思考與拒絕的機會就緊捉著我的手用力地朝紅色垃圾袋突起的、抖動著的部分捶了下去。
啪嘰─
那是股強大的、不容遲疑的、堅決且明確的巨大力量,我怎麼也無法想像母親細瘦的手臂是如何產生這樣無從抵擋的力道,我因肌肉緊縮而死握著鎚子的手只能任由她擺佈,一次又一次地用力往下敲擊。
啪嘰啪嘰啪嘰啪嘰─
隔著袋子,老鼠骨頭的碎裂、肌肉的崩毀、血液的流失、肚臟肝腸噴出體外的觸感透過撞擊在它身上的鎚子化成了真實而細膩的手感反饋到了我的掌中。
幾縷殷紅的血流了出來盤據在層疊的袋子邊緣形成了個深色的小窪。
雨聲持續著。
母親放開了我的手,我則死盯著那個被打得扁平變成幾坨群聚的扭曲小疙瘩的袋子表面,她從我手上接過鎚子,順了順亂掉的劉海,推正眼鏡,吐了口氣。
「你們去休息吧!我來收。」她說,語調輕盈。
我半張的手還舉在虛空中,那擊毀著血骨肉臟的感觸就這麼凝聚在掌心並滲透過皮膚附著在每一條神經上。
窗外的雨之後連下了三天。
而在第二天父親便失蹤了,只留下一張以繁複華麗的英文草寫文字混搭著方正的中文標楷體所構成的信放在書房的桌上。
5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MPDVWaK7CP
5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7JUnJDCZmN
5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arIRtetJ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