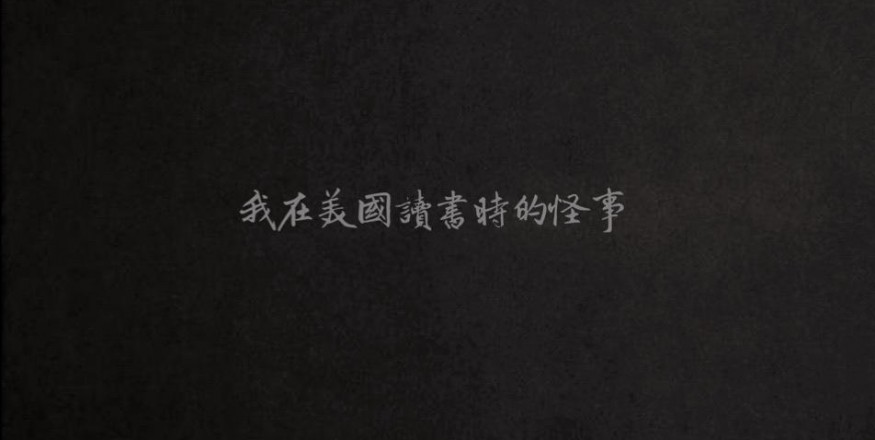第一章
「Not to be opened till the death or disappearance of Mr. Wesley Yeung. 」
以下為殘存的日記內容:
這件事很怪,怪得有點不可思議,很多地方用常理說來根本解釋不了,卻又同時仿佛都解釋得了。我很不幸地捲入了這次事件的漩渦之中,我不知道以後會不會有甚麼更不幸的發生在我身上,因此我希望在我記憶還未模糊,人身安全還未受威脅之前,把整件事記錄低,裡頭的內容或許會有點難以置信,難以置信得就是我自己把這段經歷記錄下來時也不相信它們確實曾經發生,但天下之大,本就無奇不有,還請各位本著一點好奇心,沏一壺清茶,把這段故事看完,到底內容是真是虛,相信各位看後自有判斷。
我叫Wesley,是一個在美國留學的香港學生。我是一個考試制度下的失敗者,當年因為中文不及格,無奈之下唯有選擇到外國升學。由於家境不算富裕的關係,所以每逢假日我也會找份兼職,賺點生活費,算是減輕一下家裡的負擔,而今日要說的這件事,就正正是發生在我假期裡當兼職的時候,現在想起來,仍叫我心有餘悸。
今年是我在美國渡過的第三個聖誕。因為身邊的同學都相約一起去聖誕旅行了,而我又不擅社交,兼之旅費太貴,所以便答應了宿舍舍監的邀請,在學校當一個月的兼職,於工作中渡過聖誕。
我讀的大學名氣不大,位處偏僻山野之間,四周圍著的是大片叢林,離最近的城鎮少說也有半小時的車程,簡而言之,就是一個很荒蕪的地方。但正因為這裡如此僻靜,如此遠離繁囂,卻又使之成了渡假的絕好地方,所以每逢暑假寒假,也會吸引不少旅客到來暫住數日,而學校為了應付這個需求,便會把部分學生宿舍騰出,招待遊人。我工作的地方便是在這些本來空置,新騰出來的宿舍。由於我英文說得尚算流利之故,所以很幸運地被編了做接待處的工作。工作時間在半夜,夜晚客人不多,工作內容也就是接接電話,回答一下客人查問,說白了也不過是一份閒職。我唯一的同事是個三十來歲的黑人,名作森姆,他是當保安工作的。
我們無聊時會一起在房裡打德州撲克,小賭怡情,時間好像會過得快一些。森姆總是搶著當莊家的,他一手牌打得很好,大的賭注他總是贏我,有次我說笑的問他是不是使詐了,怎麼都在贏我的錢,他卻答我:「Wesley,你為人也太老實了,單會說謊是不夠的,要騙得過人,先要把自己也騙得過去。」我聽著不信,想撲克牌也不過是賭運氣,只要拿著好手牌便是必勝了,結果當然是輸得一敗塗地,每晚也輸幾美金給他,現在想來也有點後悔,根本打從開始就不應該跟他對賭。
事情的開端發生在這麼一個夜晚,我很記得這是我到來工作一個星期後的事,這晚我如常的跟森姆在打牌,這一盤我手牌很好,拿著一對ACE,很自然的便把賭注也押至十美金了,森姆還在猶豫是否要跟注之際,卻聽外邊有人在拍鐵閘門:「喂,有人嗎?」說話的是一把女聲。森姆聽後笑了笑,作了個很奸詐的表情,我對他說:「別使詐,我這就回來,這局我是贏定的。」他笑而不語,只是催促我出去應門。
那是個大約三十歲的婦人,半夜裡仍戴著一副墨鏡,黑色圓頂帽,只露出了金色的曲短髮,皮膚很白,白得全沒血色,可口紅卻塗了反差很大的鮮紅色,我看到先是呆了呆,然後問:「小姐你好,有甚麼可以幫到你?」她凝神看著我,隔了很久才吐出一句:「我想登記入住。」她說起話時語調的起伏不大,聲音很冰冷,叫人聽起來有種距離感。
「好的,你有訂房嗎?或者 … 」她沒有答我,只是向我遞來顯示著電子帳單的手機。我如常的替她辦著登記的手續,可期間卻始終忍不住不停的偷看她,在如此半夜要登記入住的人本就不多,她還要如此奇怪的打扮,總叫我感覺有點古怪。「小姐有泊車嗎?」我又問。「沒有,」她答,仍是聽不出絲毫語調的變化,
「好的,那麼請在這裡簽名,如果沒有其他問題的話,你的房間就在 ... 」我想快快把一切交代完,便回去贏了那場十美金的賭局,那知那女人卻問我:「可以告訴我這裡有安裝防盜攝錄機的位置嗎?」我聽著楞了一楞,心想這問題也有夠古怪,但也不以為意,想了想便答:「這裡是學生宿舍,外人不多,就只有這裡接待處和升降機有攝錄機二十四小時監察 ... 」她沒聽完便回頭要走,走起路來時有點閃縮,而且不停的往四處張望,好像在找著些甚麼,又好像在逃避些甚麼,可走得不夠兩步,卻又見她慢慢停下來,回過了頭,「先生,」她說,「我有點餓了,可以借十美金給我買吃的嗎?」
我聽著呆了呆,摸摸褲袋,答道:「我身上剛好沒錢 ... 有的話一定借給你,不過你若是急著要現金時,那邊有提款機可以 ... 」我正欲為她指出提款機所在的方向,可回頭再看時,卻已不見了她的蹤影。「怪女人。」我在心中對自己說,然後便急著回去跟森姆賭錢。
「開牌吧,」森姆笑說,我再回去時已經見他把一張十元紙幣放在桌上,桌上亮出的牌是A, 8, 3, 4, Q,我再看牌面的花式,想森姆無論如何是贏不了這局的,「謝謝了,」我笑說,一邊已急不及待的拿下他的錢,「這麼有信心,你手裡拿甚麼牌啊?」他說著翻開了我的底牌。
「哈哈,輸的是你,」他接著翻開自己的牌,是兩張Q,「三張A怎麼也比三張Q大吧,」我笑說,「你看清楚一點再說,」他指著我的牌,我一看時,見自己手裡只餘一張A,另一張卻換成了K。
「這 ... 這怎麼可能 ... 你換了我的牌?!」我氣道。「誰要換你的牌,這裡有閉路電視的,你不信自己回帶看吧,」他笑說,一邊已搶下我手中的20元美金,然後站起來拍拍褲子:「好了,差不多時間巡樓了,回來再打吧,」我實在難以置信,森姆為人雖然從沒正經,可賭錢使詐的事他卻是不做的,為求真相,我待森姆離去後立即就把影帶翻前一分鐘,可期間只見森姆乖乖坐著不動,自顧自的按著手機。
時至今日,我仍然想不出當晚到底是森姆使詐,還是我累過了頭把牌看錯,但有一件事我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這一切都發生在當晚的凌晨三時正。
ns 15.158.61.44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