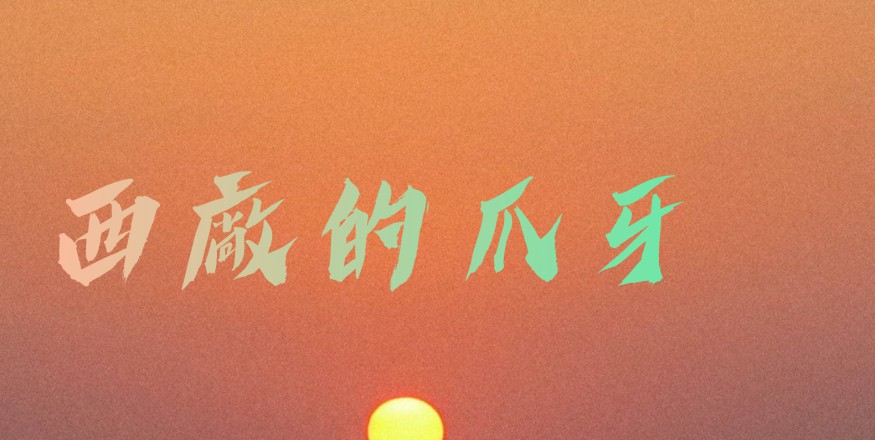夜半時分,位於廣州城西北三里處的一座荒廢小廟,忽現人蹤。
一個身穿淡青長袍,帶着青綠面具的女子,抱着一個身受重傷的雲飛,快步走入荒廟。他們來此作甚?
那姑娘緩緩放下雲飛,從懷中掏出了藥瓶,塞了兩顆白色的丸子入雲飛的口。
說也奇怪,不知是甚麼靈丹妙藥,雲飛居然漸漸醒了,一臉茫然之色。
那姑娘依然冷冰冰的問:「閣下是何許人也?」
雲飛才剛醒來,正感此人之怪,忽被問及姓名,便說:「我姓雲,單字飛。姑娘問此作甚?」
那姑娘嬌軀突微微一顫,聲音有些抖動,激動說道:「令尊是否雲中龍?」
雲飛並沒有留意到那姑娘有異,皺眉說道:「家父已在多年前失去蹤影,姑娘怎知家父之名?」
那姑娘好像如釋重負般,鬆了口氣,自言自語道:「終於找到你了,總算完了師父的遺願。」
雲飛聽得一頭霧水,正想開口,那姑娘忽然以迅雷般的手勢,一口氣點了雲飛五處大穴,使其手腳皆不能動,有口也不能言。
這把雲飛給嚇了一跳,心想:「怎麼我才出道不久,就得罪了這麼多人,怎麼連素未謀面的姑娘也似對我存敵意?」
那姑娘竟一把背着雲飛,急步離開荒廟。
這可把雲飛弄得非常尷尬,紅雲由俊臉飄到耳根去。他本來就從未與女子接觸過,除了家母。
現在,他的胸腹都緊緊地貼着那姑娘的玉背,自然心跳加快,「蹼蹼」在跳,連呼吸都粗重起來。
最壞的是,他不能動,還要讓那姑娘感覺到自己心跳加快,尷尬之感乃雲飛生平從未試過。
那姑娘忍不住「噗哧」一笑,遂以「傳音入密」,說道:「請恕小妹莽失之過,皆因情況危急,遂未經你同意,擅自點你穴道,待情形許可時,再向你解說。」
雲飛仍然聽得一片茫然,完全不知所以,又無法問,只得悶悶的弊在心裏。
由於雲飛受了重傷,還未徹底復原,因此大感疲倦,在一片温香裏沉沉睡去。
醒來時,雲飛已發現自己身在一間密室,身旁坐着那姑娘,湛湛神光注視在自己身上。
雲飛被她那眼睛瞧得大感不安,囁嚅着道:「姑娘,我睡了多久?」
那姑娘點了點頭,道:「整整兩天了。」
然後就是一片沉默,誰也沒有說話,那姑娘像定格了般沒有動。雲飛忍受不到這種異樣的尷尬,於是開口問道:「未請教姑娘芳名?」
那姑娘似是從回憶中醒了過來,「啊」了一聲,道:「我知道你現在很迷茫,倒不如你問我,只要是我知道的,就一一向你解答?」
那姑娘似沒有聽到剛才雲飛的問題,答非所問,雲飛又不好意思一再追問那姑娘芳名,只好說道:「請問姑娘為何知曉家父的名字?」
那姑娘答道:「因他是我的授業恩師啊!」
雲飛頓感心頭一震,急急道:「以家母所告知,家父不是早在我出生不久後失蹤,應該都已離世?何況家父只會些基本拳腳,何來成為姑娘的恩師?還有……」
那姑娘突打斷他的話:「等等!你一次過問這麼多?我怎麼答得了?」
雲飛的俊臉立時一紅,問道:「不好意思,我是一時情急才……」
那姑娘又打斷了他的話:「好了好了,讓我先回答你的第一道問題?其實令尊並沒有去世,只是因故離開了你。再者,令尊武功絕世,才能成為我的恩師。」
這不能算沒有答,但對於雲飛來說,卻似沒有答過。雲飛依然不明所以,遂問道:「為何家父無故棄家而去,遺下兩母子,還要有一身武功,在外傳授武功,那是算怎樣?」
那姑娘嘆了口氣說:「這我怎麼知道?其實小妹所知有限,何況這是你的家事,我怎會知道?」
雲飛道:「姑娘不是說家父是你的授業恩師嗎?」
那姑娘道:「雖是恩師,但師父卻很少提及些前塵往事。所以關於令尊為何離家一類問題的具體原因,就最好不要問我。」
一種強烈的失落感,泛上雲飛心頭,故嘆了一聲,道:「那即是無話可問?」
那姑娘又忍不住「哧」的一笑,說道:「你不是想知道我為甚麼帶走你?」
雲飛立時被點醒了,道:「對對對!我正想問姑娘何以帶我來此?」
那姑娘嘆息一聲,接道:「我奉恩師遺命,把你帶回他老人家墳前……」
雲飛臉色大變,語聲不覺提高:「你剛才不是說家父沒有離世嗎?」
那姑娘似對自己說話不清楚而感慚愧,道:「小妹的意思是令尊並沒有在你出生時便去世,而且還收了我作第子。」
那姑娘微微一嘆,接道:「但在三年前,恩師身體健康每況愈下,直到年許前仙逝了。」
這可把雲飛耍得氹氹轉,剛以為可見父親一面,失而復得的喜悅猶然而生,怎料父親卻在年前離世。一直以來,雲飛的父親須失蹤,卻依然無屍可尋,雲飛亦一直希望能見父親,現在那姑娘給了個假希望他,再一擊打碎,那痛苦不言而喻。
受傷過後,元氣還未徹底復原,新創又來。雲飛不禁想起兄弟決裂那場悲痛,在極度哀傷之中,竟不自禁熱淚盈眶。
那姑娘深感自責,使雲飛憶傷斷腸。遂以無限温柔的語聲,說道:「你也不必太過哀傷,只怪小妹說話不清,致你誤會……」
不知不覺間,整個密室都瀰漫着沉重哀傷之氣氛,那姑娘居然也不禁眼眶一紅,幾乎掉下眼淚。
但那姑娘似突然發覺些很嚴重的事情,長身而起,在雲飛的「命門穴」上拍去!
「命門穴」是練武之人最重要的一個穴道,如貫注內力用力一拍,輕則癱瘓,重則死亡!那姑娘究竟幹甚麼?
電光火石的一瞬間,玉掌已拍上雲飛的「命門穴」上,只見雲飛張口吐出一口鮮血,暈了過去!
那姑娘反而緩緩鬆了口氣,走入內室,拿了盤温水與毛巾,把毛巾沾了些温水,放在雲飛的額頭上。
原來,雲飛剛才哀傷過度,竟走火入魔,真氣逆行,變得癡呆,時間一久,傷會更重,甚至死亡。
幸好那姑娘及時發現不妥,遂以極陰柔之力,巧妙地在「命門穴」上導入內力,使真氣導回正軌,才免去一場大劫。
雲飛又醒了過來,那姑娘立時道:「雲兄現時身體虛弱,不要胡亂動身,重點在於先養好身體,別再勞神傷身了。」
雲飛長長嘆了一口氣,細聲道:「那麼姑娘能告訴我更多關於家父的事嗎?」
那姑娘道:「我記得小時候好像有丫鬟在身邊照顧我,直至五歲時,紛紛離奇失蹤,只剩一個帶着我出走原來我住的家,她帶我到了處別有天地的山谷,名為『碧雲崖』,把我交給師父,至此我就跟着師父學武。不過師父素來待我嚴厲,每天都督促我練武,從無一日間斷。不知何解,小妹總覺得這一切好像都已安排妥當的。師父武功高,但甚少在旁親身指導,反而常躲在山谷中那木屋,不知在做甚麼。我有一次還見着師父用雁傳書,我還好奇的問師父在幹甚麼,師父卻搖頭不讓我知,還叫我繼續練武。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小妹在山谷中的日子就是這樣平凡的渡過。直至數年之前,師父忽然一天召我到木屋中,說我武功已集天下大乘,要我在待谷一年方可離谷,更交代了他的身後事。但那時的師父還精神勇武得很,此也令我很震驚。師父沒有向我交代原因,不過卻沉重的跟我說,江湖大變將臨,命我日後務必要將我這身武功用以救國救民。我真的有點不知所措,師父說些盡是費解的話語,當我追問時,師父又盡說那些不相關的事,所以我起初也不明白。但就在此後,師父就仙遊了,我就依約在谷中再待一年,也仔細觀察了整個山谷,發現了很多不尋常之處,好像小橋、流水、木屋、花園、峭壁也放得恰到好處。最初我還以為是錯覺,後來竟被我發現了在木屋臥室中的衣櫃底下有一暗格,原來下面暗藏住地下室,有一大廳,連同八所臥室。大廳中央放了一張圓形的石桌,還放了一張紙,是師父寫給我的,我一度以為是甚麼大秘密之類的,卻發現其實師父只是告訴我這所密室是供我避難所用。我只能夠說,一切都好像充滿住神秘,卻又不得而知,委實讓小妹難受。但既然身負師父所託,我自然要下山探查一下江湖情形,看看究竟江湖是否隱藏住一場大變。我原本以為要自己從頭開始探查江湖上各種異常之事,但想不到才剛下山,我就遇到了貴人……」
此時那姑娘頓了一頓,發現雲飛已不知何時紛紛入睡,便不禁微笑起來,住口不語。
由於雲飛傷勢甚重,加上武功底子不好,因此康復得慢。
翌日,雲飛陡然起了興致,問:「姑娘何以武功絕高?雲某相信以姑娘的武功,甚至不下於武林七大派之掌門。」
那姑娘不禁靦腆一笑,手撥鬢髮,道:「小妹可是令尊稱之為骨骼精奇的練武之人,儘管我還不怎麼相信,然而我在學習不同武功時,都不覺困難,更甚有興致想深入精研。小妹學的亦是陰柔派武學,雲兄要知道,武林中絕大多數的武功,均以剛陽之力而習,能真習陰柔之力而又通達者,不過十之一二。當然,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我相信武功比小妹高的絕不少,雲兄的誇獎,小妹不敢當。」
後來,雲飛有數次都提出要離開密室之願,但那姑娘每次都回絕,指雲飛傷勢未復原,貿貿然出去只會造成身體創傷永不復原的後果。
沒有辦法,雲飛只能照辦,反正他也覺得身體比平常的自己明顯容易疲勞得多,所以一天有七個時辰都在睡覺。
那姑娘又會偶爾叫雲飛下榻,作一些基本習武練習,說是適當的運動有助加快身體復原。
雲飛由原來尷尬的說不出話,到後來和那姑娘暢所欲言。
他們就這樣待在密室整整近一個月的時間。
就連雲飛也沒想像過自己到底是傷得多重。
ns 15.158.61.4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