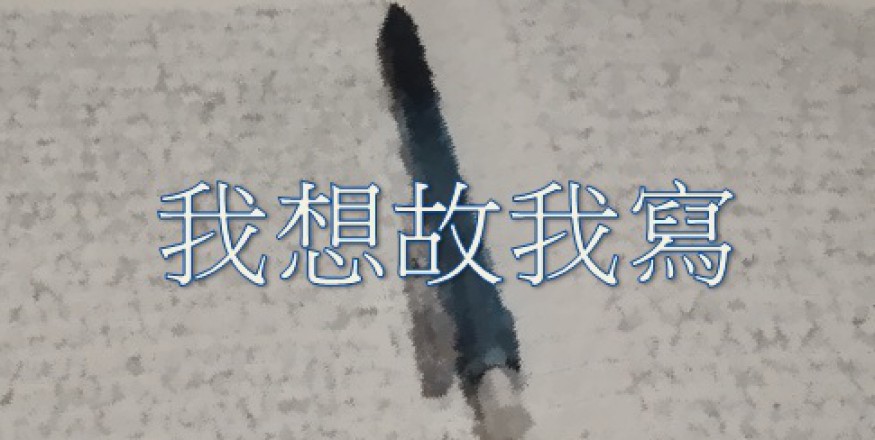在光亮純白的手術室中,瀰漫著一股淡淡的血腥味,而在手術枱上躺著的,是一頭漂亮雄壯的麋鹿,血液緩緩地從牠脖子的子彈孔中流出,並滴至一地。310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oCSExWdn4a
穿著無菌保護衣戴著無菌手套的喬納森醫生皺著眉頭,汗珠正從他的額上漸漸冒出,他突然朝我瞧了一眼,我迅速地從散佈一枱的工具中拿出止血鉗遞給他,而他接過後則默默地繼續埋頭苦幹,而身旁的祖雲則偶爾替他抹掉快將滴下的汗水。310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NN277Je8BF
歷時六個多小時的手術終告完成,將那麋鹿送往康復室等待麻醉藥效過之後,我回到了工作室看還有什麼未做。310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UUvwttMOZ4
「牠的情況還好嗎?」正在認真地寫報告的喬納森醫生問。
「還好吧,所有維生指數都很正常,不過麻醉藥效還未過就對了。」我答。
「剛才謝謝你,珊迪。」在沉默了一陣子後,他突然又說。
「啊?這不算什麼,別客氣。對了,牠......傷得很嚴重嗎?」我想起他剛才在手術室中緊皺眉頭的樣子,以及平時總是一臉輕鬆自如的模樣,不禁有點擔憂。
「嗯⋯⋯」他只是輕輕點頭回應。
「那⋯⋯牠會好起來的吧?」我追問。310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o5avQaasVr
「這很難說,最主要還是看牠。」也許他不想我過於擔心,所以故作鎮定地說,但正在寫字的手卻出賣了他,他右手明顯地加強了力度,使得他手上的筋脈更加浮現,使我一時看得入迷,而他似乎發現了,又問:「幹麼瞪著我的手?」
「沒有,只是想起了點以前的事罷了。」我搖了搖頭,憶起了當初我和喬納森醫生的相遇。
十年前,當我還在胸肺科病房工作時,他也還未是一個醫生,只是一個患上氣胸(俗稱爆肺)的青年。
對於我們來說,他是一個很好的病人,行動自如,不需要我們照顧之外,沒有什麼要求,態度良好,有禮貌,對醫護人員甚至清潔人員也一樣恭敬。
原本只是住個幾天的病人照道理不會令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但那天晚上確實是他拯救了我。
那天深夜,我如同往常一樣在當值夜班,在巡視病人之際發現一個垂死老人正努力地用手把氧氣 罩挪開,我當然馬上走過去阻止他,並幫他重新戴好氧氣罩。
豈料,他用他那無力的手抓住了我的手腕,氣若游絲地對我說:「幫⋯⋯幫⋯⋯我,我⋯⋯想⋯⋯死⋯⋯」
他的眼神很堅定,沒有一絲猶豫,仿佛要告訴我這是他必定要做的事,隨即又說:「我⋯⋯不⋯⋯想⋯⋯活⋯⋯」
反而是我,我猶豫了⋯⋯
這老人雖已年過八旬,但頭腦卻清醒得很,無兒無女,老伴比他早離去,只剩他孤獨一人,這次肺炎入院,相信也兇多吉少,可惜的是,這裡並沒有安樂死,他得苟延殘喘至最後一口氣才能擺 脫這痛苦的世界,但⋯⋯或者,只是或者吧⋯⋯我可以幫他嗎?
我看著他努力地求我幫助,手正不由自主地逐漸伸向氧氣錶頭。
驀地,一隻手突然間捉住了我。
「護士小姐,你這樣做可是謀殺。」一把年輕又低沉的嗓音響起,正是他,他那清澈澄明的眼睛像看透了我般,直直地望住我說。
我反射性地甩開了他們的手,並且迅速地跑走了,也許是腎上腺素飆升的關係,心跳快得像要跳出來一樣,我手心冒著冷汗,大口大口地喘著氣,活像個做錯事被逮個正著的孩子般。
在我努力地安撫好這種緊張又不安的情緒,正打算鼓起勇氣去面對被我逃避掉的窘境時,卻發現那兩個人均已經沉沉地睡去⋯⋯
這⋯⋯算什麼?虧我還一直提心吊膽地去想該怎樣去面對他們二人,唉!那就算了吧。
而直至我下班前那兩個人也一直在睡覺,在我憂心忡忡的幾個休息日過後回來,那二人卻早已經離開了,一個是出了院,而另一個則是真的離開了人世。
至於我和喬納森之後的重遇和輾轉間在他的獸醫院就職,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我們都在回憶中尋找虛無。」他那依舊低沉的聲音把我從回憶中拉回到現實來。
「啊?你說什麼?」我並不是聽不到他說什麼,只是他說這句話實在讓我摸不著頭腦。
「沒有,我也只是在想你在想什麼罷了。」他邊伸手拾起地下一張紙邊答,那深藍色透徹的眼眸像告訴我他想知道答案。
「你有聽說過有種超聲波儀器可以使人的血管顯而易見,方便設置靜脈導管嗎?」我隨口敷衍了他想把話題轉移。
「有,你想回去了嗎?」他只輕輕地問,眼神卻有點飄忽。
「才不,我已經厭倦了服務那些人。」想起了以前工作的種種,我一口就拒絕了。
「嗯嘿!也許,每個人都是妓女,只是服務的東西不同罷了。」他輕輕地撇嘴微笑了,老實說,我很少見他笑,他笑起上來卻令人有種與別不同的感覺。
「你到底想說什麼?」但他說的話卻愈來愈莫名其妙。
「沒有,我只是隨口說說的,要去散個步嗎?」他伸了個懶腰,脫下了醫生袍,問我。
「不了,我還要照顧那頭雄鹿。」這次我拒絕了他,心想著牠應該也快醒來了。
「那好吧,回頭見。」他披上了黑色大風衣,離開了獸醫院。
起初,那頭雄鹿還是虛弱得很,醒來後也是奄奄一息的樣子,連喝水和進食也要人餵,但後來隨著時間慢慢地流逝,牠也就一點一點的好起來,直到有一天⋯⋯
「喬納森醫生!糟糕了,班比牠不見了!」祖雲慌張地衝進了工作室,朝正在寫報告的喬納森大喊。
「誰是班比?」換來的卻是他一個問句。
「那頭雄鹿,他們管牠叫班比。」我搶著答,隨即馬上換上了皮靴,準備走進森林去找牠,牠身上的傷還未完全康復,不能放任牠不管。
「等等,我跟你一起去。」他放下手上的筆,脫下了醫生袍,換上了皮靴,就跟我一起走。
「你不用那麼擔心,我大概知道牠去了哪裡。」他邊走還拍了我肩膀安慰我說。
他帶我到了距離獸醫院頗遠的一大片草地,草地不遠處有個圍籬,圍籬後是被禁止進入的森林,但可能因為日久失修又或是被動物咬破,那圍籬破了一大個洞。
「嗯,這其實是我弄破的,哈哈。」也許他是感受到我的焦慮而開了個玩笑,隨即又認真地對我說:「如果你害怕的話可以留在這裡等我。」
「不,一起進去吧。」我搖了搖頭說,雖然是有點害怕,但我更擔心他會出事,也不想被撇下自己一個乾著等。
「那,好吧!來,小心點。」他很熟練地從破洞鑽了進去,然後伸手把我扶進來。
森林裡漆黑一片,只有天上那微弱的月光和我們手上的手電筒使我們勉強能看到前路,腳底傳來的是濕潤的草地觸感,我們每走一步也留下了一個腳印。
「嘭!」的一聲巨響,嚇得樹上的鳥兒都飛走和正在走路的我跌倒在草地上。
「來,快點走吧!」他出奇的冷靜地扶起了慌亂的我,抓住我的手臂朝巨響的源頭跑。
「等等,那是什麼聲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一頭霧水地問,想要搞清楚狀況。
「槍聲,這是狩獵,我要去阻止。」他只簡短地解釋。
我沒再多問,只跟著他的步伐在森林裡左穿右插,期間又傳出了另一聲槍響,只見他暗罵了一句「該死!」,隨即又加速前跑。
我吃力地跟著他跑,直至見到他和一個持著狩獵槍的獵人扭作一團才停下來。
「住手!你們在幹什麼?」
我試圖分開正在打架的他們倆,但顯然這並沒有用,他們依舊打得激烈,而明顯地文質彬彬的喬納森正佔下風,獵人正騎著他一拳又一拳地打在他肚子上,他雖然也有還擊,但好像捱打的份兒比較多。
我嘆了口氣,不是來找班比的嗎?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在我嘗試拉開獵人時他一揮手就把我推跌了,正當我想站起來再次分開他們時,一個巨大的影子忽地遮蓋了我,並撞向了獵人,把他撞開了幾米遠,還撫著身體吃吃叫痛,我抬頭一看就知道是失蹤了的班比,牠脖子上的彈孔仿佛成了牠的標記,使人一眼就認得出牠。
不過獵人的反應很快,他忍著痛跑向了狩獵槍,我和喬納森雖很快發現了,不過還是阻止不了他拾回槍,他正舉槍朝著班比,更快速地拉了保險掣,下一秒就能再次奪走牠的性命⋯⋯
又是「嘭!」的一聲巨響,樹上的鳥兒嚇得再次飛走,我這回卻沒有再跌倒,看見的卻是千均一髮之際衝過來擋在班比身前的喬納森正流著血,而獵人卻被倏然出現的數隻小糜鹿撞飛到不知哪裡去了,其中一隻更把狩獵槍咬爛了。
我撲到喬納森跟前看了看他的傷勢,幸好只是普通擦傷了。
又認真地檢視了班比一次,除了那顯眼的子彈孔疤痕外,跟今天早上仿是一模一樣完整無缺的,真是太好了!
牠仿佛知道我心思般用牠那圓滾滾的眼睛望住我,又向我緩緩地眨了眨眼,用牠的頭輕輕地撞了撞我的手臂。
「嘿!牠這是在多謝你呢!」身旁的喬納森正開懷地笑說,手在摸著班比的頭。
「是嗎?牠多謝的是你吧,救牠的可是你呢!」我也笑了,邊摸著牠那柔軟的毛說。
「可是照顧牠的是你吧!」他又說,我第一次見他如此燦爛的笑容,有點像陽光般的溫暖。
「對了,你為什麼會知道牠在那裡?」在和班比告別後,在回獸醫院的路上我問喬納森。
「因為我就在那遇上牠啊,當時牠血流成河,卻堅決不肯跟我走,我就知道這裡對牠很重要。」他說。
「可是你最後還是救了牠啊,就像當初救了我一樣。」我最後一句刻意壓低了聲線說。
「嗯?我什麼時候救過你了?」沒想到他還是聽到了,還反問我。
「你忘記了嗎?當時在醫院是你阻止了我,不然我現在可能在監獄裡了。」
「嗯?喔,那又不算什麼,對了,我還未告訴你吧,那個伯伯說很感謝你,只有你全心全意地照顧他,他說他不該陷你於不義,也沒想到你真的願意幫他。」
「是嗎?他竟然能跟你說這麼多。」聽到後我覺得真的有點釋懷了。
「也許那就叫做迴光反照吧!」他想了想又輕聲細語:「我才要多謝你救了我。」
「嗯?你說什麼?」我聽不清楚他最後一句又問。
「沒有,我說,也許我們都在等待,等待別的人來拯救我們自己。」他又說著令人想不透的話了!
創作挑戰:連接的圖片故事5
ns3.145.109.76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