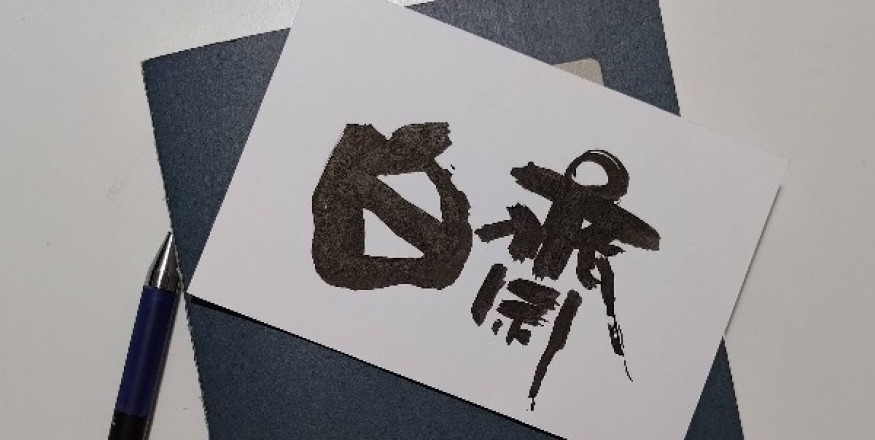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活著總要有自己的陽光;而我的陽光呢?在夜晚的宇宙邊陲?歷經一生也照不亮我的所在,在陰鬱的狹縫?獨自閃耀只遺我一道無力觸及的遐想。我也不知自己是怎了,突然之間便爆發了情緒,是委屈、是慍怒、是受困於人世,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的脫力。我無力吶喊,更無能吶喊,心中的憋屈似難纏的黏膠,逐步填塞了我的氣管,向下至胸肺,乃至心臟,大口而奮力的喘息卻未見效果,如是的無助感彷彿像我宣告,我如今的生命,並不握在我中。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眼下我急需一個洩口,一道能嘔出這口濁氣的路;一把能將我救出這軀牢籠的利刃。既無法吶喊,那就吹奏吧!72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8X55z6q6g9
我想。
讓心中的混濁在管中共鳴,讓同樣崩潰的人們接收音符的感召。這大抵是我第一次,如此用力、如此悲傷的演奏;本是萬物生機的森林狂想曲成了最後一夜的狂歡—它是那樣放肆,那般恣意,卻聽得令人心慌,好像稍縱即逝的曇花,盡情地綻放最後的美好;終於,在最高潮時的一聲尖銳中這場宴會剎那而止,破了的高音為發狂的舞會畫下截止線,無盡的夜幕降臨了。
隨後奏響的龍貓、阿拉斯加海灣、有沒有那麼一首歌,都像是野獸死前的嘶吼。漸強、再漸強;每段音律都好似要炸裂般的被拋出,可又有誰人真正聽清了背後那早已顫慄的氣息與聲止後的哽咽。當我最後奏完周深的"借過一下"時才發現身上早已汗濕,渾身都是止不住地發抖。
上次如此失態是在何時?我早已沒了印象,但我確是實在太久太久沒這般毫無顧忌地任由體內的情緒噴發似的向外湧了。太久了,連自語都被允許的囚禁早該將我逼至極限了;也許,在我蜷縮床角,獨自一人卻無法開口時便已經在支撐不住了。可誰曾總被評價沒心肺的這人竟生生一口氣憋了過去呢?也許我果真沒有心肺八,才會不知道肉疼,不知道人心也該是肉鑄的,面對這些我也是疼的,能疼的,該疼的。
只是,除了太陽,似是再沒人會提醒我,"你可以回來,可以哭,可以難受。"
情緒漸緩了下來,下了床直往地上躺倒,雖然不明白其中的緣由,但比起些柔軟處,這較原始、硬冷的地板更受到欽賴,它能讓我平靜。看著天花板,我將早已看過無數次的深空和星座投影,逐步將心中的小宇宙建構,重新築起宮殿。
她總擅長將歇斯底里強加於我,扼住我的脖梗,好似我的生死,我的情感都只是他們的附屬品,是可以召之即來,呼之即去的物品;是她不滿的收納箱,硬生生吞下。
就這樣吧,也有些倦了,但也只能這樣了72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0H2VXVz7k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