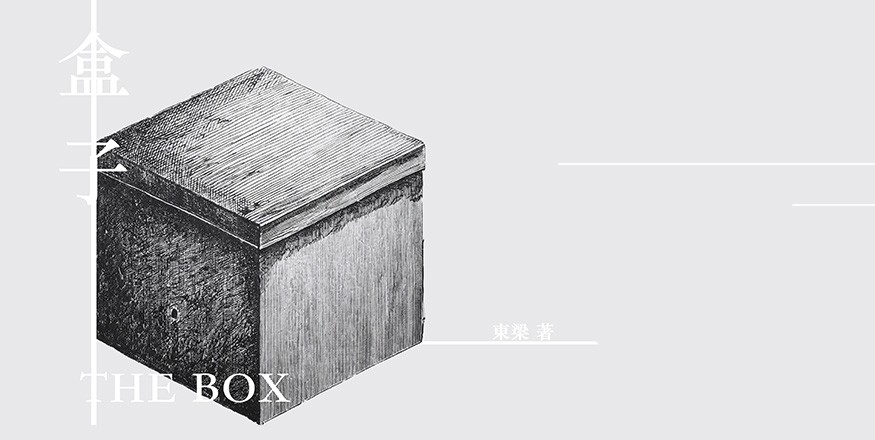接下來的日子裏,我們不停歇地在C區打遊戲。累了就在沙發上睡覺,精神尚存的人兒便繼續闖關。大家餓了就吃,吃了就睡,睡醒就打,到時間點就抽念量,休息一會再繼續打遊戲。袖珍筆記本裏甚至沒有那幾天的筆記,忙得無瑕紀錄。而這種情況應該持續到第十天。
D10??
- C區,睡 0907梳洗
- 醒後-虛無…?
- E區,廚師健身
連時間也沒有記載了……日子也是依體感時間結算得出。每當與女人對上眼時都會想起第一天據理力爭的畫面,若果任憑手錶淪落為口袋內的御守,那麼一切都不證自明。我的自尊過意不去,第十二天以後的筆記定會重新紀錄。可這都是後話。已定的事實是,被刺眼的白燈籠罩下和虛擬世界的誘惑下,我與時間漸行漸遠。好像做了很多事情,又好像沒做什麼;好像過去了很久,又好像只眨了眨眼。我癱坐在沙發上,看著天花板。虛無感襲來,自以為能夠選擇,但是當你選擇某個選項時,或者冥冥中被他人所影響,又或者被外世態所影響。那麼這還是自由嗎?還是自以為的自由……我自以為可以支配時間,其實我才是被支配的一方。雖然現在比起之前賺的多,但那串數字遠不足以彌補心靈。玩樂過後,我理性上知道時間的流淌,可周遭人事物卻說:不,當下即永恆。僅有時間作參照物。看,多麼單薄無力。
我胡思亂想了一番後,打算做些什麼……看了看手錶,現在是早上九點零七分。那刷牙洗臉吧。我去到B區洗漱,看見廚師戴著頭戴式耳機上廁所。身子隨節奏律動,他的自在顯得我格外拘謹。上廁所、洗澡、甚至是滿足性需求在我價值觀內都是極其私人的事情,事到如今我依然沒辦法如其他住戶那般自在地在開放式空間解決以上需求。總是要等到他們睡著或者沒人在B區的時候,以千萬分之一秒的速度處理一切。他們像是已建立起某種不成為的規矩,奈何我來的時間不久,仍在制度外。
我的視線不敢離開牙刷牙膏杯子水龍頭鏡子。感覺要是偏離了半釐米就可能瞧見了某些東西,雖然我知道他不會介意。我洗完臉抬頭看鏡子,鏡子內的反射映照著廚師朝我揮手。我看不見我看不見。
襪子掩護了我蜷縮的腳趾。梳洗完畢後直徑走向D區。坐在看窗戶的絕佳位置。白晝隨窗戶滲入,和這裏的光線融為一體。天花板是白色,光管是白色,住戶們的睡衣也是白色。年輕人坐在沙發昏睡,昂頭,嘴巴微張。雙手隨意地擺在兩側。長鈴側躺,睡在地上。可惜我的視野被桌子擋住,不能夠再仔細地觀察她。我猜她是雙手合十,枕在枕頭旁。因為我也是這樣入睡,創作總會添加一些個人色彩。半年…乍看之下她不在C區。我猜她應該回去A區睡覺吧,平躺且雙手放在小腹上。上次玩一個經營餐廳的遊戲,半年很執著於食材和工具的擺放位置。平日裏打完遊戲都是她收拾。我問她為什麼這麼執著,反正過一會也會再玩。她說習慣了,不喜歡雜亂無章。於是我跟她一起收拾。感覺睡得像死人是她的脾性。我開始數天花板有多少根光管、盒子內有多少監視器、廚師舉了多少次鐵、袖珍筆記本一頁有多少條橫線…然而時間依然似定格,現在不過九點二十分,才過了十幾分鐘。我看著天花板,天花板看著我,我倆面面相覷。我羨慕它有事可做,能掛幾盞小燈;它羨慕我無所事事,口袋卻長滿了金桔。
感官上的刺激使得衡量快樂與痛苦的天秤持續向前者傾斜,每一次遊戲開始,傾斜再續。但當出現遊戲結束後,天秤回歸平衡。天秤本是如此,它只不過是回歸常規樣貌罷了,可是常態卻讓虛無滋生。以尋求比從前更大強度快感去維持傾斜。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清晰地,清楚,明白,意識到,這痛苦的,輪回。C區有閱讀區、E區有健身器材、各種體育館,甚至還有其他未解鎖的領域。可C區也有各類遊戲,冒險、槍擊、格鬥、音樂、卡牌、桌牌和昨天還沒通關的解密遊戲。我痛恨這種自以為然的身不由己。
我忘了當時候的我後續做了些什麼,記憶斷片了一樣。或許是年輕人醒來然後叫我回C區打遊戲,抑或著半年醒來後叫我幫她煮即食麵做早餐,之後一起打遊戲。身子有意無意地向C區靠近,我想欺騙自己,說我控制不了這個軀幹......可這滑稽低劣的謊言我說不出口,這是對自己的一種侮辱。原諒我在這一篇章的情感抒發多於對盒子的敘述。我曾問過自己為何在一個可以縱情享樂的空間內卻仍在埋怨。但要知道我的念量未曾接受人為破壞,一個思想儲備充裕的人格在這樣的環境裏,自主意識開始模糊,連「為什麼」都會變得一文不值。慾望使我頭昏眼花,似崩了角的瓷器又如沒吸完的半隻煙。總缺了點什麼,外人看似不痛不癢,可有時候能要了你的命。我該做些什麼,我不該做些什麼?這個問題從也隨著危機感貫徹到後續的生活裏。
ns3.135.221.98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