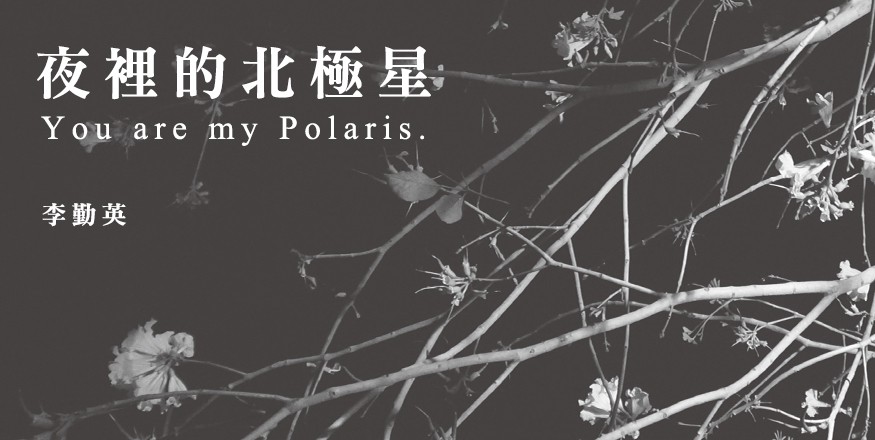寒風因為重機的速度讓人感到更加寒冷,沒有被大衣遮蓋到的脖子感受到刺痛,吳元青只能不時把長度已經到極限的衣領再往上拉一些。
儘管如此,吳元青的胸口卻依舊暖熱,陳聖硯給予的力量還在心頭縈繞,像是剛充好電微微發熱的電池。
彼此緊貼的胸膛、輕撫背部的觸感也還留在皮膚上,好像閉著眼、伸出手就可以再次得到這個擁抱。
從山路騎到平穩的道路,一路高掛的太陽也轉變為夕暮,天空出現橘黃色及藍灰色的漸層,中間那段由兩色交織、混和成的部分有無數種顏色拼湊而成。
其實吳元青很不喜歡這個時刻,這時候的景色自然是美麗,但黃昏和黑夜交接的時候,總是有說不出來的感覺。被驅趕著的亮光彷彿無能為力一般,只能朝著西邊逃走。
但今天的感覺似乎有點不太一樣,明知道黑夜來臨了,吳元青也能夠被唯一的那道光永遠的照亮著。他忍不住笑了起來,原本想要像之前陳聖硯那樣在機車上隨意大叫,但還是因為太害羞而作罷,只能在全罩式安全帽裡偷偷地笑著。陳聖硯說過的話,像是小說詩詞般一句句浮現,回想起來便能感受到當時他的表情、手心的溫度、雙臂緊貼在自己身上的力道……
吳元青不自覺又加了點油門,在筆直的路上享受著速度感。
突然,眼前浮現一個穿著白色制服的少年,明明應該只是腦中的想像,但那個少年好像確實在眼前。
那是高中時的吳元青,尚未成年的背影比現在的他消瘦很多。少年騎著沒有變速的腳踏車,像是剛起步般搖搖晃晃地前進,等到平穩之後,屁股離開了坐墊,卯足幹勁踩著踏板,似乎是要追趕著什麼。
吳元青不用看到正面也知道那個少年與現在的自己一樣,臉上掛著的是滿滿的笑容,因為眼前的畫面正是他的一段久遠記憶,一時還想不起來當時是趕著要去做什麼。
就這樣,像是在帶路般,少年的他一直騎在前面,騎著重機的吳元青不管騎的多快,和少年的距離始終如一。
在過了一個需要壓一點車的彎道後,吳元青突然想起來那是有一次母親去日本出差三天後回來台灣的日子。因為飛機抵達的時間,他在學校無法去機場接她,所以一放學後就趕緊騎著腳踏車趕回家。
他記得母親出差的那幾天,雖然生活作息和平時沒有什麼兩樣,也是早上起床去上學、放學回家煮飯、晚上在家念書。但平常煮完飯,他總是等待母親下班回來一起吃晚餐,這幾天卻是獨自一個人吃飯。每天母親的存在已經成為習慣,直到獨自一人在家的日子,才知道自己不過是快要成年的毛頭小子而已,雖然能夠自己打理基本生活,但終究還是需要相依為命的母親。
那天趕回家後,頂著一頭被吹亂的自然卷,臉頰上還留著汗珠,在母親面前假裝鎮定地打招呼,並說著一些無關痛癢的寒暄。因為不管怎麼樣,都不想讓她知道自己騎著腳踏車狂奔回來。
但氣喘吁吁的樣子似乎還是露了餡,母親先是噗哧地笑出來,摸了摸他的頭後就去煮飯了。那天她究竟有沒有發現,也無從確認了。
現在的自己成長了嗎?還是只是年齡增長、學會獨自生活而已,其實內心還停留在那個時候根本沒有長大?自己在那時候丟失的東西,現在有找回來了嗎?一連好幾個問題問著自己,但沒有一個有確定的答案。
這時,從剛才就一路追隨、揮之不去的記憶――少年的腳踏車漸漸慢了下來,直到完全停止時,吳元青也同時壓緊剎車,雙腳著地。
他懷疑自己在作夢,但緊握龍頭的手又是這麼真實,而且從剛才到現在的記憶是連續的,表示這並不是夢境。但他也說不出來現在這個實體化的記憶到底是怎麼回事。
眼前的那位少年,也就是自己,突然轉頭對著吳元青笑著,那是個尚未蒙上任何陰影的笑容,青澀但又帶有一絲自信。
啪的一聲,一些記憶回到了吳元青的意識裡。
對了,那天也是像現在一樣,是白天和黑夜追逐著的時刻。當時也是反覆踩著踏板追逐著時間。
他總覺得方才問自己的那些問題,那個少年的他或許可以回答。但他自己心裡再清楚不過,這個少年只存在於他的片段記憶,只是一個畫面而不是真實的過去,因為當時的自己早就已經徹底被毀滅了。
所以吳元青才回答不出那些問題。
剛才還在眼前的記憶片段漸漸消失了,少年和腳踏車就像調整了透明度一樣,慢慢變淡,然後直至消失不見。
但吳元青卻覺得那個記憶並不是消失了,而是像一塊拼圖般回到了自己身上,與真實的過去拼湊在一起。因為母親過世後,吳元青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如此鮮明的回想之前的記憶。
和陳聖硯在一起的自己,是不是就有修復過去的能力了?他不禁這麼想著。
刺眼的橙黃色的光線朝吳元青照射過來,像是故意要引起他的注意般。他朝右邊看去,方才躲在建築物後面的夕陽現在露了出來,因為有雲層的阻擋,吳元青可以直視著太陽和四周的景色。
吳元青瞇起了眼睛,並不是因為陽光刺眼,而是看著昏黃的夕陽讓他覺得有些想睡。剛才會看到彷彿實體化過後的記憶,說不定就是太累了。
把機車停妥在路邊,坐在一旁的水泥護欄上,這裡離進到城市還有一小段距離,天空顯得遼闊。他無意識地摸了摸大衣內袋,發現口袋是空的,這才想起來自己已經把菸交給陳聖硯保管了。對於還想用菸醒腦的自己,突然浮現對陳聖硯感到抱歉的心情。
於是他朝背包裡面翻找了一番,摸索了好久才找到隨意塞在包裡的耳機。平常都是好好地用捲線器捲起來的,但上次太過匆忙就胡亂塞進去,結果演變成現在這場糾結的悲劇。脫掉手套,他專心地解開惱人的線,好險一下子就解開了。
把耳機塞進耳朵裡,尾端插進手機,快速地操作一下後耳邊便傳來了熟悉的音樂。Crying Kana的世界末日的舞會。
設定成單曲循環後放下手機,吳元青抬頭看著比剛才更下降一些的夕陽。腦袋放空,就這麼感受著眼前的畫面。
其實這個時刻也並不壞嘛。或許並不是追趕,而是白晝拉著黑夜來到這個世界,想和它一起高掛在空中。
呆愣愣地,直到夕陽隱沒在建築物的後頭,吳元青才像是看完電影準備散場的客人般,緩緩地站起來。
再次跨上機車,朝著黑夜來臨的方向繼續前行。
◆
連續兩天騎了總共將近快五小時的機車,對愛騎車的吳元青來說也是有點吃不消。
疲憊地轉開門鎖,拖著沉重的腳步進屋,鑰匙還一度忘記從門上拔下來。吳元青決定待會先趴在沙發上讓下半身休息一下,再去隨便煮個麵來當晚餐吃。
但才剛把黑色皮鞋擺放整齊時,放在背包裡的手機響了,因為放在夾層裡,發出了很低調的嗡嗡聲。
拿出手機看了螢幕,又是不認識的號碼。
吳元青原本不以為意,先把還在響著的手機放在餐桌上,脫下大衣和領帶。直到他把大衣掛在椅背上後,又朝手機瞥了一眼,突然覺得這號碼十分眼熟,雖然不太確定,但似乎是這陣子一直打過來的號碼。
電話在思考之際掛斷了,心想可能對方真的有急事才會一直打來,於是吳元青毫不猶豫地拿起手機回撥。
回撥後,響了好幾聲都沒人接,很想躺下來休息的他顯得有點不耐,又不想等對方打來打擾自己,於是掛掉電話後又再撥了一次。
這次也是響了一陣子,但終於接通了。
「喂?」
吳元青急著先出聲,但另一頭的人並沒有同時出聲,只聽得見呼吸聲還有一些不明的窸窣聲。
他皺了眉頭,問:「請問是哪位?你打很多通了吧?」
另一邊卻還是悄然無聲,正想請對方沒事別再打來後,對方終於開口了。
「……元青。」
彷彿來自洞穴深處的乾涸聲音喊著自己的名字,直衝腦門來到記憶的深處喚醒了什麼。
那是他埋在最底層、永遠不願想起來的聲音。
對啊,之前接到無聲的電話時,怎麼都沒想到是他呢?安逸的日子過久了,就沒再想起他了。應該說吳元青的本能告訴自己不可以想起來。
吳元青全身定格,剛才滿載著胸口的溫暖極速消退,隨之取代的是他再熟悉不過的焦慮感。血液彷彿也被這股焦慮滿滿佔據,心跳聲聽的一清二楚。
他雙眼失焦地站著,呼吸越來越粗重,有種快要吸不到氧氣的感覺。空著的另一隻手不安地搓著西裝外套的邊緣,越搓越急,呼吸也跟著急促。
「爸。」他虛弱地用僅存的力氣說道。
儘管對方讓他多麼想忘記,他還是用這個稱謂來稱呼他。即便對方根本沒做到這個稱謂該盡的責任。
隨著心跳越來越猛烈,吳元青心想自己完蛋了,說不定此刻會因為久違的恐慌症發作而暴斃在這裡。他感到十分暈眩,雙腿瞬間無力,終於忍不住直接頹坐在客廳的地板。手機也因為手指發麻抓不住而「喀喀」兩聲滑落至地板,電話另一頭說了那兩個字後就再也沒有出聲,但也沒有掛斷電話。
果然自己是沒有辦法擺脫那個黑暗的,這句話不斷反覆在嗡嗡的腦袋裡環繞。
ns18.221.49.39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