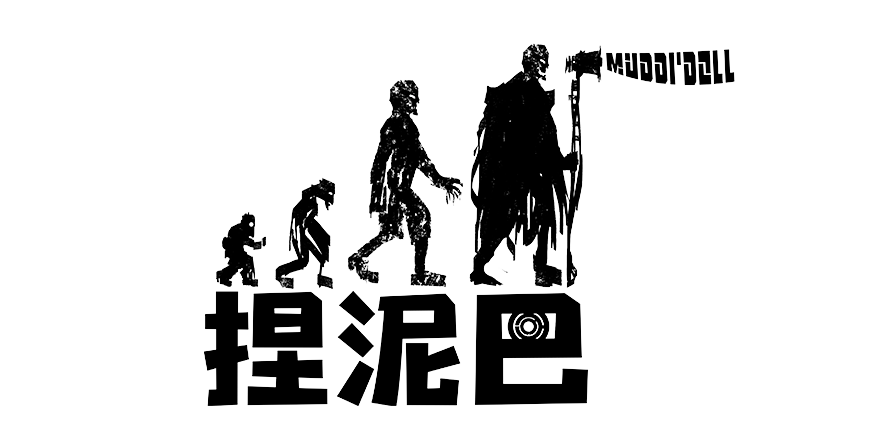 x
x
拉比們看查瓦媽媽冷靜後,溫柔的扶起她,並找人帶上查瓦的身體到村子裡的神廟中。25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Lx5BkMIbMl
那時的神廟純粹是追憶已逝去族人的地方,並不像現在放滿電池和導管。在古老又傳統的神廟裡我們搥胸頓足,流下淚水,或埋怨不被上天眷顧的逝者。
只因他們擅自留下愛而無法傾訴的我們。
即便我不想他們移動查瓦的身體,但春季下午常有的細雨已經到來,即使我想再看看查瓦,也不願意讓她再淋雨。像隱藏在天上烏雲後的上天,還嫌查瓦的身體不夠冰冷一樣。25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39BQnUe6mu
所以我沒有阻止他們,可是那種感覺好陌生,這樣靜靜的看著他們將她抬起,然後束手無策地看她再次離開我的關注範圍。即使我早就知道她不在那付破敗的皮囊裡。
雨滴們漸漸的大膽起來,他們已經開始捉弄這位新來到村莊的暗黃朋友,雨滴們輕輕的拍打著他金屬製的皮膚,他們似乎根本沒滴落在這樣稀有、堅硬又美麗的材料上過,所以他們全部都因自大而碎裂成更小的部份。但小雨滴們比較幸運,他們碎裂之後只要慢慢滑過金屬,就能夠再次與朋友們合為完整的一體,然後快樂的回到泥濘中。而我還要等好久好久才能再次投向查瓦的懷抱中。
不過那時候我的身體也快要消融進去那片沈寂的大地中了,大地包容一切,但卻是這麼安靜。
它溫緩地讓人沉醉在永恆地孤寂中。等這一陣風雨停歇之後,我猜他們會將查瓦包裹上部落中最美麗、華貴的外衣,即使她從來不喜歡那種矯蹂造作的形式和色彩,他們仍然會將她以他們自認為隆重的姿態埋入大地之中。真可笑的執著,人類在未經努力的愛之後仍用全無道理的形式假裝曾經在乎。
不過我自己也挺可笑的,就像以往我和她進行計算行列式的小比賽,只是那時候比的是誰會比較快埋入寂靜。
她贏了,而我一點也不喜歡這個比賽。
腳步聲,這次很輕微。
我將意識拉回到眼前的暗黃人身上。他降低重心用他毫無生氣的金屬面容對著我,我想人類會稱呼這動作為凝視。他的臉其實更精確來說並沒有明確的五官,就像是帶了黃色的面具那樣。
我突然意識到他的臉,或者說面具,就像我的第二副木頭身體,查瓦用泥巴捏成的五官一樣。
或許他......
他蹲低後將包含最多意識的,也就是有我鏡銘石的那快身體抓起。當下我真的感受到害怕,我像強風下的早苗,根本沒有選擇的進入他的掌控。但又不僅僅是恐懼,情緒波中還包含著興奮。我認為他是我第一個認識的同類。
暗黃人也是魔像。
即便他的波很短淺和容易被人忽略,但我在如此靠近他的情境下,聽到從他金屬製的身軀中傳來機關摩擦的聲音。他究竟是靠什麼活動的,我竟然完全想不透,霎那間我完全忘記自己正在他的掌心中,我快速的搜索著所有看過的書籍,天阿,我的資料實在相當匱乏。
我仍然在記憶中挖掘到某一本查瓦負責研究的註解中看到了一些模稜兩可的大小橢圓結構。她紀錄那些想法的來源是一種昆蟲 — 伊蘇斯葉蟬。她似乎看過一兩次那種昆蟲,所以隨手紀錄了。不過她留在羊皮紙上的那些只是她的初步發想,並沒有後續實現在暗黃人身上的如此穩定、和諧。後來我才知道在大陸北方,也有人想到類似的運作系統,而那個喜歡仰望星空的工匠稱這些組裝式金屬圈為齒輪。
這是我從來沒有想到的完美系統,光是看到這尊魔像能夠成功的運作便是最讓我興奮的事情,她真的成功了,一種耐久的材料,足以支撐如此巨大的重量和身高。不被天上的雨水和陽光欺侮,在保持所有系統和諧運作的前提下能夠轉換自己,甚至是自己加上查瓦身體的動能。
這完美的身軀究竟是從何而來?他想做什麼?
那時的我已經無法在構築出足以稱為聲音的波,可是我仍然想從他那邊得知關於查瓦死亡時的資訊。這使我思考一套更加節省力氣的溝通規則,我發現自己一直以來都沒有思考以內部的「情緒波」直接進行溝通。這是環境與外部刺激帶來的成長,我那時深刻認知到一直以來我都是以人類的思考方式與人類溝通,如果「魔像」是有專屬於魔像之間的交流方式呢?
查瓦母親曾說,魔像都不會開口。我認為那些魔像並不是沒有開口,他們只是遲鈍的以為人類聽到了,而人類總是傳出陣陣疲累、焦躁這樣負向的情緒。
那時候我知道自己必須在回歸塵土之前,證明這個超越過去一切的大膽想法。
一個專屬魔像之間的溝通規則......那是多麼讓人興奮。
快速構思並計算過初步的溝通規則之後,我將想傳遞的想法「逐字」拆開,要有一道長波以每個波峰為單位去調整正弦或鋸齒。
這個規則其實並不是新的發現,那就像人類從說話變成唱歌,而唱歌中有更多情緒的起伏和故狀態,所以只要改變思維就能做到。
後來這套規則我稱之為訊號。
相對於有機生命發出的訊息。
我同時花了一些時間教導暗黃人規則並改善了一些本來沒想到的規則謬誤。
「你,什麼?」那時我已經很難整理複雜訊號了,不過我還是竭盡所能的在他面前發出一陣一陣的微弱聲波。「你是,什麼?」
「我是你。」聲音碰撞著他身體內部的金屬然後經由他面部的深孔傳遞,聲音是這麼清晰、飽滿。但這個答案是什麼意思?我想應該是指和我一樣是魔像。
「哪,來。」我先整理出單個詞彙,再連接。「哪裡過來?」
對方沒有回應。
「你,魔像嗎?」我用了另一種問法卻是同一個問題,這能確保對方沒有敷衍或者欺騙我。
「是。你呢?」他送出一道嘲笑的情緒。
我將他的嘲笑整理成我加工過後的滿不在乎,像「兩手一攤」那樣的情緒朝他推送。他是個蠢笨卻有趣的傢伙,我的確漸漸失去被稱為魔像的資格,但能在回歸大地時跟另外一位魔像說話,我感到欣慰。
「你,查瓦。」我在他掌心的土不斷低落到地上,身體和意識都漸漸流失。「你認識查瓦?」
「知道,她創造我。我感謝,帶她回家。」
那時我才了解,「我是你」這三個字是什麼意思。
只要是查瓦創造的,都能稱為「我」。
「她,稱呼?」我不知道自己是難以開口還是因為意識的消逝才如此。「她怎麼叫你?」
「禮物。」他很堅定的說。
「什麼?」我擔心他也擁有與我相同的名字。
「禮物。」他似乎有點驚訝我不知道這個詞。「禮物是一種示好,一種具體的證明……」
我在他繼續解釋禮物的定義時分心,因為我發現稱為「禮物」的暗黃人真正的身份以及意義。
希望……當時我的理解不是錯的。直到今天我仍然時不時回想起這段回憶。
「禮物是愛的展現,一種奉獻。」他解釋完,我同意他說的。
「謝謝,你的禮物。」我對暗黃人發出明確的最後訊息,不過其實我想自己是想親口對查瓦說。
我要謝謝她不惜生命製作並交付給我的......如此美麗的第三副身體。
我送出一道又一道的鋸齒波衝擊著禮物。以沒有任何保留的力量建構出波長,再以新的訊息手段推送。禮物金屬製的身體不斷的抽搐,金屬版片互相撞擊出刺耳的聲音,那就像是他的尖叫。
他很不情願的打開位於自己後頸的金屬板,他實在不想在下雨時讓雨滴進入內部,但是這不是他能決定的,我需要他這麼做。
他用沒有捧著我的另一隻手,拿出自己的鏡銘石,然後也捧在手上。他從我身邊傳出悲傷,因為他在離開身體之後變得跟我一樣虛弱。他對身體的掌控已經越來越弱,而這就是我要的。
我推送一道口氣強硬的訊息,要他輕巧的把我放入後頸。他不是相當願意,所以我加上一段比較和緩的正弦波在訊號中,那種訊號模擬人類特有的謊言,柔和而富有道理,卻殺傷力十足。即便暗黃人有更多生命去支撐他發出訊號,但這是我的遊戲,是我架構的。
我就是規則。他在我的計算之下成為我掌中一個微弱的存在。禮物當然是相信我的,他根本沒理解這條訊號中隱藏的真正意思。
他將我鏡銘石上殘存的木頭身體部件移除,然後扔到地上,再慢慢的把我放入他金屬身體的後頸中。關上金屬板。
我進入的瞬間感到相當驚訝,還無法完全感知到這樣巨大的結構如何運作和相互協調。我發出一點聲波,讓波在金屬製的體內衝撞、摸索著。
嘗試過幾次之後,我終於了解什麼地方稱為手,哪邊的特定部件稱為頭,齒輪彼此之間誰的關係更親密。
很快,真的太快。我掌控了他的身體。
我的身體。
我向禮物道別。
那隻握著他原有鏡銘石的手慢慢收緊,金屬的手掌摩擦他刻有粗糙行列式的鏡銘石,他像我發出強烈的鋸齒波,後來漸漸轉為哀求的正弦,而我仍然持續加大力道,握緊。
一聲爆裂,他的鏡銘石完全碎裂。
他不再擁有世間的任何波,只是全然的靜止。這樣安靜的世界只剩下雨水拍打在我身上金屬的聲音。
張開手指,禮物碎裂的鏡銘石被雨水沖刷進滿是泥濘的大地。那邊同樣是靜悄悄的。
我站起身,張開雙臂,並且仰望天空雨水的源頭,那應該是天堂吧?查瓦會上去那裡。
某天,當我靜止之後,一定無法上去吧。
ns 15.158.61.19d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