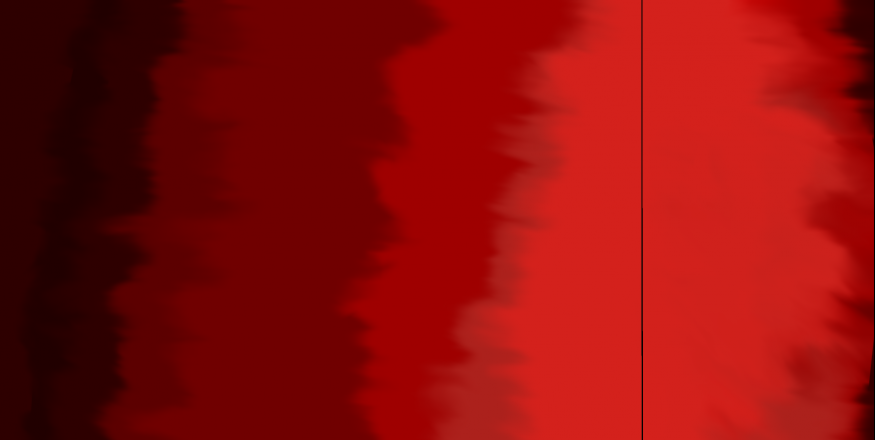小時候,因為爸爸工作的關係,我們常常搬家,原本說要給我寫信的朋友,在他們信件送到以前,我可能又搬了家,或者他們只是口頭上說說而已,也許過了幾個月,他們也就把我給忘記了也不一定。
由於這層關係,讓我在國小的時候,從本來非常渴望交朋友,到後來很害怕交朋友,因為往往在和他們熟透之後,我便要和他們分離,這對一個九歲的小孩來說,可能沒有甚麼比這個更殘忍的了。有次,我們全家搬到一個小鎮,小鎮在山腳下,一出門,抬頭就能看見一片蓊鬱的樹林,從家裡不用十分鐘,就能走到上山的入口,可儘管這樣,學校自然課,一次也沒帶我們上山,不光是學校,就連這裡的鄰居都告誡我們一家不要上山。
有幾次,我偷聽鄰居太太和母親在聊天,說是山上似乎住了甚麼東西,會把小孩拖上山,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鄰居太太發現我在偷聽,說這段故事的時候,還說得特別大聲,母親也是似笑非笑的表情看著我,我總覺得這故事鐵定是他們編來騙我的!他們後來見我不理不睬,便轉頭繼續閒話家常,我便也沒有放在心上。
學校的小孩都是成群結隊的,他們有幾次也想邀請我一起踢足球、踢毽子或是玩竹槍,卻都給我搖頭拒絕了,雖然他們並沒有因此欺負我,但漸漸地有活動也不再找我參加。雖然總有點落寞,但我總覺得這樣是好的,因為這樣爸爸如果又搬了家,我就不會想念他們,也不用一個人傻傻地站在門口等郵差,至少,那時候我是這麼想的。
但這次爸爸沒有很快搬家,我在那邊唸完了整整一學年,這讓我感到十分的不可思議!我甚至產生一種爸爸會在這邊生根,直到我結婚生子的錯覺!可待得越久,我就越不容易打進其他小朋友的圈圈裡,每當我下了課,我就自己騎腳踏車回家,也不在學校多做停留,有幾次,在停車場牽車的時候,我總會看著球場,然後故意將腳踏車牽得很慢、很慢,想著或許他們會邀請我參加,可終究是沒有。
那天下課,我並沒敢直接回家,手裡捏著那張不及格的考卷,我牽著車,往反方向走著,因為媽媽對我的課業盯得很緊,總說轉學也不該影響課業,換個新的學習環境,應該會對學習更有熱忱、也更能吸收新的學習方式,她總能有一套自圓其說的方法。
我就這樣一直走、一直走,早到手裡的考卷都因為手心的汗水被弄得皺巴巴的,我也沒停下腳步,走著、走著,遠遠地,我便看到三個和我年齡差不多的小孩聚在一塊兒,好像在玩甚麼有趣的遊戲,可這三個小孩,是我在學校裡不曾見過的。
他們看見我可高興了,說要和我一起玩,我沒有拒絕,便把腳踏車停在了一旁,他們說,要到山裡去玩,我跟著他們走了一小段路,森林的大樹很快地遮掉了半片天空,陽光漸漸地照不進這葳蕤的密林,看起來,就像是從白天走到了黑夜。
我問他們:「那我們玩甚麼呢?」
另外兩個小男生沒有答話,看著穿紅衣服,齊瀏海的小女生,小女孩說:「當然是玩娘仔仙」,我沒聽過這個遊戲,便讓他們教我怎麼玩,她說,玩法和鬼抓人差不多,只是鬼會有三個,而人只能有一個,當鬼的,必須轉過身去,面朝大樹,不可以偷看,還要唱歌,唱完了歌,才可以轉頭開始抓人。
我搖了搖頭,從來沒聽說鬼比人多的鬼抓人,這樣有甚麼好玩的?我反駁她,鬼抓人就是要人比鬼多才好玩啊!兩個小男生還是沒有答話,其中一個穿白色調嘎的小男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山裡冷,竟然有些發抖,小女生笑了笑,說也可以,便讓白吊嘎的男生和我一組,可是,她和剩下那一個光頭的男孩,要當娘仔仙,也就是她剛剛口中的鬼。
我想著,我才來這裡一年左右,他們感覺在這個鎮上住了很久,怎麼樣也對這裡比較熟悉,由他們當鬼,我們說不定一下就被找著了!因此便想要和他們交換,誰知道那個女生突然臉一沉,吊著眼睛看著我說:「你們會唱娘仔歌嗎?」
我搖了搖頭,穿白掉嘎的男生拉了拉我的衣角,讓我別和她爭,我本想再說點甚麼,但轉念一想,有人肯陪我玩不就很好了嗎?要是和她起爭執,以後他們都不跟我玩了怎麼辦?這才點了點頭,答應了他們的要求。
女孩和光頭男孩轉過了頭,然後就唱起了娘仔歌,我本來還想聽聽他們唱甚麼,卻被白掉嘎的男孩拽著胳膊,往山下跑去,我們越跑越遠,但隱隱約約,我還能聽見他們這樣唱著。
娘仔仙,娘仔仙,衣衫紅紅,蓋頭紅。
奉茶水,拜公婆,相夫教子起大樓。
誰人知,郎情薄,夜夜宿留花滿樓,
繞白綾,三尺樑,衣衫紅紅,長舌紅。
歌聲越來越遠,我沒能聽懂歌詞到底在唱些甚麼,只覺得旋律讓有不大舒服,跑了一陣之後,我覺得夠遠了,也不大想跑了,這可把白掉嘎的小男孩給急壞了!我不斷給他說,這不過是個遊戲而已,幹嘛這麼認真?他塞給我一把糖球,讓我繼續跟他往山下跑,我吃了一顆,味道不壞,便把剩下的全塞進了口袋裡,才又和他跑了一陣,可說也奇怪,我們上山的時候,明明沒有這麼遠,怎麼下山的時候,卻怎麼也看不到來時的入口呢?
他的臉越來越慘白,他抓著我的手也越來越冷,我不由得把手縮了回來,然後搖了搖手說,我不玩了。
這時候,一大群的烏鴉從林子裡飛了出來,發出惱人的叫聲,伴隨著那首漸漸走近我們的娘仔歌,這種感覺讓人不由得頭皮發麻。
白掉嘎的男孩不由分說,抓著我就要跑,我甩開了他的手,要他別玩了,讓他一起回去找紅衣服的小女孩他們,一同下山玩別的遊戲。這時候他才抓著我的肩膀吼說:「這不是在玩遊戲,這是在抓交替,被抓到的,都要留在這個山裡!」
我沒搞懂他在說甚麼,只覺得歌聲越來越近、越來越近,我的頭好像要裂開一樣,這時候,我突然被推了一把,後腦像是撞到了甚麼一樣,眼前一片黑,就沒有了意識。
醒來的時候,我在醫院,媽媽說,我在往山區入口的那條馬路旁給暈倒了,被巡邏經過的員警給送來了醫院,經過一些簡單的檢查,身體並沒有大礙,隔天一早,就可以出院。
翌日,媽媽帶著我去了一趟派出所,買了一些點心和冬瓜茶,要給員警們送去,他們大人說了很多客套話,我因為閒來沒事,便在派出所裡轉來轉去,我在一面布告欄前停了下來,上面記載了很多走失兒童,令人驚詫的是,上面,就有那個白色吊嘎的男孩。
可男孩,在十五年前,就失蹤了。
我摸了摸口袋,摸到一些乾硬的東西,想起了男孩給我的糖球,便拿出來一瞧,可那哪裡是甚麼糖球?我只看見一些乾掉昆蟲的屍體。
後來沒多久我們又搬了家,上了高中之後,爸爸的工作也定了下來,不再需要外調去其他城市,某一天我問了媽媽小時候的事情,可媽媽似乎一點也不記得,還說我們一家,從來就沒有搬到甚麼山區的小鎮。
ns52.14.141.131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