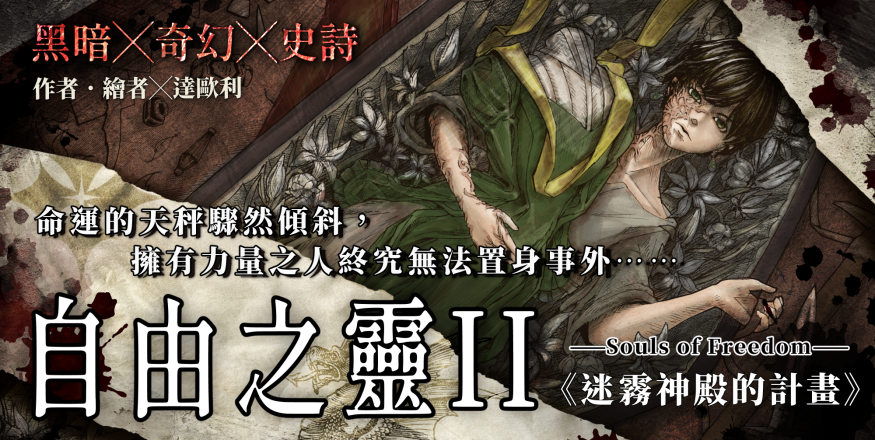就算以她愚鈍的眼光來看,亨謝也是美的驚人。五官柔和秀麗,灰金色的眼眸猶如冬日晨曦,隱隱帶著憂傷。還有一頭銀灰色、彷彿凍結垂楊的長髮。身材高挑挺拔,像是一尊大師雕琢出的藝術品。
然而,他的美只存在於他什麼都不做。
「智慧!」亨謝喊的是古埃德語,通常只會用在古老的宗教儀式上。梅蕾迪斯把信收起,托著下巴,等著看他表演。「無形無相,卻有利爪磨人生疼!」
他甩掉羽毛,重重跳下階梯,「咚」、「咚」兩聲跑到王妃墜崖的窗前,從大桌旁的竹籃裡撈起一隻明顯已經死透的渡鴉。
「噁,這隻吃了特特斯吧?皮膚都是疹子!」這句是通用埃德語。他將渡鴉屍體丟到桌上的銅盤裡,然後從頭髮裡撈出一根還在冒黑煙的羽毛,撥開渡鴉的喙直接塞進去。
「現在要做新的?這是第一步?」她迅速抓起放在桌腳旁的畫板,把炭筆在邊緣抹了幾下,磨出尖銳的角度,快速鉤勒出渡鴉的輪廓。「特特斯會讓心臟衰竭,這樣沒問題?」
研究進行到現在她還沒機會觀摩,不是被安娜拉走、就是亨謝說流程還不穩定,有她在場可能會失敗。
亨謝頓了一下,緩緩抬頭,「不,這是前置作業,只是先確保到心臟的迴路暢通。」他迴身從書架取下一個漆黑的鐵盒,直接忽略她第二個問題。「妳退到門邊,我比較好做事。」
梅蕾迪斯立刻依令行事,生怕亨謝突然改變主意趕她走。鐵盒在亨謝手中發出微弱但絢麗的紅光,映照在亨謝的銀髮上顯得華麗又詭譎。她忍不住發出渴望的讚嘆。
「真漂亮。」好想偷幾個回去。
「用剩的。王城幾萬盞燈,一天就不知道要換下多少。」亨謝往鼓鼓的圍裙口袋撈啊撈,掏出一把鑰匙,「妳親愛的王女多給點經費就不用這麼麻煩了。啊,但被流放的傢伙沒什麼好抱怨的對吧?謠言,混亂,哼!」
「總管大人居然願意賣?」
魔獸核心是魔導具運作的重要資源。二次充能效率很低,但用過的核心依然能賣個好價錢。她曾向勞倫大人提議開發蟲祟淵,計畫利用蟲型魔獸生命力強、群體龐大的特質為騎士團增加額外收入。不知道進行的怎麼樣了……
「王城有幾萬盞燈。」亨謝聲音低了下去,一刀劃開渡鴉的腹部。「女僕很熱心。」
梅蕾迪斯停下手中的筆,「你……算了。」王城有幾萬盞燈。「小心她們拿這點威脅你。」
「威脅?」他哼了兩聲,把掏出的渡鴉內臟丟進一個缽,從頭上又拔了幾根魔驛鳥的羽毛,混進一種像膽汁的綠色液體一起搗成團。「能造成具體傷害的才叫威脅。盜賣的對象也不只我一個。像這樣把大部份內臟替換掉,瘴氣就會由內而外逐漸侵染整具屍體。然後時間會幫我們喚醒它。」
亨謝順勢解說,說完他隨手把殘餘的綠色黏液抹在早已五顏六色的圍裙上。
「跟催眠魔法的運作方式很像呢!」由內而外,一點一點改變。時間長了連根深柢固的想法都能改變。就像「人類」從本質上變成「魔族」。「『王城內埋藏著惡魔』。」
「那是隱喻權力邪惡的童謠吧?」亨謝漫不經心,「無趣!」
「說不定真的有啊!只是這城裡的百合實在太多,花香滿得像氾濫洪水,所以大家才沒發現。」
如果有她還真想看一眼。
魔驛鳥安靜了,亨謝也把處理好的渡鴉放進籠子裡。梅蕾迪斯正要拿下耳塞,就見亨謝抬起頭,朝天花板指了指。「我很好奇,妳在這裡也聞得到?」
「無處不在。」她回應,然後嘆了口氣,捏緊鼻子再鬆開。「我當然想過會不會是幻覺,但在地下那時味道就消失了,梅莉莎的神蹟也——」
「嗯哼。」亨謝制止她,再度比了比樓上。「如果百合的味道等於女神的關注,那這些小傢伙為什麼沒事?」
「為什麼……」梅蕾迪斯皺眉。「因為沒人有行使神蹟的意願?」
「神靈這麼無力嗎?」亨謝嗤笑。「妳只是沒有自知之明。」
「我可不想被你說。」梅蕾迪斯有點惱怒,但亨謝無視她繼續說下去。
「第一,一直以來,除了妳沒有人聞得到。」
「第二,味道在特殊情形下會加強,但同樣,即使有教士或神官在場也沒人注意到。過往神蹟降臨的現象鮮少有花香的例子,更沒有強烈到會把其他所有味道都蓋掉。」
「這些我都知道。」梅蕾迪斯剛開口,亨謝就噓聲要她安靜地聽,抬腳踢了牆邊的渡鴉籠子,屍體僵直地倒向底盤中央。
「第三,我剛剛才正式確定。女神或許在凝視妳,但只要妳無意讓祂進入,祂就無法改變這個世界。證據就是魔驛鳥都還活得好好的,沒被妳說的煩人的神輝殺死。」
「等一下……」梅蕾迪斯扶著額頭,嘗試理解。「你在安慰我嗎?」
「不,這只是事實陳述。」說著亨謝彎身到桌下,翻找著什麼。「今天要來試試嗎?」
「試什麼?」桌底下湧起一股粉紅色的煙霧,把亨謝整個上半身撲成桃紅色。他卻擦也不擦,只是拿了塊布把手楷乾淨,「碰」一聲把一台狀似小型斷頭台的裝置放到桌上。
「『魔暴倖存者』的肢體是否更利於魔力傳導?」亨謝表情變得陰險,把一根羽毛丟上平台,按動開關放下刀刃,粗厚的羽管剎時一刀兩斷。
「那個理論嗎?『突出皮膚的紋路並非單純疤痕,而是增生的可見迴路。由此可推測倖存者的傳導效率比起尋常人類更接近魔獸』……但切開疤痕並沒有觀察到什麼。」
感覺亨謝好像是要轉移話題,但剛才有什麼不好繼續講下去的?梅蕾迪斯抱著困惑,但還是放下畫板走到桌邊,端詳著鋒利的刀刃。
「我很有興趣,但——」刀刃輕易就在指尖留下傷痕,隨即痊癒。亨謝終於撈到一條抹布把滿臉紅暈擦掉,但卻抹上更多黑忽忽的炭灰,看起來更狼狽了。「噗。咳!我最近要參加宴會,安娜一直跟進跟出的,我可不想被她發現。」
「妳多久可以長回來?」對她的嘲笑毫無反應,亨謝盯著她擱在桌上的右手,目光灼熱。
「我沒試過。」梅蕾迪斯惡作劇心起,猛然把右手貼到亨謝面前。果不其然亨謝整個人跳了起來,往後倒在竹簍上,整張臉脹得通紅。「都看這久了你還沒習慣啊?」
「誰會習慣啊!這種醜陋的痕跡!」嘴上這麼說,但梅蕾迪斯覺得亨謝眼神根本不是那樣。那熾熱、執著、不達目的不罷休的神情,跟——呃,跟懷亞特口中看到魔獸的她一模一樣。「多久?」
他頓了一下才決定無視她正假裝成觸手在臉前晃盪的手掌,用力拉過來放到平台上。
「全神貫注的話半天,有藥水的話四刻吧?」她其實挺期待的。這是連埃內斯——她那冷酷無情的父親都不曾嘗試過的實驗。梅蕾迪斯伸展著手指,心裡有些雀躍。「應該能切得很平整?不用固定吧?」
「當然。」亨謝一副「廢話少說」的無奈樣,從書架上拿起另一個漆黑的鐵盒。這個比剛才裝魔獸核心的要乾淨許多。他把盒子打開、放到桌上,一手拿著一塊乾淨的亞麻布,一手扶上開關。「三、二——」
「異端!我都聽到了!」研究室的門被猛然撞開,穿著衛兵制服的金髮男子面目猙獰,衝到斷頭台邊一把揪住亨謝的衣領就往牆上按。「你要對邁爾斯特小姐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