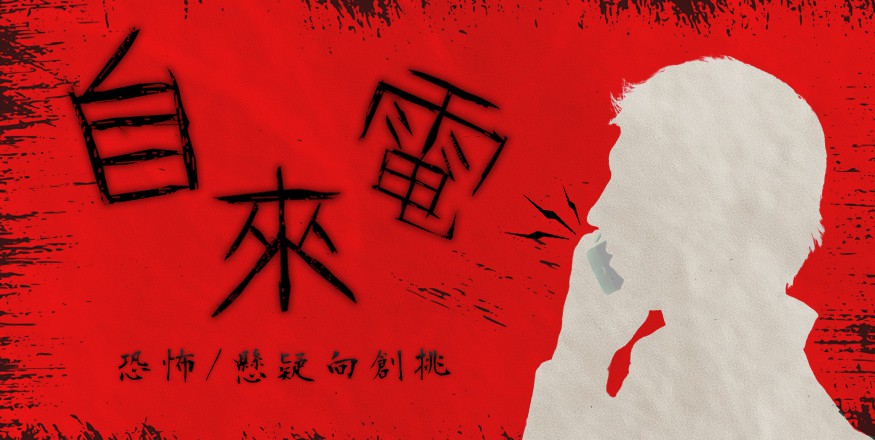我拿著工作證到糧食站換麵包,站員對著電腦一陣敲打,轉身到倉庫。我探頭看了一眼空白的螢幕,啐了一聲裝模作樣。回來的站員發現我的動作,露出厭煩的表情。
「三片,已經給你厚片的了。」
我看了看那不知該如何形容的「厚」;總之不是裸眼能分辨出的差異。除了當成糧食自用,所有作為貨幣使用的乾麵包都是按片來算,些微的誤差就算能多提供一丁點飽足感,在買賣上也毫無用處。
「麵包放到發霉沒人吃,最後還不是用來打發我?」
他大概以為拿出發霉的麵包會讓我知難而退,實際上是把無理取鬧的素材遞給了我。
我大獲全勝的帶著三片沒有發霉的厚麵包離開糧食站,有些意外的看到跟我一樣非常在意麵包的霍爾雙手揣在兜裡看著我笑,不知道看了多久。他肩背窄而瘦,穿著不知道多久沒洗的油膩大衣卻有風流落拓之感,像個飽受折磨的浪子,進可賣騷調笑退可勾引同情。他取得麵包的方式與我不同,我們向來互相嘲笑彼此為撒潑專家和軟飯專家。
我們並肩走向站台。上一班接駁車在我跟站員吵架時已經開走,下一班車在兩小時後。通常我們會在等待時閒聊,事不關己的說著誰誰誰死了,商量著去對方宿舍打劫。不過最近有比討論撿死人的破爛更有吸引力的事。
主城不定時發布的任務被簡稱為主城任務,獎勵多半是些不食人間煙火的花俏東西。但偶爾也會有吸引力微妙的任務類型,上週發布的「永生的阿基里斯」就是這類。參加者所要做的只有按照格式填入一個必死條件,剩下的就是等待主城的居民投票,最高票者將獲得如阿基里斯一般浸入冥河的機會,身上的弱點只剩下他為自己寫下的死因。
如何藉由這個任務得到永生?設下邏輯上不可並存的條件;我們這樣想,大多數人也是這麼做,然而在在目前得票數最高的回覆的襯托下相形見絀。我和霍爾的難以放下不是相信自己也有獲得獎勵的機會,而是因為它開啟了對任務的想像。
「『當死亡條件出現時,若我和初戀在一起了,視為條件達成;反之,條件視為不達成』。」
世界上竟有如此聰慧之人。
「穩賺不賠的買賣。」霍爾語氣飄忽的贊同。
這個人將很快擁有死而無憾的人生。如果他或她是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之徒,這是理所當然;如果這位初戀很不幸的成為了無法和人在一起的狀態,所謂的弱點就再也不是弱點。
「『當死亡條件出現時,若我有菸抽,視為條件達成;反之,條件視為不達成』,你覺得這樣如何?」
「如果我是你,這就是我能想到最穩賺不賠的買賣。」
「我也這麼想,『不划算』的念頭卻總是揮之不去。如果活得夠長夠久,我會有無數菸抽,而不只是臨死前夠送我最後一程的一根。」
「這麼說也不算錯。」
儘管工資減少為三片乾麵包的現在我十足懷疑有無數菸抽的未來能否存在。而且霍爾點出了這件事的矛盾之處。努力工作朝向能夠抽菸的目標前進反而是加速生命消亡的行為,若得到了獎勵究竟要繼續努力還是停止?
「那麼你的買賣呢?」
「跟未來有關吧,例如接到未來的我打來的電話?」
這是個更明顯的悖論,如果將接到「未來的我」打來的電話設定為條件,我會因接到電話失去生命,失去生命的我則不會有未來。
「…我以為會是吃不完的肉罐頭。」霍爾愛吸菸的兔子和我只吃肉罐頭的貓是我們各自生活中的壓力源。
「我可以問問未來是否有無數肉罐頭供我享用。」
等待了許久的接駁車在夜風中一輛輛靠近車站。
接駁車沉默的載我們踏上歸途。它在三號宿舍停下,我從座位上站起,卻發現霍爾坐在原位不動,盯著窗外故意不看我。
車門不等人的關上,我將自己砸回座位中粗魯的再次按鈴。第三次按鈴時我開始計算要搭乘反向的接駁車最晚必須在哪一站下。如果霍爾打定主意坐到底站,我不打算奉陪。
據說底站是一處唯有死亡能夠止歇的尋歡作樂之地,放棄未來的人在此聚集,將一輩子的財富濃縮在短短幾天中的狂歡。我沒有去過,也不認識任何去過那裡還有回來的人,關於它捨生忘死的傳言更像人試圖對無法理解的事物提出的解釋。
否則為何那麼多人在無意義的延長生命,卻有人會在去了某處後再也不回來?那裡必定有某些普通人所無法理解的過人之處。
在生命盡頭追求狂歡,不需要親眼見聞也能想像得出那裡的瘋狂。
「你的表情像是已經想好了葬禮上的悼詞。」
霍爾開了個玩笑,我卻只聽出想避免不歡而散的不祥。從前我以為我們對彼此的壓力避而不談是種默契,此刻我卻不再能自信的分辨霍爾的決定是絕境中的放手一搏還是投向深淵的自暴自棄。
「你知道如果路的盡頭什麼都沒有該怎麼做吧?」
他對我的提問摸不著頭腦。
「回頭啊,白癡。」
霍爾恍然大悟,發出驚動一車暮氣的狂笑。他笑得完全忘了自己的寶貝兔子,只記得向我揮手道別。
我跳下車沿著站牌往回走,接駁車在我身後呼嘯而去。
宿舍本來是這一片唯一會亮燈的地方,但我舉著手機避免撞上一根根在黑暗中靜靜佇立的燈柱時險些錯過宿舍大門。門口長明的燈泡不知何時熄了,我站在台階上往黑黝黝的燈座中望,無用的思索了一會,順利刷卡進門時對不是電力問題感到慶幸。
拐角牆面上的電子鐘漠然的表示時間已來到會讓貓咪憤怒的深夜。我數著號碼找到霍爾的宿舍,闖入前先敲了敲以確認不會進錯門;拉開門,從縫隙鑽入房間中。打亮電燈時我便知道我多慮了,霍爾口中活潑又膽小的兔子既不會從縫隙竄出尋找他的主人,也不會受驚的在黑暗中亂竄被我踩到。
正對著門的硬木板床上用棉被圍出溫馨的小窩,軟綿綿的兔子沉睡其中本該是賞心悅目的景象,如果它不是如此毛髮黯淡且發臭的話。
確認霍爾不會回來後一些散亂的思緒浮出腦海,最遠只能追溯到今天傍晚。他向來花更多時間說服站員多給他一些麵包,傍晚時分我卻在他的注視中走向他,在漫長的等待中漫無目的的閒聊。既然他從未談起,想必知道兔子的死訊只會造成困擾。
我本就對此無能為力。想通這點後我釋然的關上房門。
回到自己所屬的樓層,在宿舍走廊上就能聽見公主瘋狂的撓門聲。她是隻綠眼睛的黑色短毛貓,肚子餓時會由內而外的冒綠光。
食盆中的麵包一動未動,公主連碰都不屑碰。我能放她在家餓肚子是因為今天本來就沒有罐頭給她。一個罐頭值八十塊乾麵包,我現在的工資一天能領三塊乾麵包,她會在肉眼可見的將來餓死,因為她是隻公主貓,公主不吃乾麵包。我的如意算盤是讓她苟延殘喘久一點,餓極了願意接受庶民飲食更好,只可惜她寧可兩天吃一個罐頭也不接受用乾麵包填飽肚子。
我的用心良苦僅收穫了她的敵視,只能以自己的聰明才智苦思冥想。我沒有想到什麼達成了便能死而無憾的心願,於是老套的決定要活得長一點。這需要一個不容易實現的必死條件,我想圍繞著電話就是不錯的主意:接電話看似被動,實際上手機一關就誰也打不進來。
我正這麼想著,讓人感到陌生的手機鈴聲便響起,來電顯示鋪天蓋地擋住了我所在的任務頁面。我懸在提交按鈕處的手指按了個空,不知是反應不及還是驚恐的差點掛斷電話。知道號碼的只有國稅局和我自己,但在我產生任何有趣的推論前我就已將那一長串數字看清楚—眼熟,對一個少有報電話號碼機會的人來說。
「嗨,塞西爾。」
「別害怕,」對面發出一聲輕笑,「如果我沒弄錯,你現在正打算參加永生的阿基里斯任務。你的朋友霍爾有些有趣的想法,你在他面前猶豫不定,內心卻比表面更堅決。」
「你聽起來像我肚子裡的蛔蟲。」
「只要看得夠多,你會發現人們落入陷阱時的姿態驚人的相似。」
「真知灼見先生,你想提出什麼真知灼見?」
「太棒了,你已經開始展現被動的攻擊性。」
「彼此彼此。」
我聽到自己的聲音在那頭的回聲,意識到我們聽起來十分相像;只除了他輕快的語氣讓語尾上揚,像隻要上天的貓。
「好了好了,停止與來自未來的提醒唱反調。」
「你說你來自未來,那你知道你差點害死我嗎?」
「那可真不幸。」
「你…」
「我們可以掛斷電話重新來過嗎?你繼續正打算做的事,只是要比剛才更堅決,而我等等再打過來?」
「不可以。你為什麼那麼高興?」
剛才他聽上去好遺憾,現在他發出一連串誇張的噢噢噢。我想不出來自己如何以及為何會發出如此做作的聲音。
「好奇的塞西爾,都是我的不好,我該滿足你的願望再提出要求。原始人問不出關於黑洞的奧秘,我有自信解答來自你的疑惑。」
「但你連我的疑惑是什麼都不知道。」
「我可沒有自稱全知的神,」他笑道:「大方向不出錯,其餘皆是無關緊要的小節。你的小腦瓜裡彼時彼刻充斥著各種問題,難以抉擇哪個真相能讓自己死而無憾。不論重來多少遍,我都無法準確預知這次你隨便選了哪一個。」
他在距今三年後與我對話。底站之後的樂園不是一般的樂園,是長生的樂園。他的聲音中一直帶著輕鬆的笑意,活潑開朗得像另一個人。先前我只是疑惑,然後我想起自己最後一次出城工作,手臂被岩蟲咬下時也是控制不住自己跟鮮血一起噴湧而出的大笑。
他最後記得的日期是二零二三年的八月三十日,走出宿舍前他砸爛了大廳的電子鐘,當時的溫度是攝氏五度,他只穿了薄夾克,心裡想著會有點涼。然後他沿著街道一直走,打算在碰上車時跳上。手機上的時間和日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不再向前,他沒有感到飢餓或口渴,但因為覺得自己該吃東西而用手從地上摳出石片丟進嘴裡。
「崩了我一顆門牙。」
「我完全聽不出你說話有漏風。」
對面傳來咑咑兩聲:「健健康康。」
「如果這是你想改變的命運,你已經成功了;我這輩子連坐車都不會再坐過站。」
他笑了出來:「不要妄言命運。」
人不會無緣無故走進底站。
乾麵包會減少為一天一片,接著工廠會停止運轉,來自主城的高級幹部們收拾東西離開下城,這裡則徹底成為無政府狀態。考慮到我曾受到的肢體損傷,以武力保護自己度過難關不太現實,在此之前就要做好準備。
他知道我不想死,細緻的傳授我如何到處搜刮,從何時開始固定提出存在糧站的乾麵包,規劃安全點。
我幾乎忘了他一開始是盼著我死的。
「竭盡所能消除你對死亡的疑慮,這樣你才不會將寶貴的必死條件變成沒有盡頭的永生。」
「你想要說服我提交某個必死條件,好在將來死去?」
「沒錯。現在的你會覺得死很容易,可是獎勵發放後就是另一回事了。你以為你在得償所願的死跟碌碌無為的生之間做選擇,實際上只有不如人意的生和死。你不會想…不,你該去看看,同時坐著和同時站著是什麼樣子。」
我的智識無法為我建構出那些邏輯上矛盾的場景,但我猜它們的恐怖之處就在於無法被理解。
「我還是不明白。你為什麼要去底站?」
「你決定要去的時候就會知道,一切都理所當然。但我還是可以跟你說說那是怎麼一回事。
隨著時間過去,你對未來的期待會越來越明確,你越來越知道你所貪戀的是生命的哪些部分。但是陽光沒有回來,植物不會恢復生長,溫度還在下降,金色的大地在記憶中成了看不清的虛像。
沒有乾麵包或罐頭,你開始違反規定闖入死者、病者、弱者、不能反抗者的宿舍,因為不再有權威與秩序會制裁你。你拿出許久沒有用過的刀叉鍋盆,從死人、活人、半死不活的人身上剜下血肉,睽違已久的開始烹調,卻並不享受。你吃過人肉、鼠肉、貓肉…」
「貓肉。」我僵硬的重複。
「是的,貓肉。其他人不會比你高尚太多,所以你不太可能吃到他們的貓。」
「你是個糟糕透頂的人。」
「我知道,用不著你提醒。然後你吃空這裡,有一天決定去看看山的那頭有沒有未來。」
「你是說底站?」
「我喜歡將它看作登山,翻山越嶺,充滿鬥志與努力,符合苦難之後會有幸福的想像。」
如果目標是避免相同的命運,我似乎不該將珍貴的永生機會改為據說終將達成的的必死條件。可是我的聰明才智被無數通電話窮盡,我接到的那一通說服了我這是最好的路徑。我決意要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將條件改為打電話給過去的自己。
那通電話後過了幾個月,我的回覆成為最高票後被鎖定,於是剩下的回覆中自動誕生了新的最高票。跟打電話給我的塞西爾不同,我掐死了公主,跑出宿舍的時候沒有理會一樓的電子鐘,強迫自己停止思考她死前是否痛苦,是否其實寧可餓得形銷骨立也想苟延殘喘。
手機上的時間停在二零二三年的八月三十日,我咬下自己的小指,嚐不出味道的咀嚼。一些無傷大雅的細節差異並不影響前進的大方向。我應該是第一次走上這條路,卻總覺得自己正行走於無數前輩踩出的軌跡上。
二零二三年的八月三十日始終只有一位塞西爾踏足於此,我的腦海中儲存了無數塞西爾的嘗試,他們之間的問與答。
「你為什麼回頭?」
「因為路的盡頭什麼都沒有。」
「也許你走得不夠遠,翻越的山不夠多。」
「我也這麼想。」
「如果我按照你說的做了,你會『得救』嗎?」
「不會。」
底站之後實際上一路向下,身體會自然而然的被重力向下拽。很快我也將之看作登山,有時感覺自己在向天空伸手摘星星。
路途很長,回憶和思想終有耗盡。我腦袋空空的走,最後一個念頭是來自未來的我是正確的。如果不是他口中的信標,我早就無法說服自己繼續前進。我往前走,有時是賭氣,有時懷疑這是一個自以為仁慈的謊言,有時候心中突然升起豪情壯志,腳步不停腳下的路就永不窮途。
我終於找到信標,那是根光禿歪斜的旗杆,被我握住了向前拖行。到了某個時刻,我再也無法向前一步,決定這就是終點。我對聯絡人列表中唯一的聯絡人按下撥打,不由自主地想時間線上各個節點上的我是否會攔截到這通電話。我每撥出一通,就往前走一步,於是我又往前走了許久,在走得更遠的喜悅與尋求解脫之間煎熬。
我向後摔倒在地,胸口悶脹幾近爆裂,狂喜必須得到釋放。
命運要我打通這通電話!
「嗨!塞西爾!」
電話那頭一片死寂,他想必被我嚇壞了!
「別害怕!」
噢,塞希爾,別讓自己聽起來像個瘋子;我覺得三年很不錯,所以我告訴他我來自三年後,在此之前他要一直走,直到看到信標,因為那是我停下的地方。
他問我這一切的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每一個塞西爾都多往前走一步,然後有一天我們會找到想要的未來。
他不知道未來是什麼,所以我為他描繪它的面貌,它在我的腦海中已經明晰,彷彿觸手可及;陽光、空氣、水,霍爾、兔子和貓,我們會走到所有好東西存在的地方。
它提不起我的眼皮,但能讓我嘴角上揚。
「如果我按照你說的做了,『你』會得救嗎?」
「你會。」
ns3.137.174.12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