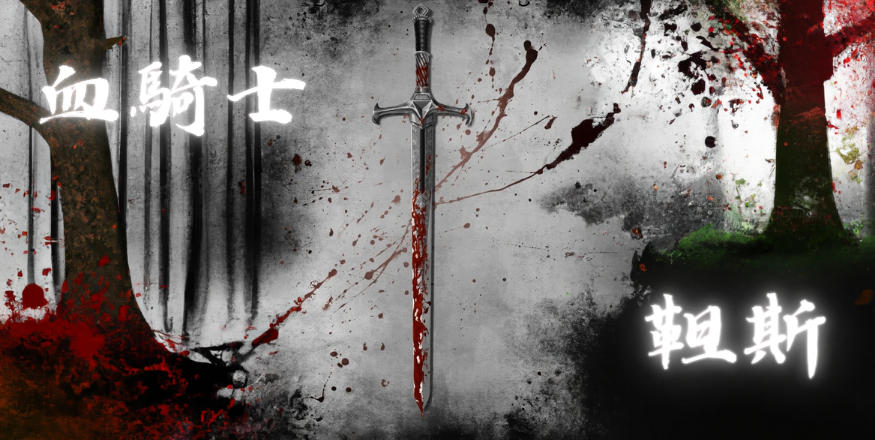x
x
靼斯閉上眼睛。這總是可以讓他平靜下來。
倒不是因為這可以讓他放鬆,或是可以沉思。不,閉上眼睛以後他甚至比張開時更活絡。
他的靈魂會更活絡,因為他裡面的另一扇窗打開了。
是個讓生命之聲流入的窗子。
一開始什麼都沒有。但是沒多久,這『色彩鮮艷』的世界就在他面前展開......當然,這些『顏色』是他眼睛睜開也看不到的,但是他『聽』得到,也感覺得到。就如同一般人可以從鮮綠飽滿的葉子感受到春天的律動一樣,他也一樣可以從樹木的生命之聲聽出蓬勃的生命。且不僅是樹,樹旁的草,草上的花,花旁邊嗡嗡飛的蜜蜂蒼蠅,上頭爬的甲蟲,在靼斯的聽血術前,都有一番美麗的風貌。這個草叢一邊低吟一邊手拉著手在跳舞......啊不,靼斯發現了,它們不是彼此在歌唱,而是它們的花朵正對著蜂兒發出甜進心坎裡的低吟,而蜜蜂也一邊舞著一邊唱『蜜蜜蜜,覓覓覓』,然後迎了上去。而在另一棵樹上,有隻小甲蟲躲在樹木的歌聲中,偷偷唱著求偶之歌;唱得歪歪扭扭,不甚悅耳,但認真的態度使靼斯會心一笑。他就這樣走進這些生命的歌曲之中,他也感覺到自己的生命越來越單純,越來越像小孩,好似生命中的煩惱,人前的偽裝,都隨著歌聲而被洗淨,散在飛出去的音符中。他的靈魂開始在這些交織的生命之歌中跳舞,而他的舞也激勵了附近的歌,使大家不管本來在唱什麼,都唱得更賣力了。小草更多的唱著『長長長』,搖頭晃腦的聲響宣告著成長的渴望。土裡的蚯蚓因著土壤鬆軟而發出幸福的吟唱,而這吟唱在他心上打著拍子,每打一下都給靼斯無比的滿足......
然後他聽到了。
眾多歌聲中,他聽到了一聲召喚。聲音非常小,但是非常精確,好像在眾多樹木中,看到一隻從草叢中伸出的手,朝著他招手,要他過來。
那是個強大卻不強硬的聲音。
那是個複雜而不自然的聲音。
那是個細微但卻刺耳的聲音。
那是個奇妙且又誘人的聲音。
但,那卻是靼斯熟悉的聲音。所以他跟了過去。當他伸出手,觸碰那聲音的那一瞬間,整個世界的聲調都翻轉了。本來他聽到森林那很單純的生命之聲,都轉變成另一種更悅耳美妙,更細緻複雜,卻失去純樸樣貌的歌聲。那種炫目的美,使靼斯沉迷,久久不能自己。那聲音又如同揭幕一般,再把靼斯帶到另一個地方;那不是真的『地方』,而那些『歌』也不是真的『歌』,而是那個聲音在展示一個夢想,一個期許,是一整個活絡的忽爾乎達支派,在營地裡高聲歡呼歌唱,裡面人的歌聲比靼斯過去理解的更複雜,也更美妙;但最重要的是,變成難以干擾或是間斷的歌。生命之歌通常都會因著疾病或受傷而轉弱,因著死亡而消逝;但這種歌似乎無法被中斷,一首接著一首,歌與歌之間有個很奇妙且複雜的東西使之強化,使之整體強壯且美妙,成了無所敵擋、無畏無懼的歌。
靼斯被這些歌聲激動,讓他也跟著高歌起來;但跟剛剛孩童之聲不一樣,這次他開始讚美這強力且美好的歌,崇拜這美好的夢,想宣揚這歌的偉大,將之唱出去,唱到血族人之中,好讓這樣的強壯和美好占據忽爾乎達,或許他們就再也不用害怕任何的敵人......
歌曲中斷。
就在那一瞬間,所有的聲音都縮進一個點裡。那個點就是本來朝著他呼喚的聲音。而從那聲音之中,靼斯聽到了有另外兩個強壯的聲音臨到,那個聲音不得不中斷對靼斯的吟唱,轉而面對他們。
靼斯轉回頭,看看本來的森林之歌。還是一樣的美好且單純,但是靼斯心裡卻好像空了一塊。
沒有那麼強壯,也沒有那麼艷麗。
靼斯想念剛剛那首歌。
他眼睛睜了開來,因著不適應光線而眨了眨眼。剛剛美好的歌聲都嘎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眼前的密林,以及遠方血族人輕微的生命之歌。
靼斯必須要知道剛剛他聽到了什麼。他知道那聲音的來源是誰,他認識那人,所以他想要去找那個人。
靼斯離開了他平常喜歡靜坐聆聽的小丘,穿過了的巨木及樹叢,避開了淚蜘蛛的巢穴以及黑土熊的排泄物,遠離罪行獸的惡臭體味,然後找到了入口。
地下實驗室的入口。
入口處是一個圓扁大石,上面長滿了植物以及青苔,使得大石跟林地黑土幾乎融合在一起,任何路過的人都不會發現這是某種入口。靼斯翻了翻遮蔽的植物,把手按在一個看似過分巨大的蕈類,但實際卻是一個石雕上,而那石雕發出鮮紅色的光,圓扁的大石就朝一旁移開,露出樓梯來。
靼斯走了進去,沒多久之後大石就合上,陰暗濕冷的地道中只有牆壁上的符文發出微光。走沒多久,他就開始聽到清楚的對話聲音,而他也繼續前進......
…...直到他發現對話的對象之一是他父親。
「......到底在幹什麼?」此時發問的是大酋長。
「例行性的實驗。」回答的聲音粗曠但是枯乾,像是中氣十足的老人。「為了忽爾乎達的安危,我們必須要讓血魔法更加的進化,才能在天使靈敏的鼻子前隱藏......」
「這種官話俺聽膩了,欽薩。」大酋長繼續說。「為什麼你半夜需要帶屍體進來?你為什麼自己看起來像個該死的屍體?他媽的你是一百年沒吃飯了嗎?」
欽薩沒有回應。
「最近有淺列族的夫婦到我們這裡來。」多薩馬開口了。「從他們口中我們得知淺列支派除了他們之外已經滅族了,而且滅他們的並非我們認知的天使大軍,而是指揮元素的天使。」
「指揮......元素?」欽薩說。
「而且裡面有死亡元素。」多薩馬說。「我們合理的懷疑,雖然淺列支派聲稱他們不使用血魔術,但是還是有人使用過頭了。」
欽薩突然發出陰笑。
「如果像他們這樣都會因著死亡元素而滅族,那我們是不是該對血魔術更謹慎保守一點?」多薩馬說。
「多薩馬,不要鬧了,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欽薩說。「我們能安全,不是因為我們在血魔術上保守,而是在血魔術上精進。你並不瞭解元素的運作。就算是我再瘋狂個十倍,遠勝我們父親好了,我頂多就是被魔法給反饋,我見不到元素的。」
「況且,如果是淺列的某個人做了什麼,元素只會找他,幹掉他,接著就會消失了。死亡元素滅族?那要整個族都跟我們父親一樣瘋狂才可以。」
「所以我不管你聽到什麼故事,但是那個講故事的人很明顯的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俺不管這些。」大酋長說。「俺只知道這聞起來不對勁。不管是這個實驗室或是淺列的滅族方式。俺希望你低調,俺也希望你他媽的給我講清楚你在搞什麼鬼東西。」
「尤魯多薩......」
「怎麼?現在了不起了?連大酋長都懶得喊了?」
「......大酋長。尤魯多薩大酋長。」欽薩說。「我們不可能在血魔術上保守。忽爾乎達太大了,而且我們並沒有住在任何遮蔽內,使我們顯眼到附近的罪行獸以及淚蜘蛛會整天來騷擾我們,而光是跟他們打爛仗就足以引起天使注意了。就是我的血魔術才有辦法欺哄所有的生物,讓他們認為這邊是一點也不重要的地方。」
大酋長以及多薩馬都沒回應。
「但是光這樣還不完美!如果只是這樣,我們也只能苟且偷生。而且誰知道能活多久?如果等到我死了,賽倫那個草包又什麼都不懂,若沒什麼人可以好好接續,我們就曝光了,那離忽爾乎達滅族也不遠了。不!我們必須要更積極一點!最好我們能帶著這個法術移動,這樣我們不會只是被動地躲在這裡,而是可以進攻,甚至可以拯救其他支派......」
「沒有其他支派了。」大酋長說。「淺列是最後的了。」
欽薩愣了好一陣子。
「所以我們要更加積極!」欽薩說。「如果我們再怠慢的話......」
「如果我們再更積極的話!」多薩馬說。「你都忘了父親當時發生了什麼事嗎?死了多少人?我們不是該記取那時候的教訓嗎?」
「父親根本不管支派的死活,才會導致這個結果!可惡!難道我的苦心你都不懂嗎!」欽薩聲音越來越大。「你難道不知道為什麼我要把我自己關在這裡嗎!如果要為所欲為,我不能出來當下任的大酋長嗎!如果血族可以跟這個世界和平共處,我也不需要......」
「這樣你只會做出更誇張的事,像父親一樣。」
「你給我把這話收回去。」欽薩說。
靼斯看不到現場,不知道父親有沒有比什麼動作或是什麼眼神,但是接著他聽到有點類似肢體衝突的聲音;而除非父親刻意想挨打,不然欽薩叔連他衣角應都摸不到。
…...如果他不用血魔法的話。而靼斯已經聽到了,欽薩叔的血充滿憤怒,而且隨時準備好使這樣的憤怒轉成力量投射出去......
…...但是他沒有。他硬把怒氣吞了下去。
「滾出去!」他吼。「全部都滾出去!」
「或許你可以叫那個對你過分溺愛的長兄滾出去,但是你對俺沒有這個權柄。『差點』是大酋長不代表你是大酋長。」大酋長說。「欽薩,這是最後警告,俺不想看到你再做奇怪的事。若是再發生,俺不管你是不是忽爾乎達的血術大師,俺會自己來對付你。你聽見了沒有。」
欽薩沒有回應。
「聽見沒有!」
這吼聲大聲到連躲在走道的靼斯都縮了縮身子。
欽薩還是沒有回應。但是不知道他是有比了什麼手勢,或是大酋長已經滿意了,所以他就帶著多薩馬從實驗室另一頭出口離開了。
沉默佔據了整個實驗室。靼斯不知道該不該出現,還是就這樣偷偷回去比較好。
「是靼斯嗎?」欽薩說。「過來吧。」
靼斯這才離開彎曲的走道,走進了實驗室。
ns3.144.220.79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