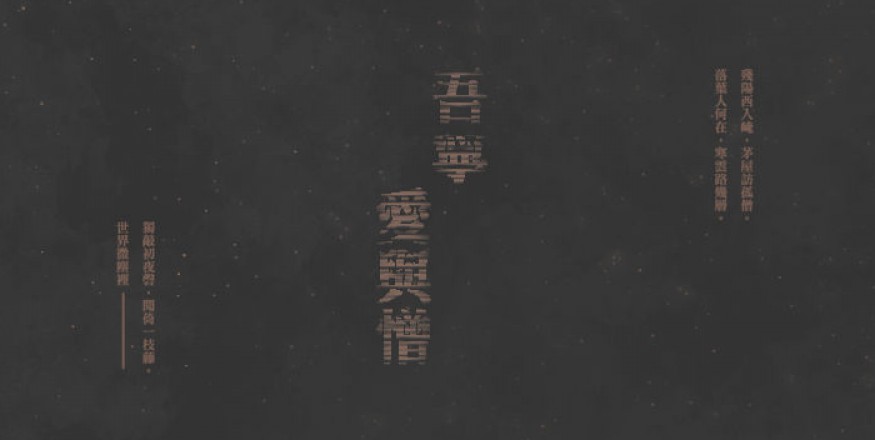死亡時間,晚上十點零六分。
護理師看著手腕的錶,誦讀時間,接著拿下北張罔市臉上的氧氣面罩,隨後離開。
北嫺怡的目光在北張罔市的軀體逡巡,它是如此的死白,白裡透著朽敗的青灰。她知道北張罔市早就走了,在她趕到醫院的前一刻。替祂掛上氧氣面罩、坐著救護車直奔南部老家,不過是遵循習俗──要在家中嚥下最後一口氣。
金黃綢布自正廳的橫梁懸掛而下,遮蔽通往其它房間的左右出入口以及正對大門的供桌,圍出屬於往生者的空間。北張罔市躺在位於正中的鐵架床,雙眼緊閉,嘴巴微張,臉頰塌陷得好似剜去了肉,薄薄的皮緊貼出顴、頦骨的形狀。
「怎麼走的?」
二叔端著一盆溫水,走進正廳。他是北嫺怡最先通知的親人,也是目前為止抵達老家的唯一親人。
閒談的口吻,彷若他們之間從未有過疙瘩。北嫺怡斂眸望向那盆溫水,盪漾的水面裡有著同樣垂下眼的二叔,兩人的視線藉此相對,「吸入性肺炎引發的敗血症,最後……造成敗血性休克導致多重器官衰竭,醫生說阿嬤一直在昏迷,走得並不痛苦。」
北張罔市離去得很突然,卻不意外。
二叔沉沉的吸氣聲響起,抵在胸前的臉盆被往前推了幾吋,她聽見二叔毫不責怪的對她說:「妹妹啊,辛苦了。」
感傷不多、衝擊不多、自責不多,多的是如釋重負的輕快。他們是何等的感激,感激北張罔市薄弱的求生意志,興許,這是祂身為長輩,贈予他們的最後溺愛。
只見二叔繞過她,將溫水端給站在床旁邊的土公仔,讓她幫北張罔市擦身、整理遺容、更換壽衣。土公仔是二叔依照北張罔市生前的囑咐,請來處理後事的人,北張罔市不喜歡現代感甚重的禮儀師,不喜歡殯儀館冷冰冰的冰櫃,祂說土公仔是祂的老朋友,早就約好後事會給她操辦,祂還說祂很怕冷,死後不想要待在那冷颼颼的空間那麼多天。
活著的時候不懂得順從,死去的時候倒是滿足了祂所有的心願。土公仔的助手在正廳角落放置一台念佛機,純黑的小型錄音機不停吟唱南無阿彌陀佛的韻律,度化亡者,也度化生者。
助手走了過來,拿著一張表格與他們商量喪禮的程序,天氣炎熱,北張罔市沒進冰櫃的遺體不能久放,入殮、做七、做旬等等儀式都得提前並簡化。北嫺怡愣愣的,跟隨二叔點頭答應,「從簡就好」據二叔說,也是北張罔市的願望之一。
毫無用處的北嫺怡杵在一旁,終是發現,自己只是個旁觀者。聽著二叔宣洩情感般,抱怨亦懷念的傾訴,訴說北張罔市在未生病之時,總愛反覆交待這些後事。她聆聽,插不上一個字,甚至要她舉出五個關於北張罔市習慣、愛好,恐怕想破頭都是白做工。
她終究醒悟了。
她付出得太少,索求得太多。
她不曾給出自己的真心,卻總要別人真心待她。
守靈的日子是一成不變的枯燥,接下來的幾天北嫺怡都待在寬闊的埕裡,搭建在那的靈堂占走三分之一的空間,遮陽擋雨的塑膠帆布立起棚子,涵蓋整個埕。每天,她都坐在跟鄰居借來的、擺放在埕裡的流水席大桌椅上,與早已生疏的堂兄弟姊妹圍成一圈,靜靜的摺著紙蓮花、紙元寶,好似這樣就能抵銷曾經不堪的念頭,以及過往的自私狹隘。
她攬下所有治喪的瑣事,騎著機車,千里迢迢,從山區老家前往鎮上,為了去衛生所開立死亡證明,為了去區公所辦理火化申請,為了去她阿公所在的寺廟,購買新塔位與骨灰甕。土公仔不像葬儀社,包辦所有事務。
她終於主動的、由衷的,替祂做好一件事,亦是她能為祂做的最後一件事。
來回的路途已不是小時候的崎嶇蜿蜒,但她騎著,眼前的柏油路總是重疊著過去黃沙路,路中央有位奶奶腳踏老鐵馬,後頭一位身穿小洋裝的女童用她短短的胳膊環抱奶奶的腰,鐵馬後輪捲起一陣紛飛細沙,朝她襲來,她眨了下眼,切斷時空交錯,前方只剩筆直且暢通的馬路。
她笑著,紀念這段回憶。
死亡赦免一切負面,僅留下無盡的緬懷,彷彿他們未嘗有那麼一秒,厭煩病重的北張罔市,祈禱北張罔市消失在他們的生活。
出殯、火化、入塔,一件件按照排定的時程到來,十幾天的喪禮跟風一樣,輕拂即逝,而人,乘著風,到那遙遠、觸及不到的天,沒有病痛、沒有罣礙,與活著的人不再有實際的接觸,留下的,僅是一縷如煙的念想。
這晚,北嫺怡留宿在南部老家,家裡空蕩蕩的沒有人氣,喪禮終了,人也散場,或許往後再不會有這麼「熱鬧」的時刻。她躺在北張罔市生前的床,放空思緒,把今夜當作陪伴北張罔市的最後一夜,不久,便沉沉睡去。
迷濛間,她睜開眼,日正當中的豔陽直射瞳仁,亮得世界朦朧,但她竟不覺得疼痛,反而莫名的知道自己正在老家的埕裡漫步繞圈。她不慌張,這裡有股讓她安心的氣息,她放空腦袋順著心意走了幾步,左手忽地被微微一勾。
北嫺怡偏頭,身旁多了個人影,但模糊的眼底世界使她看不清來者的面容,可是──
她的心知道祂是誰。
剎那,她哭了,熱淚奔瀉而下,轉眼便抽噎得發不出聲。
是歉疚、是思念、是感謝。這次,她不需要對方來愛她,她只期盼對方曉得她是愛祂的,儘管她悔悟得太晚。
「哭什麼呢?」
話語剛落,花露水的香氣淡淡繚繞。淚水暈染視野,本就不清晰的景物更加混濁,可北嫺怡似乎能看見,對方那包容一切般的慈祥微笑,不知不覺,她也漾出絢爛奪目的笑容,如同這道璀璨的陽光。
心裡若有祂,無論漂泊至何處,哪裡都是家。261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4sDsf9ivJg
261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g4SHT9tSVV
「北嫺怡。」吳寧盯著右首尼姑,輕喚她的名字,「是,我認得妳。」
語落,狂風驟起,檀香撲面,右首尼姑忽地打回原型似的,不復先前模樣。吳寧微瞇雙眼,這般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變竟沒讓她有絲毫的惶恐,她打量北嫺怡的及肩短髮、眉上劉海,加上圓滾滾的眼眸,讓她的外貌年齡銳減,她身材勻稱,不似故事描述的枯瘦萎靡。
「不是這樣的……」吳寧連連搖頭,「不是妳說的──」
「當然是,怎麼不是?」
「北嫺怡,妳沒必要欺騙自己。」
北嫺怡淺淺一笑,「我沒有。走的路不同,到達的地方不一樣罷了,但是……那都是我的故事。」
「不、不對……」
北嫺怡向著吳寧跨出一大步,伸指,輕輕的點著她的眉心,「妳聽清楚重點,無論如何,那都是『我的』故事。」
「那、那……」吳寧眉眼耷拉下來,目光盡是旁人不明所以的乞求,「妳可以原諒我嗎?」
北嫺怡輕笑,閉眼無奈的晃著頭,她指尖一推,竟讓吳寧往後退了半步,「我沒有資格原諒妳。」
說罷,北嫺怡收手,旋身,背對著吳寧,不發一語。
「北──」
「好了!」中間的尼姑橫插進來,硬生生擋在兩人之間,「時間寶貴,吳寧啊,妳就不要再糾纏啦!」
「妳……」
「聽聽故事吧,妳也會認得我的。」261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hRcHrLqlr8
261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BXCNKdhx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