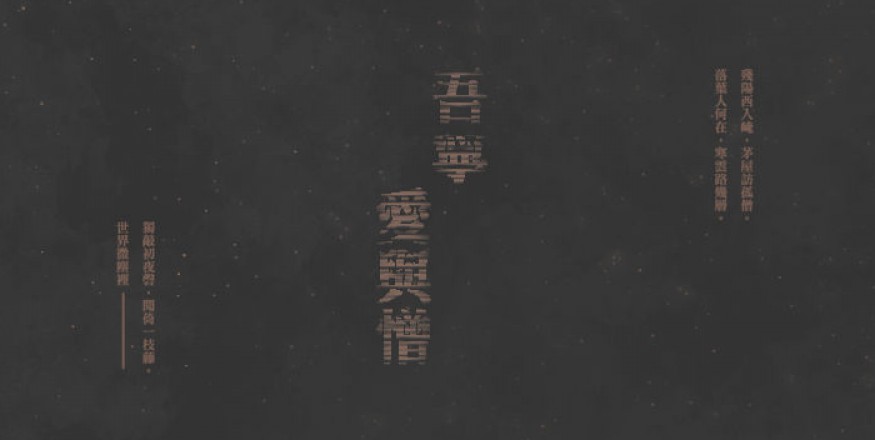剎那間,火藥味奔湧而上,空氣稀薄得令人窒息,如同北嫺怡偷聽到兩人秘密的那晚。
「但我們其實都知道。」驟降的氛圍好似影響不了酒友,只聽他接續說:「我們都以為沒人可以代替小筠。小筠發生那件事後,你家也出了些狀況,我們很怕你爬不起──」
「閉嘴。」
單良延的語氣冰冷且陰鷙,北嫺怡打了個激靈,而酒友充耳不聞,沉靜的說著自己的話,「──來。後來你開了家麵店,撐起單家,然後結婚,我們私底下都在慶幸你真的走出來了,直到我們見到北嫺怡。」
酒友刻意停滯幾秒,等待單良延的暴怒。
噗嘶──
單良延拉開一罐新的啤酒推給對座的酒友,緘口不言。見狀,酒友順手接過,他能看穿單良延鎮靜面皮下的猙獰,那是為了逃避事實而生的戾氣。酒友昂頭猛灌一口,不禁呵呵哂笑,似在責備他的荒唐,「小筠就是小筠,北嫺怡也永遠是北嫺怡,不是嗎?」
「你到底想說什麼?」
「雙胞胎再怎麼相像,也是獨立的個體,何況北嫺怡不過是某個角度很像小筠。我不懂你這麼做是能得到慰藉還是怎樣,但我真的很看不起你,要嘛對人家好一點,要嘛離婚放人家走。」
霹靂啪啦。
喝得精光的易開罐在單良延的手中扭曲扁塌,只見他臂膀一瞬擺盪,銀光飛擲而出,堪堪掃過酒友的額側,接著匡噹脆響,易開罐撞擊牆壁彈到了地板。
「我對她哪裡不好了?」單良延壓抑的嗓音緊繃,聲量漸大,「供吃、供住、供穿,連她阿嬤都過來了,我有對她怎麼樣嗎?我有要她做什麼過份的事嗎?只是讓她用那張臉滿足一下我不行嗎?她的用處就是那張臉!」
「良仔……」聞言,酒友無奈且失望,他瞄了瞄樓梯,「你小聲一點。」
「怕什麼!被她聽到又怎樣!」單良延拍桌站起,被酒精醺紅的雙眼直瞪對方,悶在胸腔的怒氣使得他吭哧連喘。但很快的,他鎮定下來,揚起一抹滲人的淺笑,「反正她離不開我。」
是,她離不開他。
反抗,即是自我毀滅。
北嫺怡縮回另一隻在門外的腳,徐徐的闔上門,不帶一絲細碎響動。她回到廚房煮飯,動作沒有一丁點躊躇,彷彿什麼都沒發生、什麼都沒聽見。不一會兒,蔬菜粥的香味瀰漫整個空間,她舀起一勺嚐嚐鹹淡,隨即熄火,添了一碗熬得濃稠的粥走到北張罔市身前。
幾步路的距離,已讓她感到雙腿無力,掌中的碗傳遞滾燙,卻捂不熱她的手。
她知道,有了北張罔市,自己是更加離不開他了。
難怪單良延從未對她的家庭背景有任何意見,原來只是心懷鬼胎的包容。
「阿嬤……」北嫺怡坐到左側的沙發上,垂首,望著捧在胸前的粥,「我真窩囊……」
北嫺怡拿起小湯匙輕輕攪拌,在稠得有些固態的米粥畫出一圈圈的線條。蒸氣四散,替她流不出淚的眸子釋放一點潮意,北嫺怡說不清她內心的感受,她曾以為他們最初的結合是因為愛,她仰賴、她依附,她渴求安定,可現實總是背道而馳。
沒辦法,她如今無非是隻沒有主導權的寄生蟲,那麼,寄生在寄生蟲上的,又該如何是好?
北嫺怡舀起一口粥,遞到北張罔市嘴邊,輕碰她的唇。北張罔市反射性的張開嘴,讓北嫺怡餵了一口,她瞅著北張罔市似嚼非嚼的蠕動下頦,忍不住說:「阿嬤……妳可以跟小時候一樣,摸摸我的頭嗎?」
空洞的眼神,是北張罔市竭盡所能的應答。
北嫺怡盼望的奇蹟沒有出現,為了她而短暫清醒的劇本沒有上演,甚至兩人的目光毫無交集,「阿嬤,我好難受……阿嬤……」
她的語氣是心灰意冷的平淡,說出口之時,她便明白,這個世界已經沒有人真心待她,已經沒有人會憐惜她。那個輕撫她的頭、要帶她回家的北張罔市早就不在了,不會再回來了。
此時此刻,她終於正視到失智症給予的核心傷害。
北嫺怡移開注視,冷漠的雙眸黯淡無光,曾經的熱情親暱、甘願付出已然化成灰燼。
那晚過後,單良延依然堅守他的「秘密」,殊不知,這個秘密繁殖了另一個屬於北嫺怡的秘密。兩人的互動沒什麼變化,終歸不是恩愛夫妻,之間的裂縫多出幾公尺又如何?反正不都一樣,他過他的,她過她的,各取所需。
「您好,是北小姐吧?」
如此渾渾噩噩的過了兩個月,期間,北嫺怡並未憶起前往醫院諮詢的事情,只求便利的替北張罔市穿上紙尿褲。直至北張罔市的病況出現更明顯的惡化──精神症狀在日間頻繁發作,以致於餵食、擦澡、替換紙尿褲等等事物,都得耗費過往的兩倍時間。
也一齊耗損了她僅存的耐心。
「是,我是。」北嫺怡抬眸,漠然的環顧一周,此處是醫院附設的照顧管理中心,窗明几淨的諮詢室仍然無法讓她有一刻的放鬆,「我有先看過長照服務的項目,但是……好像都不太適合我。」
坐在她對面的個案管理員掛著微笑,將桌上一張花花綠綠、條列所有長照服務項目的宣傳單推向她,並輕柔的道:「我翻閱過諮詢紀錄,大約知道您親人的狀況,嗯……的確失智共照中心與失智社區服務據點,較不適合像您親人這樣的中晚期患者,但我們還是有照服員可以提供居家照顧。」
「但居家照顧主要是早上,不能選晚上吧?」北嫺怡連瞄一眼宣傳單都懶,那上面的內容她早看過網路版本了,「我早上雖然需要工作,但還能勉強應付,我只是……想要好好的睡一覺。」
個管員聽聞,打量起她憔悴的容顏,竟描繪不出她原本的樣貌,但見過如花天仙被摧殘凋零,北嫺怡這神態對個管員來說,仍不算慘烈,「既然您的需求是夜間照顧,那我會建議您請全天候的看護。」
北嫺怡安安靜靜的,像是在聆聽,像是在發呆,沒有接話。個管員只好繼續說:「外籍的話,必須先請醫院開立巴氏量表才能進入聘僱程序,可能需要等待兩個月左右,本籍的就不需──」
「如果是療養院呢?」
「嗯?」個管員愣了愣,對著北嫺怡始終如一的面無表情答道:「您是指護理之家跟長照中心吧?那也是可以的,您親人並沒有插管,設備及照護需求會比較低,不管是護理之家還是長照中心都能去看看。」
「好,謝謝。」
北嫺怡從沙發站起,強行結束這次諮詢,而離開的腳步與進來時一樣,沉重且拖沓。她沒有多加理會個管員的反應,滿腦只塞得下每個管道會遇見的阻礙。
倘若申請看護,先除去等待時間與金錢,光要讓家中再多一個人就是個大挑戰,再者,這人並不是她或單良延的親戚朋友,是貨真價實的陌生人,品行、生活習慣等等根本無法預測,新聞上看護虐待、偷竊的事件可不少。
那麼,送去療養院……二叔他們會同意嗎?
思及此,北嫺怡不禁露出揶揄的笑,笑自己的多慮。北張罔市住進單良延家近三個月,他們從未打一通表達關心的電話,更遑論親自過來探望。或許她把北張罔市送進去療養院待到死,二叔那夥人都不會發現呢。
北嫺怡走出醫院,曬在皮膚上的陽光和三個月前、接走北張罔市的那天一樣熾熱,只是風有些轉涼,彷若她的心。26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YgQ3e1LZg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