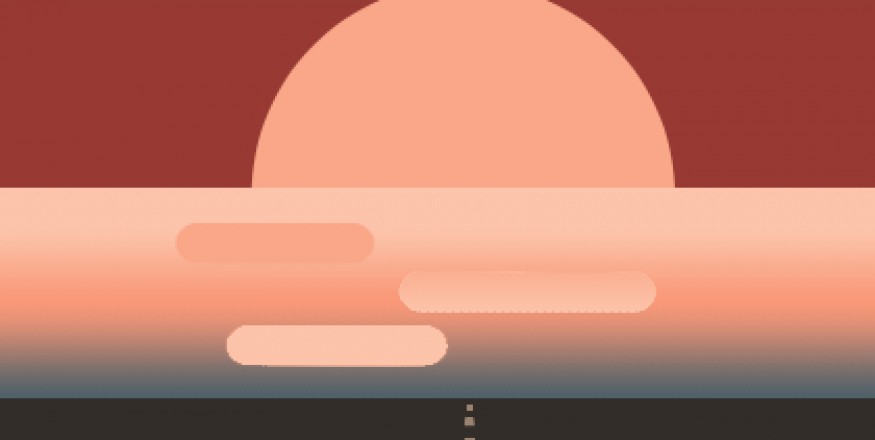12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pzLqIavNr0
5、雨紛紛(中)
「幸好聲音剩雨的水滴,否則我會赤裸地像條魚。」
Ng過了一會才發現說話的是自己的聲音,他不知道自己在何時說了這些話。接著聲音變成激烈的爭吵,但不再是自己的聲音。
「幫我?用那種垃圾根本是給我多找麻煩!」一個男人的聲音吼道,接著罵其他人是豬玀。
「你醒了。」一個中年男子進門,語句平淡,單純陳述事實。是剛才的爭吵裡罵人的那個。除了臉色較紅外,表情跟口氣不像是剛跟人爭吵過的模樣。
「你是誰?」
「安哥。」安哥從一串芭蕉裡,拔了一根黃的,撥開,露出偏白的果肉。「記得自己是誰?」
Ng搖頭,「這裡是哪裡?我為什麼會在這裡?」
「你叫Ng。」安哥說完後咬下那根黃蕉。沒有回答其他問題。
阮志德是被冷醒的,他打了一個噴嚏,起來時覺得全身痠痛,鼻腔裡都是陌生的氣味。空調的溫度太低,讓他打了個寒顫。
「早安。」一個男人的聲音跟他說。
阮志德抬頭,他困惑地看著眼前陌生的男人,片刻間他才發現那是昨晚那位南薊雉的人,昨晚的回憶立刻灌回腦中。
「睡得舒服嗎?」那個南薊雉的男人放下手裡的蛋花吐司,提起桌上的塑膠袋,抖了抖。「幫您準備的,可惜不知您喜歡的口味。」
小的單人床他睡得一點也不舒適,還有空調太冷,他整個人都縮成蝦子,而南薊雉的那個男人還不知道在這間房裡待了多久。可是阮志德沒有什麼都沒說,眼神死死的盯著對方。
「咖椰吐司,我們在這裡的朋友推薦的。」南薊雉的男人放下手裡的袋子。
「你到底是誰?」阮志德問,又隨即補充:「我知道你是南薊雉的人。」
「誰也不是,不過是跑腿打雜的。」男人吸了一口飲料。「這麼說吧,您可以稱呼我『陳濁水』。如果這能讓您安心的話。」
阮志德不相信對方自稱的那個名字,然而他也不知道自己還能再相信誰。他的的拇指、虎口及食指貼在額頭,「我要去洗個臉。」
他走進浴室,上完廁所後刷牙、沖把臉,卻沒立即用毛巾將臉上的水珠拭去,而是放任水珠流下臉頰,匯集在下顎,最後滴下。
他盯著水盆裡的反光,良久,打開水龍頭,水不斷流入排水孔,能聽見迴盪著於水管內的奔流。
Ng是被不適的呻吟聲給吵醒的,接著他才意識到是自己所發出的。他感覺自己全身僵硬,正想改變自己的睡姿時,一股拉扯阻礙了他的動作,在那一瞬間他完全清醒。
「午安。」陳先生翹著腿,交疊的雙手把筆記本壓在大腿上,並在兩指間夾著一枝筆。
四肢被縛在床上的Ng沒有掙扎,他不打算做如此浪費力氣又毫無作用的舉動。他眯起眼看向發話者,對方口說的腔調是屬於南薊雉的,接下來眼神飄向房間內的各處,並在阮志德身上多停留幾秒。
「黃先生,」陳先生說出Ng真正的姓氏。他翻開筆記本,讓筆在兩指間轉動。「我們沒有意願傷害您。」
陳先生停頓了一下,無人接話,他補充:「若您能配合我們。」
「我們。」阮志德在心裡複誦一次。哪個我們?他想。
「前幾日條月國西北的大城有個傳聞,」陳先生的手繼續轉著筆,毫無做筆記的意願。「據說對條月的聖堂進行恐怖攻擊的主使者,並非為條月族群,而是國家內的其他種族。」
阮志德困惑得唇些微開闔,然而在發出聲音前趕緊閉上。
「商會立即發佈聲明,與恐怖行動撇清關係。」陳先生繼續,「不過戰後的這幾年間,的確有幾次對城市的游擊戰,是秋牡國族裔的組織做的,背後的金錢來源皆來自商會。」
Ng與陳先生對視,不發一語。
「不過那些都是不成氣候的東西。」陳先生表示。「隨便抓一個青年,再用民族尊嚴說服他為這個民族送死。」
這是陳先生第一次下評斷,然而口氣或神情卻無任何情緒上的起伏,維持一慣的文雅。
矯揉造作,Ng認為。他沈默,等著對方慢慢出牌。
「你認為恐怖行動是他做的?」反倒是阮志德展現出自己的不安,卻在自己開口後立即反悔。明明在小時候,爺爺總是要求他有耳無嘴,小時候輕鬆達成的事,到了現在卻十分困難。
「阮先生,若您覺得精神疲倦,何不回飯店休息呢?或是去外頭散散步。」陳先生低頭翻閱腿上的筆記本。
「沒事⋯⋯我⋯⋯抱歉⋯⋯」阮志德咕噥道。這是他們兩人的協議,出於同情,陳先生不強迫阮志德迴避審問,前提是阮志德不能開口。「無論您的朋友記得什麼,都可能暴露重要資訊。」阮志德在心裡默念幾次陳先生對他的建議。
「恰恰相反,我們並不認同這種殘忍的行動,會是您執行的。」陳先生抬頭,繼續轉筆。「但,或許您可以談談自己的想法。」
Ng保持沈默,連臉部都沒有因為聽到對方的話,而起到任何細微的變化。
陳先生的獨角戲倒演得無所謂,縱使兩個國家為敵對狀態、有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不過基本的訓練大多相似。他沈住氣,正常人到這時若不是在被恭維後滔滔不絕,不管是要表現出自己的高人一等,還是憤怒地打斷他們的話;要不就是被這些毫無章法的閒聊逼到受不了,反問他們究竟想得到什麼。這兩者為一的共通點都是激烈的情緒波動,只要情緒被牽住了,套在脖子上的項圈就再也取不下來,最後項圈成了上吊的繩結,自己將自己勒斃。
Ng的安靜過於標準,完全是按照教學所複印出來的模子。跟「那個人」不一樣,陳先生心想。越是沈默的人,越能驗證是自己人,「那個人」當時就是利用這點,誤導了他。
「不過關於這些行動,有出現一些謠言。是由秋牡國的一名情報人員所建立的。」陳先生停止轉筆。「有些人稱呼他『安哥』。」
Ng盡力不在臉部的表情上透露出資訊,不過對陳先生來說,Ng的是否有反應並不重要。
「我們無意傷害您。」陳先生改用食指,將筆頂在本子上。「若您能配合我們,當然,我們會立即釋放您。只要您將『安哥』的資訊告訴我們。」
陳先生等待著對方吐出充滿漏洞的資訊,基本訓練就是這樣,面對審問時在真實裡頭摻入虛構,要不是故意遺漏掉某些東西。然而Ng沒有按照對方所想的,依然沈默。
「無意傷害您的是我們。不過若是其他國家的話,誰也不能保證。」這次,陳先生站起對Ng說「您仔細考慮考慮」,走向門邊時,阮志德追了上去。「阮先生,有什麼問題,我們去外頭談,好嗎?」
按規定,阮志德不能全程參與剛才的審問,可是陳先生卻放行了,還願意跟阮志德單獨談話。
兩人走到醫院中央的庭院,不過陳先生沒有停下腳步的意願。
「為什麼他都不記得我了?」阮志德問:「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嘛⋯⋯可以合理懷疑黃先生服用了一款,能讓人失去記憶的藥。」陳先生回答。可是按他所知『安哥』對這款藥物極為反感。「我們的成員的確在您飯店房間的床底下,找出這款藥物。」
「他為什麼會吃這種藥?跟你說的『安哥』有關嗎?『安哥』是什麼人?」
「誰也不是。」陳先生看了一眼錶。「阮先生,您該回去陪您的朋友了,或許多陪伴您的朋友,能幫助他找回記憶。失陪。」
陳先生踏步離開,刻意繞了一點路才招到一台計程車,回到自己用假名租下的安全屋。
他還記得自己第一次見到安哥時,自己還是隻大學剛畢業的菜鳥,偶而幫忙處理些雜事罷了,而安哥已經是經驗豐富的探員了。
機票、幾本假護照、現金跟地址,以及地址的鑰匙。還有菜味的陳先生尚未清楚完整的任務內容,就立即搭上飛機執行他第一次的海外任務。在飛機的廁所裡,他簡單掃過其他本假護照,上頭的照片神似秋牡國的異議份子。
很明顯地,他必須協助安置那群異議份子。按照回程的機票時間,他只需在當地待個幾日。
下飛機後他遲了一點才出關,下班飛機抵達時,他很快地鎖定那幾個喬裝過的異議份子,將假護照交給他們,接著混在人群裡排隊出關。
安置的地點治安不錯,除了第一天有人在外頭探頭探腦外,毫無異狀。
好奇的鄰居,總會有這種人。
「我們是學術研究的參訪團。」陳先生拿出慣用的說詞。「抱歉打擾您幾日。」
不過那位鄰居似乎不打算放陳先生回屋,加上菜鳥的通病——總是抓緊所有學過的東西,連一些微不足道的事物都要套出情報。這場閒聊一下就被陳先生的生澀變成了附和,而對方在自己所提出的內容上憤慨。
明確的情緒起伏,平民聊天聊到激動時總是這樣。陳先生複習。
「簡直一代不如一代。」最後鄰居粗暴的總結。
陳先生掏出根菸送給對方,作為友善的意味。
幾日後,按照機票上的日期,他回到南薊雉。剛下飛機,他立刻接到消息,那些異議份子全被人殺害,兇手在桌上留了一根菸,像是在嘲笑一樣。
從此之後的十年,陳先生不斷搜集那男人的資訊,查到那男人是秋牡國的高階探員。為了這男人,自己也不斷地往高層爬。不過在七年多前,一場秋牡國內部的整肅後,那男人的訊息忽然全斷了,陳先生焦躁到一有空閒就反覆地翻閱之前蒐集到的卷宗,這兩三年間,條月國傳出有那男人的蹤跡,他還不敢妄下判斷。直到這幾個月,在條月國出現了幾個手法與那男人相似的拙劣模仿者。
他接著更深入的調查,發現到有位自稱「安哥」的人。
ns 15.158.61.20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