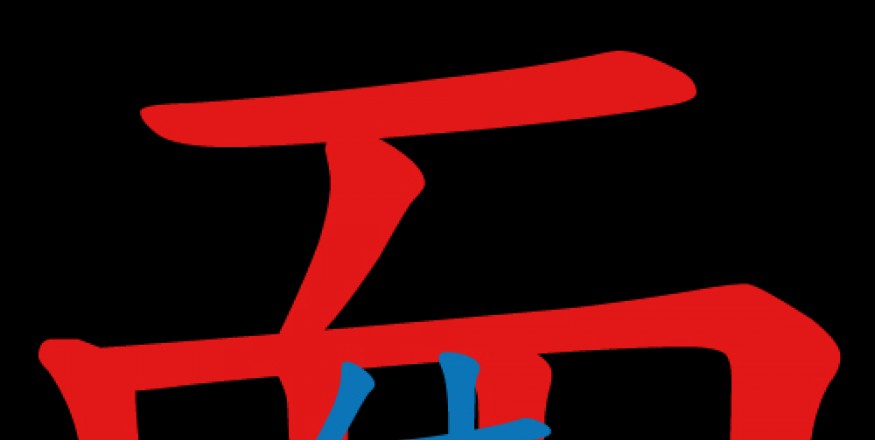第四回:桃源鄉
長孫讓察覺了此處三人正在閒聊,便留著那色目人於原處,自個兒來到了三人身旁,玩笑道:「哈哈,杜兄腳步那般輕,莫不是曾為殺手吧?」
杜承生聽言,話鋒一轉,邪笑道:「殺手?如此說倒也是沒什麼不對,你與承生皆是殺人無數的殺手,手上皆已滿是血腥,披了層『俠客』之皮作遮羞布罷了。」
長孫讓聽言,還以為這玩笑讓臭嘴邪拳火大了,便道:「杜兄,方才的玩笑似是過火了些,對不住。」杜承生又道:「不,承生並未因長孫少俠之言而惱火,就是想起了些不快過往,口氣便差了。」
長孫讓這些倒真看不清這臭嘴邪拳在想些什麼了,師父總說其下手兇殘,他亦是親眼見識過他那殘暴一面,如今一言倒似是幾分佛家慈悲為懷的味道在,若不是這男人在扯謊,就是他亦是個自相矛盾之人。
杜承生苦笑道:「三位皆是武林世家出身,自小所受教育便是碰上惡徒就要斬於刀劍之下,事後亦不覺愧疚,但承生不是,承生不過就是想當個普通百姓,卻給命運逼入絕境,不得不為俠。就如這『桃源門』一般,承生未曾欲開宗立派,不過就是找個地方安置我所救卻又無處可去之人罷了。我授他們武功亦是只為令他們得以自保,但武林中人卻不這麼想。」
魯仲恆聽言,諷道:「對對,你最慈悲了,說得我們自小就給訓練成殺人魔王似的,你不也十五歲就受丐幫長老洪慶賞識就成了──」話未道完,魯仲恆就給杜承生的表情給嚇傻,話語硬生生給截成兩段,當他提及洪慶二字時,那杜承生的表情便變得無比猙獰,令他無法置信如此清秀之人竟可有如此恐怖之神情,縱然這表情一閃而過,卻又令三人都留下深刻印象。這下他三人皆知,那洪慶怕是與杜承生有什麼天大的恩怨。
杜承生強撐面無表情道:「關於丐幫長老傳藝那事,自然是假的,你當江湖傳言可信多少?」杜承生呼了口氣,又道:「還有,望幾位在承生面前莫提那姓洪的那畜生不如的敗類,那廝承生聽了便來氣。亦莫要追問此事,亦莫將此事向他人提起。」
三人皆明白,杜承生與那洪慶怕是有血海深仇,才會將他罵得如此難聽,可他又叫他們莫要道出去,似是為避免事情鬧大,長孫讓長年遊歷江湖,自是聽得出杜承生是滿腹冤屈,他本著一片俠義心腸,便道:「讓雖聞丐幫一向忠肝義膽,但幫中仍有些許下作之輩。讓欠杜兄一命,若有冤屈,不妨道來聽聽,屆時令讓自當鼎力相助。」
那李義亦是道:「報父仇之恩,我李義亦不會忘,就給義助門主您一臂之力吧!」
杜承生聽言,便笑道:「你們若是中原武林的各大派的掌門人,你們會信承生這毛頭小子,還是那號稱忠肝義膽、聲大勢大的丐幫?他們便是真信了承生,怕是亦將不敢得罪丐幫而佯作不信,丐幫幫眾超出千萬餘人,乃中原第一大幫,中原武林各派都得怕他們。再說,有必要因一個敗類牽扯到整個丐幫嗎?沒有必要,代價過大了,承生亦不想見桃源村的村民們捲入江湖的血腥鬥爭當中。」
長孫讓嘆息道:「難不成就給那惡徒一條活路?」
杜承生對此,只是輕搖其首。
而那魯仲恆瞧著這一切,若有所思,欲轉移話題道:「呸呸呸,別講這般惱人的話題好了嗎?人家糞門就是閉著了,你倆卻這般不識趣欲以玉莖去肏人屁股!好不知恥啊!」
聞言,杜承生便噗嗤的笑了出來,長孫讓便道:「阿恆!對人家門主別講些汙言穢語!趕緊向人家道歉!」魯仲恆卻「哼」了一聲,又道:「我可沒對他說汙言穢語,我是對你們說汙言穢語啊!」,長孫讓聽言搖首道:「杜兄,阿恆他年少不懂事,說話無禮了些,還望您見諒。」
聽見這般汙言穢語,杜承生倒是樂的很,誰叫魯仲恆把他欲言之事全都道出了?笑道:「呵,沒什麼,魯兄真乃性情中人,承生記住了。有我杜承生一句話,我保證桃源村日後都歡迎魯兄前來作客!」
「臭小子,你又在胡說些什麼!」
那任劍霄從屋內步出,想來他於褒禪紫霞功相助之下,在屋內亦能將屋外之言聽得很是清楚,至少可聽清自己徒弟之穢語,還能走出來對他大罵幾聲。
魯仲恆道:「仗義、自愛、重道、清友,我又犯了哪條啦?褒禪派何時門規裡多了個『不許說髒話』啦!」
任劍霄便道:「臭小子,你怎麼還是如此不受教?這張嘴再不改改,總有日會鑄下大錯,像是你方才你叫你師妹肥婆,她身負重傷,你那二字可差點把她給氣死!」
魯仲恆一聽便是理虧了,搔面問道:「她在我離開後沒出事罷?」任劍霄笑道:「沒事,你擔心小師妹啊?」,魯仲恆知曉師妹無事,轉頭便道:「哼,誰擔心那廝。她本就胖,我道她肥婆又有什麼了不得的。」
任劍霄聽言,也只是呵呵笑,心想這弟子真是不坦率,道:「那麼師父便先回去了,留夏荷一人在宮觀內也很是不便。」
長孫讓見師父已從屋內出來,也走近道:「師父,夜已深了,放姬姑娘在家的確不便,徒兒也一起回去。」任劍霄搖首道:「不必,夜已深,為師一人回去便可,你們倆還有師妹要顧。門主,任某徒弟受了內傷,今日可否讓她在此歇息一宿?」
杜承生頷首道:「這自然是沒問題。」
魯仲恆此時卻是道:「我也要一起回去!姬姑娘在一個人留在那不大好,總需要人照顧。」任劍霄道:「有老黃在,怕什麼?」魯仲恆又道:「可是──」
任劍霄原是想讓魯仲恆留下和夜雨榴弄好關係,但一想,方才那般亂點鴛鴦譜已讓自個徒兒反感,他雖知二徒一向口硬心熱,卻又難以忽略他有時是直話直說,說不準他是真討厭這師妹,才欲速速離去,便嘆道:「罷了,你隨師父一同回去罷。」
魯仲恆聽言,面露喜色,回頭便道:「那師兄、少掌門、還有村長,仲恆先走一步啦。」那村長二字聽得杜承生眉開眼笑,想來江湖人士總忘了他不過就想當個村長罷了,而李義本是對他那般汙言穢語有些窩火,卻見人家門主都沒意見,亦不介懷笑道:「魯兄,聽聞你刀法不差,雖是今日因故未能帶刀,有朝一日我倆人定要切磋比劃個兩下。」
魯仲恆自滿道:「哼!才不用比劃,想當然一定是我會贏!」李義聽言笑道:「那我便期待那日到來罷。」長孫讓也道:「師父、阿恆,天色已暗,路上小心。」
任劍霄笑道:「讓兒,你傷才好不久,也早點歇息罷,我倆明日再會了。」語畢,魯仲恆和任劍霄便轉身離去。
※
夜雨榴照著師父所言打坐調息,她已獲褒禪心法真傳,上中下三處丹田處皆湧出一股真氣,她督脈受損,但師父已傳她運氣之法,她便由上丹田髓海之處導氣入脈,真氣一入便滋潤督脈各處,她驚覺運氣時從頭頂沿背脊運至尻尾間竟是暢通無阻,其百會至腰俞已然打通,而由唇下齦交至頭頂百會亦是如此。
想來夏荷雖是糊里糊塗差點要了她的命,卻如夏荷姊姊所願,甚至有過之而不及,誤打誤撞的打通了她大半督脈,唯長強一穴未通,平白得了他人一、二年才可得之成果,而長強離下丹田會陰處頗近,若是集上下丹田兩道氣,數日甚至數個時辰內便可打通。因禍得福的她不知該哭還是該笑,那般要命之事,她可不願再來一次。
此時,那長孫讓穿門而入,道:「小師妹,阿恆和師父都先回去了,讓妳今日在此借住一宿。」長孫讓一瞧師妹正在練功,便道:「妳身上帶傷,調息完畢後,早些歇息罷。」
可夜雨榴卻神采奕奕笑道:「大師兄,讓您擔心了,雨榴現在挺好的,因禍得福,回去後定要謝謝夏荷姊姊。」長孫讓聽言,問道:「怎麼說法?姬姑娘她做了什麼?」,雨榴笑答:「師父方才來傳了我褒禪心法,雨榴便發覺督脈竟是僅剩一穴未通。」
長孫讓大喜道:「竟有這種事?」他暗自思量,想道自己就算常給師父誇天資聰穎,亦是花上半年之久才通督脈,今日這小師妹給夏荷這般胡亂點了下,沒死沒廢就已是萬幸,竟還因此督脈只剩一穴未通?真不知是幾輩子修來的福份。但他又暗自斥責自己都忘了前些日子她才遭逢巨變,運氣究竟哪裡好?
長孫讓便作為一個師兄建言道:「師妹好福氣,可督脈快通了,卻不意味未有了足以維持其通暢之真氣,若不勤加修練,待以時日也會閉合。」長孫讓非心胸狹隘之人,見師妹武功因意外而有所進展,自然是替她高興的。
雨榴苦笑道:「謝謝師兄建言。」語畢,長孫讓笑著便步出門外,留下夜雨榴一人在屋內。這夜裡,夜雨榴一以真氣滋潤督脈療傷,二又試著運氣通長強穴,儘管師兄師父都囑咐她早日歇息,但畢竟她才方知自身督脈已通,興奮的很,哪還睡得著覺?
於是她直至破曉時都未能入眠,一夜之間,督脈以然全通。
※
清晨,兩名男子躡手躡腳走進屋內,當中一人是那名喚作羅傑的色目人,另一名男子見夜雨榴打坐著便睡了,便從旁悄悄地拉起被褥,覆於其身,道:「瞧她那樣子,八成是練功練累了便睡了。」
羅傑面無表情,冷不防的道:「你喜歡她。」惹來男子一臉詫異,笑道:「怎麼可能?我也不過救過她一次,點頭之交罷了。再說老傑,你也知我都四十了,對她真那般想,可不成戀童癖了?」,羅傑又道:「我活過一百四十年了,瞧得出來你小子迷上她了。且你瞧起來不過二十,真與你年齡相仿的女性對你有意思不也都了戀童癖了?年輕便要把握好機會。」
男子拉著羅傑出屋外,往村中廣場步去,避免二人交談之聲吵醒夜雨榴,又苦笑道:「退百步說,便是我當真給她迷住了而我未能察覺,現下她亦不是我能相處的來的,至少那般女子仍不合我眼。」,羅傑聽言又問道:「那哪樣的姑娘才能入你的眼啊?」
男子搖首笑道:「就算現下我與她結為連理了,她也不過成了個小鳥依人的無聊女子,過幾年便得更加無聊的相夫教子。女子啊,若握在掌心裡折騰自己亦是折騰她,小鳥就不該依人,而是該飛!」
羅傑仍舊面無表情,又挖苦道:「飛出你掌心了便是人家的了,你這般東挑西揀的,可真白生了張俊臉,難怪都四十了還是個處。」
男子挖苦回去道:「我可不像你,練了個奇功。讓自己成了個不老又斷子絕孫的老妖怪,不怕將人家肚子弄大,才能那般沒節操的遇到哪個漂亮姑娘都能抱上床。」
羅傑又道:「中原女子保守的很,抱上床可沒這般容易。目前在桃源村也就兩人。」男子聽言,差點兒沒暈過去,罵道:「你說什麼?你竟已出手了?你這老色鬼就不能離我桃源村的姑娘家們遠點?你也知中原保守,她們給你抱上床,你是爽過了,但她們將來便很難再出嫁。」羅傑又道:「你倒不用擔心,我可不如某人是戀童癖,對少女可沒興趣,她們倆都已經嫁人了。」
男子搖頭嘆息道:「承生讓你來,不過是要你教村人劍法,可沒料想到你會給村中男丁戴綠帽子!」羅傑拍其肩,笑道:「沒關係,村長。一來我們是你情我願;二來是他們可都給矇在鼓底,絲毫不會起紛爭。」
杜承生對羅傑可說是啞然無語。
恰好那長孫讓從另一借宿屋中步出,一面伸展筋骨,一面步向二人,長孫讓仍是睡眼惺忪,就算有褒禪紫霞功相助,亦是分毫沒聽清方才二人在談論些什麼,否則以他那性子,怕就要指著羅傑鼻子破口大罵了。
長孫讓招呼道:「門主、前輩,兩位早。兩位起的真早。」
羅傑道:「年輕人,今早便要回你們那了?」,長孫讓道:「和前輩一番切磋,晚輩受益良多,但今日我倆真的得回褒禪派了,師妹還有課得學呢。」
杜承生道:「你師妹的話,她睡著呢,練功練到睡著了。」聽言,羅傑又挖苦道:「而某人瞧她睡臉可愛,怕她涼著還替她蓋被褥呢!」杜承生對那劍客斜眼一瞪,但這嚇不了功夫遠高過他的羅傑。見此杜承生又嘆道:「小爺當真該向你學學這門面無表情挖苦人的功夫,免得以後都要江湖上不稱小爺我臭嘴邪拳,倒稱你這廝臭嘴邪劍了。」
長孫讓又道:「師妹竟是這般躁進?」杜承生笑道:「怪不了她,我初練內功之時亦是興奮不已,一夜未眠。」此時,長孫讓憶起當初杜承生戰郝諒光所施展的那內功,在發勁之時發出火銃般聲響,與褒禪派內功心法似有不小差異,便好奇問道:「杜兄的內功似與我褒禪源自道家之心法差異甚大,甚至可說那般心法讓聞所未聞,可否借問師承何處?」
杜承生似是考量了下,便道:「也罷,見長孫兄是可信之人,承生若講,還請長孫兄未給外人道。」長孫讓問道:「什麼事真這麼見不得人?若是真是如此的話。」杜承生笑道:「沒什麼,你亦曾聞承生所學拳法來自西域罷?那便是由名色目女子親授。你亦明白,前朝雖已給推翻了,至今卻仍不少人仍對色目人心懷仇怨,而亦仍有些迂腐之徒道人家女子不應習武,我不願見那些人聽了這些便說三道四。」
羅傑一個挑眉道:「那我便先迴避一回兒。」說罷,便以雷速消失在二人眼前,似是出村口了。
長孫讓聽言,笑道:「杜兄放心,我不會與人亂道。再者,女子習武又有何錯?」
杜承生聽言,便解釋道:「承生心法、拳法皆師承樂華,為法蘭西人士。我倆並不以師徒相稱,而師父心法僅傳口訣,因為些緣故沒能做給承生瞧,剩下我自悟而出。勉強算來的話,屬兵家心法,通脈調息無助此套內功長進,唯有反覆對打,抑或是鍛鍊筋肉方可增強內力。」
長孫讓驚道:「厲害!那不近乎等於無師自通內功心法了?杜兄果真如江湖傳言般是奇才!讓可真是自嘆不如。」語畢,便面色黯然,暗忖:「我從小跟著師父學藝是為了什麼?人家十五歲學武,十六歲就自創獨門武功,十七歲就開宗立派,弱冠之年就足以三招擊殺郝郎光這等高手?庸庸碌碌二十多年,不過就是個庸才,學了個屁。」長孫讓想到這些,信心便是全無。
然而,杜承生似是已察覺長孫讓面色有異,便搖首道:「若論奇才,我倆皆是,在承生看來,長孫兄與承生武學資質差異並不大。」
長孫讓聽言,想道這臭嘴邪拳倒也不是這般臭嘴,還會安慰人呢,自從敗給郝諒光、又睹杜承生三招擊殺他之後,他信心便受到重創,至今仍處低潮,可說近來唯一令他開心之事,便是那師妹武功有所進展了。
杜承生又道:「但你知我倆最大差距於何處嗎?那便是見識。」長孫讓苦笑道:「讓闖蕩江湖亦有七年之久,什麼怪事沒見過?杜兄便別安慰讓了。」杜承生聽言,竟是吼道:「你這傻子!別妄自菲薄!」有如一名長輩對小輩訓話般,這下長孫讓才知他並非是在安慰自己。杜承生五指併攏、朝旁空刺,問道:「這是什麼?」
長孫讓愣道:「承生截脈手?」杜承生卻搖首道:「錯,此乃『貫手』,傳自琉球島的拳法『手』中的招式。你聽過嗎?」長孫讓聽言,一愣又道:「聞所未聞。」杜承生又問:「那羅傑手中之劍與你手中原武林之劍有數處顯著差別,你知是何處嗎?」長孫讓又愣道:「似乎重心較靠後、因此劍術比中原之劍靈活的多、但劍勁亦小的多。且那對護手長,用于架格,與中原劍護手僅為避手滑至劍刃處不同,因此與中原劍的防守之法徹底不同,那種劍衍生出之劍法相較中原劍法下更善於防守。」
杜承生笑道:「你瞧,你這不是見到了嗎?先前你知道這些嗎?」長孫讓苦笑道:「讓昨日才與羅傑前輩見面,怎可能知道?」杜承生又道:「所以你現下知了彼此之別,何不取長補短?」長孫讓問道:「杜兄是說──偷師?可褒禪派嚴令不許偷師他派武功。」
杜承生道:「此言差矣,現存世上哪家套路未曾擷取他家所長?你硬要說此為偷師,我亦沒辦法。小爺若未曾過師貫手、未曾師過瑪迦拳,那便不會有承生截脈手。褒禪派劍法固然厲害,但畢竟也不過是一人之智慧,那位前輩找出了其最佳套路,但不見得那套路適合你,你的最佳套路亦尚未尋出。世界之大,無奇不有,功夫種類亦是千奇百怪,中原比起此世不過是彈丸之地。若要尋出最佳套路,除了多增見聞,海納百川外別無他法,總是給前人智慧綁著,是走不出自己的路的。對祖傳之物,莫要讓!而要進!這便是青出於藍唯一之法!」
長孫讓苦笑道:「讓怎麼覺得杜兄你把我當弟子在訓了?」
杜承生亦是苦笑道:「唯有這般做,你才不會真把自己當庸才了。」
長孫讓道:「伊杜兄之言,便是要讓自悟一套劍法?但就是怕讓才疏學淺,創出個四不像的破爛玩意。」杜承生此時卻反問:「那郝諒光自悟的雙風快刀厲害嗎?你想他自悟的雙風快刀開始便如此厲害嗎?就是只自悟幾招亦沒關係,見識越多悟得自然更多,承生截脈手草創之時僅有三式,現下已有十式,而承生亦正在多鑽研另外兩式。」
長孫讓恍然,抱拳道:「循序漸進?讓明白了,多謝杜兄建言。」
夜雨榴笑道:「嘻嘻,竟是給門主他訓了一頓呢。」她竟是不知何時就已來到村中廣場,杜承生問道:「姑娘何時便在旁聽著了?」夜雨榴道:「從『我倆差距最大之處』那兒便聽著了,杜公子年紀輕輕,說起話來倒像是名宗師,連在旁聽著的雨榴亦有種茅塞頓開之感,令人想起在村中受夫子教誨之時呢。」
杜承生笑道:「姑娘謬讚了,宗師二字還真擔當不起啊,更何況桃源谷還有比承生更加厲害之人,羅傑那條老色狗才算得上真正宗師。」
長孫讓聽言,心底一樂,想道那杜承生怎道自家客人為老色狗了,那位前輩武功高強,但人品他倒不曉得如何,說不準還真如他所言是條老色狗。
長孫讓見師妹已醒,且儀容皆已理好:「既然師妹已醒,我即刻倆便回褒禪派罷,免得師父他擔心了。杜兄,告辭了。師妹,走了。」夜雨榴聽言頷首道:「門主,後會有期。」
杜承生卻又道:「二位且慢,既然來了,我便送些東西。」
※
在兩人離去之前,杜承生讓村人送了他倆兩塊以竹葉包覆之塊狀物,發出淡淡香味,那杜承生將此物喚作「肥皂」,乃是參照西域大食人之法所造之豬胰子,據其所言,兩者材料與製法雖不大同,但成品差異不大,是他一時興起玩起的產物,但他又在當中摻入些香料,使之聞起來有股淡淡清香,便稱之為「香皂」了。
夜雨榴未習過輕功,長孫讓為顧著師妹,刻意放慢腳步,其結果便是二人過了許久方至褒禪派,兩人達宮觀之前時,黃昏以至。那姬夏荷早已在宮觀前,坐於一張木椅上,等候已久,一見二人歸來,便是要起身。雨榴眼力甚佳,遠遠便已瞧見夏荷竟是紅了眼眶。
夜雨榴見狀便道:「姊姊莫急。」奔至身旁,正要伸手攙扶,那長孫讓卻已先一步從後拉住她,道:「姬姑娘小心。」
夏荷淚眼汪汪道:「長孫大哥、雨榴妹妹,我──」長孫讓笑道:「先坐下罷,坐下再說。」夏荷聽言便坐回原位,道:「雨榴妹妹,對不住,夏荷好心辦了壞事,差點兒害了妳性命。」
夜雨榴卻道:「沒事、沒事,差點兒便是沒有。」
魯仲恆此時從宮觀內走出,似是今日之修行已然完畢,道:「妳瞧!母猩猩都說她已沒事了,姬姑娘還擔心什麼呢?」夜雨榴聽了差點破口大罵,卻又想道夏荷現下難受,若她如平時一般亂吼亂叫,就怕嚇著人家。
長孫讓斥責道:「師弟,你消停些,姬姑娘人在這呢。」
魯仲恆聽言亦知理虧,搔了搔面頰,改口道:「既然師妹都說她已沒事,那姬姑娘還這般糾結作什?」夏荷道:「是、是嗎?」
長孫讓笑道:「姬姑娘莫需過於介懷,小師妹此次雖逢大難。卻也因禍得福,武功有所進展。」
魯仲恆聽言一驚,伸手朝雨榴頭頂摸了兩下,雨榴給這嚇著了,驚叫道:「什、你在做什麼啊?」那魯仲恆不理其言,注氣為確認其修為進展。夜雨榴生於偏鄉,衛夫子村人數稀少,與她年齡相仿之男子亦不多,哪怕是阿成也沒碰過她身子。雖只是頭頂,給年齡相仿男性碰觸身體這可是頭一遭。若只是如此倒也還沒什麼,她卻因此想起師父昨晚之言,說是那阿恆抱著她一路從褒禪派至桃源谷,想到此處,她竟又一次羞紅滿面,心跳加速。
魯仲恆縮回手,噘嘴道:「哼!不賴嘛,不過是個肥婆督脈竟已全通了!看來肥亦是有好處,給這般一弄沒死反通了督脈,肯定是那些肥油護著身子才讓妳撿回條命。」
雨榴現下是又羞又怒,不知所措,半個字都吐不出來,那長孫讓見此,一把捉住魯仲恆手腕,怒道:「師弟!男女授受不親,師妹的身子豈是你能這般亂碰的!我等幾個大男人在褒禪派生活多年,但你亦不該將師妹是女子這事給忘了啊!」
魯仲恆又道:「我、我才沒忘!只是我這個做師兄的總要確認下師妹的功夫進展,碰頭一下有什麼?又不是碰胸碰手碰腳碰腰的!」夜雨榴聽言,罵道:「你、你若真碰了你說的那些地方,姑奶奶便一巴掌朝你臉招呼過去!」
魯仲恆見狀,竟是笑道:「姬姑娘妳瞧,師妹她那臉紅得像猴子屁股似的,氣血旺盛的很,精神的可朝我臉上呼巴掌呢!肯定沒事!妳莫要擔心啦!」 夏荷聽言,先是愣了下,隨後便咯咯笑了起來。魯仲恆問道:「怎麼忽然笑起來啦?」夏荷笑道:「沒什麼,只不過是覺得阿恆你真是魯鈍啊!」魯仲恆聽言,仍是不明白夏荷再說些什麼,一頭霧水。
夜雨榴見怎麼夏荷姊姊亦是副覺得她對那野牛肏的師兄生情似的,便羞得再也待不下去道:「雨、雨榴先去找師父了!師父他需要知道雨榴現下平安無事!」說罷,她便穿過二人,走入觀內。
魯仲恆在背後道:「師父他人不在觀內,他去棧道那練輕功去了!」
他如此叫道,想見那夜雨榴亦是聽到了,卻未有回應。
※註:
註一:本文所撰寫之修練內功之法全是在查了中醫後搬出的名詞的扯淡,請不要相信本文內除了經脈和穴位位置以外的任何東西。總之就是:中醫是中醫,氣功是氣功,幻想是幻想。
另外上中下丹田之處各種醫書和氣功都有不同的見解,這部故事是參考《東醫寶鑒》所寫,設定成上丹田為腦、中丹田為心、下丹田為會陰。會陰於任督二脈相交處,而這故事又提到了任督二脈構成的小周天,將之寫成下丹田恰好可以。不過丹田位置或許在之後的描寫中會依照不同心法而改變位置,例如西域的內功心法怎麼想也不可能和小周天有關。
註二:胰子,明清時期將豬胰臟和草木灰混成的洗潔用品,色澤多呈黑,從化學成分上看來看現代香皂其實沒太大差別。
ns 15.158.61.20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