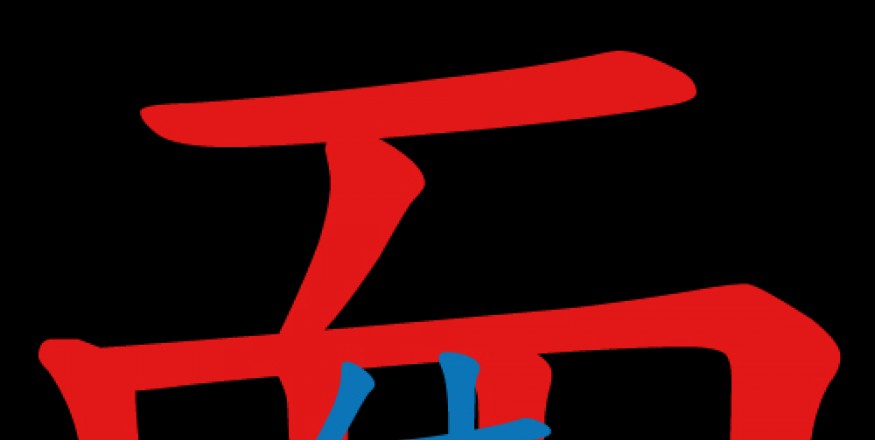第十二回:於壽宴之前……
當褒禪派三徒正要與唐門的三人道別之時,那衛蕸就似給她的少主和師父拋下,就似是要硬將衛蕸塞給褒禪三徒照顧似的,褒禪派的兩名男子紛紛表示一頭霧水,夜雨榴雖知他們在打什麼算盤,卻也不願錯過與衛蕸敘舊的機會。
但夜雨榴可忍不住,將衛蕸拉到一旁細聲問道:「蕸姊妳莫不是對二師兄他──」見其友人亦識穿了其情意,衛蕸只得微微頷首,苦笑道:「雨榴,妳莫要擔心,我不過單相思罷了,不會和妳搶妳男人。我雖年已十八,但武林中人普遍較為晚婚,大不了二十多歲後再找個好男人吧。」
夜雨榴聽言,知那衛蕸亦是瞧出她對魯仲恆之心思,卻是怒道:「蕸姊妳怎麼這般道?二師兄尚未成親,他才不是『誰的』男人!來日他要與誰成婚都是由他所選。」衛蕸聽言,便道:「可是,若真與雨榴妳爭,怕是到時我倆都會鬧得不愉快的。」
雨榴聽言,更是不悅道:「難不成蕸姊妳認為我是小雞肚腸的女子?妳說武林中人晚婚,大不了二十多歲後再找個男人。此話雨榴可以當場奉還於妳,便是到時二師兄真不選雨榴而選了蕸姊,雨榴雖不敢說能誠心為妳祝福,卻有把握絕不會因此後悔。」
瞧見兩位女子在旁聊天,長孫讓雖是有興趣明白她倆在談些什麼,卻也顧得禮教刻意收功,不聽二人之交談,魯仲恆則是對此事沒有興趣。也因此二位男子都不清楚她倆的話題就是魯仲恆,還聊得挺熱烈。
衛蕸聽言,驚訝問道:「當真如此?雨榴妳當真不會後悔?」夜雨榴瞧衛蕸面色紅暈,似是又要做出什麼出格之事,遲疑了下,卻還是頷首了。而這一頷首,便令她馬上後悔。那衛蕸先是面露笑容,卻又噘嘴道:「這可是雨榴妳答應的啊。」
說罷,她便遁離夜雨榴身旁,當著三人的面施展唐門輕功「唐嫂罵街步」,這名稱雖俗,卻也是無愧是一門絕活,劈里啪啦的,身子左扭右擺繞至魯仲恆身旁。她左臂一搭,面頰一靠,便貼上了魯仲恆的右臂,面部亦貼上其上臂,魯仲恆一個驚慌,喊道:「妳、妳做什麼?」欲揮臂甩開衛蕸,卻未想到那衛蕸又貼了上來,這次連那對碩大柔軟之物亦貼上了魯仲恆的身子,弄得他滿面通紅。瞧得夜雨榴見此驚叫道:「蕸、蕸姊妳!妳做什麼啊!」
那衛蕸亦是鼓起了很大勇氣,現下她的面色可比魯仲恆紅得多,心亦是猛跳個不停,連魯仲恆都能感到其心跳之快,但衛蕸仍強忍羞意,道::「魯公子,我倆一同玩去,別理你倆師兄和師妹好不?」
那魯仲恆的審美觀一向喜清瘦美人,衛蕸這類胸前豐滿之女子對他來說往往只是「肥婆」或是「鄉野蠻婦」,可這鄉野蠻婦遠看不怎樣,身子貼上卻又是另一回事,魯仲恆未想到不過是肉團貼上就令其腦海一片空白,他現在亦明白,為何當初杜承生會對這鄉野蠻婦的舉動頗為樂意。
現下他竟不禁在心底呼喊──
──鄉野蠻婦可真棒啊!
但有鑑於上次見過衛蕸欲勾搭杜承生,魯仲恆以為那衛蕸只是在開他玩笑,他便雙手一推,跳離衛蕸身邊,道:「妳、妳這花癡別、別拿我尋開心啊!多珍惜自己一點!」
可衛蕸此次可不似先前那般,對杜承生那次僅是為了應付門中長輩的囉唆,對魯仲恆那可是發自真心,便是魯仲恆將其推開也阻不了其決心,她盯著魯仲恆的雙目道:「魯公子怎麼這般道?我可是真心誠意,不是對誰人都能這般做的!那日長安地窖內,魯公子為救人出手之英姿,令蕸深受震撼,蕸便是從那時心繫魯公子。今日再相見,本是打算忍著不做些出格之舉,可是、可是──」衛蕸這般激烈的追求魯仲恆,可她可並非全為了自己,要激雨榴的用意還多一點,要講至關鍵之處便隨即語滯。
魯仲恆見其滿面通紅,欲言又止,便問道:「可是什麼?妳可別像先前對村長那般要帶我去妳房裡什麼的!這事我可不跟著幹!」衛蕸聽言,臉變得更紅了,瞪大雙眼道:「怎麼會?我不過是想請魯公子和我共遊這洛陽罷了!啊!恰巧魯公子方才說了答應我什麼事都行!讓我倆共遊這城又有何不可!」不論男女,欲認真地追求一人,便不會輕意道出要對方來自己房內這話來,那衛蕸對杜承生和仲恆的差別就在此處。
魯仲恆聽言,本是鬆了口氣,可此時夜雨榴在旁終於瞧不下去,伸手便拉開衛蕸,驚叫道:「等會兒等會兒等會兒!蕸姊妳也太賊了!」衛蕸見雨榴這下真慌了,便又笑道:「此乃把握天賜良機,雨榴妳學著點。」說罷,便伸手拉走魯仲恆,帶他離開市集,魯仲恆雖說與衛蕸不熟識,卻也不討厭對方,未有反抗、面露尷尬的隨著衛蕸走去。
見此,夜雨榴叫道:「蕸、蕸蕸姊!妳這花癡!恬不知恥!」語畢,那橙紅衣裳之少女亦跟著她的意中人與好友一同走去,留下在旁看完這場鬧劇的長孫讓一人,對此,長孫讓淡然道:「阿恆,真受歡迎吶。」未有阻止他三人,心中已然放棄,便決定一個人找間酒樓,喝悶酒去。
※
黃昏時分,洛陽巷內,雨榴與衛蕸正在爭論。只因魯仲恆消失,魯仲恆輕功卓越,勝過雨榴與衛蕸二人,她倆人一不留神就藉機逃跑了,衛蕸此時才發覺把魯公子逼得太緊了。但後悔也來不及,那衛蕸在唐門內習過一些簡單的追跡之法,於是二人決定沿著魯仲恆所留之蹤跡前行。
而那魯仲恆為逃離二人跑至北方河邊之處,以弄得滿身大汗,氣喘吁吁,他是名年輕男子,倒也不是討厭衛蕸對自己那般捉弄自己,可那衛蕸屢次與其多次肢體接觸,使其慾火猛升,氣血不聽使喚地朝下身湧去。若是再待在那二人身邊,他怕自己再也把持不住,就要鑄下大錯,只好逮到機會便拔腿就跑,這時他知曉為何自己練不成褒禪紫霞功了,便是因這等淫慾未除啊。
當他好不容易逃至北河流之旁時,那渾身臭汗令他再也忍不住,他見四下無人,只有些草堆,鬆了口氣,他便找了個河邊人家不要的木桶子,蛻去衣褲,杓了水便朝自個兒身上沖,用以沐浴,雖說身上未帶豬胰子,他也只好將就點。四月之時,氣溫已然回暖,河水涼得很,使他舒暢不少,但冰涼河水似乎澆不熄他體內慾火,其下身之物仍舊堅如玉石,令他頗為困擾,倘若這模樣在方才給那兩位姑娘察覺了,那肯定是件害臊之事。他對此自言自語道:「魯仲恆啊魯仲恆,你當真是個禽獸不如的小淫鬼。」
那魯仲恆是穿衣顯瘦的男子,他自七歲時便開始習武,經多年苦練,將其其身形乃是壯而不碩、肌肉結實卻不大,他江湖經驗雖少,卻仍多過於夜雨榴,當日長安可不是他初次以命相搏,因而魯仲恆的身子上仍有些大小疤痕。
他正享受河水清涼,亦不似其師兄習得褒禪紫霞功,未有高明耳力,絲毫未察覺方才拉著他走的那兩位女子已沿著其足跡跟上了他。夜雨榴與衛蕸二人,竟是躲於樹叢之間偷窺心儀男子之裸體,她倆人知此事傷風敗俗,卻又止不住好奇。
夜雨榴見他背部結實,壯如牛,心已是一陣躁動,她仍記得她曾罵過魯仲恆是野牛肏出來的。今日有幸見到他赤身裸體,竟是真有些懷疑這二師兄是否當真雙親當中有一是牛了。衛蕸如雨榴一般屏息瞧著魯仲恆,不敢多作聲響,就怕給人家發現了,罵她倆是蕩婦。
當魯仲恆轉過身來,夜、衛二人都覺得心跳欲停,從上看下去,瞧見他鎖骨如筆墨般斜斜畫下,就似在誘惑二人。雨榴嚥了口口水,繼續向下瞧,目光掃過帶毛的乳首;再朝下掃過排列整齊分明的腹肌;接著,再朝下──
衛蕸此時細聲道:「雨榴、雨榴,你還記得黃家有段時間養了頭公牛嗎?魯公子他那的樣子簡直是──」
夜雨榴和衛蕸乃是舊識了,她在衛蕸前說話可不會顧面子,便細聲回道:「嗯!當真,那可是如牛一般啊!」衛蕸聽言,亦頷首表示贊同,兩位女子雖在這保守的世道,男子之陽物她倆可不至於見都未見過,可注滿氣血的她倆可就沒那麼常見了。夜雨榴憶起那日長安見內淫賊的玩意兒,她那時感到噁心,而此時見到二師兄的玩意兒,她卻覺得興奮不已。
衛蕸又道:「雨榴雨榴,我們門內有一名師姐改嫁多次,經驗豐富,她常道男子的那話兒『長不如粗、粗不如硬』。」眼力驚人的雨榴,此時竟道:「長四吋半,粗一吋七分算大算小?」去年任劍霄是因其眼力優秀才收她入門,若是那華劍大俠知她將眼力用於此種地方,說不準一口老血都要吐了出來。衛蕸聽了亦是驚道:「雨榴妳說真的?眼力真好!」
雨榴又道:「不見得,我也只是目測罷了,這距離我也沒十足把握。所以究竟算如何?」衛蕸怒道:「妳的蕸姊如何能知道啦!」雨榴瞧她那蕸姊竟是首次在她面前示弱,便打算趁勝追擊,搭著衛蕸的耳邊細聲道:「姎曾罵其野牛肏,其壯如牛陽幹豪,若與之渡花燭夜,無異同和野牛肏。」
衛蕸聽言,差點大喊出來,好在及時給雨榴掩住口,衛蕸平復情緒後,便道:「我爹教妳作詩可不是讓妳作這下流詩的!」話才說完,那魯仲恆又一次左顧右盼,似是察覺了二人藏於樹叢之中,二人見此皆是屏息,原來那魯仲恆並非是發現了二人,而是單純環顧周圍。
然而魯仲恆接下來欲行之事,更是嚇傻了二人,那魯仲恆見河水之冰涼消不了慾火,便將木桶子倒擺在地,坐於其上,又自語道:「魯仲恆你這淫賊。」因為他背對著夜雨榴,夜雨榴瞧不清那二師兄右掌,也瞧得出來他正在做些什麼,當下便驚慌失措道:「這、這莫非是手手手……」衛蕸一聽,差點沒昏過去,羞得以掌掩雙目。
幸好直到那魯仲恆沐浴完畢,穿衣離去後,都未能發現這兩位女子的蹤跡,衛蕸在中途便羞得躺平了下去,夜雨榴則是全程目睹,還毫不怕羞的問衛蕸道:「原、原來男子會噴出那麼多東西嗎?」
想當然爾,對此衛蕸再次怒道:「妳的蕸姊如何能知道啦!」
※
天色暗下後,夜雨榴和衛蕸都回到了彼此所居的客棧,對雨榴來講,可說事倒楣之事,雨榴才回到客棧前,於門外便聽見他人咆哮之聲。
「臭乞丐,我們敬你們丐幫三分,可你們欺人太甚!這是我管定了!」
「姓奕的!你道我別欺人太甚?河南大俠之壽宴乃中原武林各路英雄豪傑齊聚之地,怎能容得下夷人攪局?今日你們帶色目夷人來便是來挑事的!我丐幫若今日不將你們縹緲、桃源帶來的夷人趕出去!怕是明日河大俠都給給人道成勾結夷狄的奸人了!」
「奸你個屁!你們這幫大男人欺負個小姑娘!老娘今日就要替師妹討個公道!」女子的聲音高亢,夜雨榴推開門便給那女子給吸引住目光。客棧內,那最年長的年輕女子身後站了三名女子,四人皆身著白衣白裙、黑腰帶、紅袖筒,好似雪地之中的白兔,她們服上又多有刺繡,頗為華麗既不似漢服那般有領口、更無左襟右衽和鈕扣。夜雨榴對自小對裁縫活特別有興趣,可那四名女子所穿服飾她卻是未曾見過,覺得新奇得很。
四人從服飾上瞧去不似中原人,可若是她們換了服飾便無人能瞧出,然而當中有一人,便是換了套漢服亦能給人看出她並非中原人,她儘管是黑髮黑眼,但其五官突出,面貌與漢族人差距甚遠,瞧了便知那是名色目小姑娘,年約十五,她瑟瑟發抖,褐色捲髮給人灑上湯水,顯然那小姑娘正是那吵架的原因。
另外,夜雨榴亦是見到桃源谷的二人站在四名女子那一方。那二人便是當初與夜雨榴過招的奕悟釗和桃源谷的劍法導師羅傑‧艾立克。
而另一邊帶頭欲趕人的人,夜雨榴倒也見過,那便是那先前與魯仲恆起過衝突的黃桿丐頭夏良蔽。
奕悟釗與羅傑二人之反應頗為有趣,那羅傑絲毫不理那些丐幫弟子們叫囂,獨自一人動筷子吃桌上的料理。而奕悟釗卻很是火大,與羅傑那副事不關己的模樣全然不同。夜雨榴亦見到不論是丐幫或是桃源谷和那些白衣女子哪一方皆有其他門派弟子在旁為之掠陣。夜雨榴雖不認識那些人,卻亦能從那些人神態氣質中瞧出那些人都不是什麼好惹的,怕是每一個功夫都遠高過自己。
站在丐幫那方的,有兩名身著靛青道袍的道士,腰間之腰帶上繫著塊小小的陰陽兩儀圖,夜雨榴近乎是在瞧見同時便明白那二位男子皆是那大名鼎鼎的武當門徒。二人一高一矮,瞧上去皆是年輕,皆在二十前半,矮的外表清秀、腰間繫著兩柄棒狀之物,四面朝內凹陷,長而無刃,那乃是對鐧,江湖中使這類兵器的人並不多,是為對付刀劍所鑄之鈍器,較難取人性命;而高的那個身長五尺二寸,壯實魁梧,他身上未帶兵器,似是精於拳掌之人。
而站在另一方的,似乎是一對夫妻,女的穿著艷麗,臉上抹了些胭脂眼線,不似江湖中人,反似是大家閨秀。她雖是滿面麻子,年齡亦以至二十後半,在夜雨榴瞧來卻仍似是夏荷那般水平的絕代佳人,她坐於椅上,有著張琴置於其面前,瞧了夜雨榴一眼後,又將視線放回丐幫諸人身上。而其丈夫年紀稍輕,長相亦俊得很,他扎髮如馬尾,身著袖口頗長的袍子,在夜雨榴一踏入門內便死盯著夜雨榴瞧,便是如何俊亦瞧得她渾身不舒服。
良久,夜雨榴才問在場諸人道:「怎麼回事?師兄他們人呢?」爭執之聲暫時因夜雨榴而停下,奕悟釗才發覺當日與他有一面之緣的姑娘又與她見面了,便走至夜雨榴跟前,向她招呼道:「夜姑娘,別來無恙。」
夜雨榴對奕悟釗的印象談不上深刻,只知奕悟釗和自己同樣無什麼江湖名聲的無名小卒,便隨口加了少俠二字道:「奕少俠,您也是。」
那坐在妻子旁的馬尾青年,在原位便拉起了大嗓門道:「長孫兄他似乎有什麼煩心事,喝掛了便往樓上房內休息了。妳二師兄我倒不知道去哪了,還沒回來。」夜雨榴不記得見過這人,但對方似是知曉自己是褒禪弟子。
雨榴問道:「這位是?」
青年介紹道:「我是無天派首徒穆陽飛,和妳大師兄是老酒友了。」又指了身旁的女子,道:「這是內人風瀟瀟。」
夜雨榴聽言,而那對夫妻亦是在這河南赫赫有名的無天派首徒與次徒,並稱無天雙俠或無天俠侶。而方才她在門外聽見幾人爭吵之聲,便明白那些白衣女性皆是縹緲派弟子,她曾聽任劍霄道過他派歷史,無天與縹緲二派本為一家,名曰七典派。傳說七典派祖師為名曰玄君,乃一位受天外飛仙授予七類武功祕典的哲學家,那七典派曾有一段時間被公認為武林魔道,原因乃是強搶各地武學精要,行事作風無法無天,無天派之名亦是因此得來。有傳說當初七典派地子赫君因不齒同門作風自行出走,這一走,便遠遁西域天山自行開宗立派。
而在此次被河槭所請來的武林名門當中,唯有那縹緲派不論廣義或狹義皆稱不上中原門派,所在疆域更不為中原皇帝所管,位於西域亦力把里國,以當今朝廷的標準瞧來可說是西戎之國,連帶不少百姓們亦不待見他們,而今次丐幫會與之起摩擦也是因此緣故。縹緲派會收到請帖只因他們名聲夠響,且多行義舉,連遠居洛陽的河南大俠亦想與他們套些交情。
時過境遷,無天縹緲兩派現下均已被視作武林正道,但無天弟子可沒忘那縹緲派同源自於七典派,便是已分家百年無天派弟子亦是看在曾為同門的交情下願意為之幫腔。
夜雨榴見現下要自我介紹尷尬得很,鬧不明白眼前之爭執究竟是為何而起,貿然插手可能會把事情攪得更亂,可若撒手不管又有違她為俠初衷,便去喚來小二,讓小二借她肩上那條抹布,隨後便朝那瞧上去哭得很慘的女子走去,為之擦去頭上那些湯水。
夜雨榴瞧她一臉驚懼,又一次問她:「怎麼啦?」夏良蔽見此,嘖了一聲,卻又不願意張口罵她,縹緲派遠在天邊,桃源門則小不啦嘰,今日這舉惹惱了他們問題不大,無天派出言相助是在他意料之外,他可不想再多惹惱個中原內的名門正派。
瞧上去最年長的縹緲弟子道:「還有什麼事情?那幫臭乞丐瞧見人家女孩子好欺負,便拿著碗朝人家頭上丟!」
夏良蔽道:「龍姑娘此言差矣,夏某奉賈舵主之命辦事,我手底下的人或許粗魯了些,但此乃為武林與社稷著想。」那龍姑娘又罵道:「社你個機巴稷!那河大俠邀請的就是我們!你這臭要飯的又不是他憑什麼代他趕人?」夏良蔽聽言,額上冒汗,他曾聽聽聞對方乃是縹緲首徒龍雪涵。他想道這首徒嘴都是如此不乾淨,可說婦無婦德、沒有半絲溫柔婉約模樣,便認同這縹緲派正如期頂頭上司曾與之道過的,的確是番邦蠻夷治下之門派。
他雖是火大,卻不作聲色,因為他知自身功夫平平,一同惹惱了這般多人,怕這些蠻夷與邪魔歪道不與他講禮儀,在一瞬之間就動手令他命喪九泉,於是乎他先是深吸一口氣,保持冷靜,道:「諸位可知,那大倭寇事件已過超過十年,東方倭寇時不時侵擾沿岸;北方蒙古韃子雖被趕出關外,可仍其殘黨韃旦仍虎視眈眈。由此可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我們怎知西域之亦力把里又有何狼子野心?就算事實不見得是如此,朝廷與天下百姓皆是如此認為的,河南大俠河槭乃是武林泰斗,如他這般人物給人瞧見與夷狄來往,河大俠便是威名再大,亦難免落人話柄,此事看似小,卻可能造就日後江湖大亂,生靈塗炭啊!龍姑娘,雖是對不住你們縹緲派,但還請妳們別帶那異族師妹出席明日壽宴,這亦是為了中原武林的和諧,若縹緲派當真如傳言所道懷著俠心,就該避免此種事情發生!而夜姑娘妳初出江湖,若愛助人還請三思,莫要因一時糊塗,日後給人道成了人人喊打的異族鷹犬,任掌門亦是位中原英雄,若是知了妳那般身敗名裂,他老人家怕是會如何痛心啊?」
較矮的武當弟子此時亦附和道:「我的意見與夏兄同樣。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話或許偏激了些,但確實有不少人如此想,瓜田李下,只怕萬一連累了整個中原武林便不好了。」
夏良蔽已是騎虎難下,若他上頭舵主沒交代,他便是討厭異族人也不至於趕人,更何況冒著丟掉小命之危險行事。如今見到那武當首徒隋燭亦站在自己這邊,稍稍鬆了口氣。隨著武當首徒發言附和,他所帶領的那丐幫弟子亦開始同意夏良蔽之言,鼓譟起來道出許多話來,諸如「夏丐頭是對的!」;諸如「色目人滾出中原!」;諸如「異族鷹犬才不配出席河大俠壽宴!」
他畢竟是貴人之後,口才自小倒給練得不差,他這麼一道,倒似曉以大義,將黑得也道成白的了,不只丐幫弟子隨之話語起舞,聽了此言,竟是連那無天首徒穆陽飛與奕悟釗皆是面色凝重,難掩遲疑之態,懷疑自己站在縹緲派那方是否正確,夜雨榴瞧見二人神情,亦是跟著有些懷疑自己方才替那女子逝去頭上湯水究竟是否做對了。
此時,有位一直沒發話,默默吃著料理之男子,忽然大喊一聲道:「好!」似是贊同夏良蔽之言,但以其身分看來,怕是比較可能在讚揚這客棧的料理。夏良蔽不知那色目人為何許人也,只知他是由桃源門的奕悟釗所帶來的客人,而他這麼一喊,現場氣氛都給打亂了,那些丐幫弟子將怒意全投向那打斷眾人的男子身上。
那名男子膚色蒼白,瞧上去年約三十後半,身材高瘦,足達五呎,身皮革混搭鎖子輕甲,他白髮白鬚、雙目色澤如銅,腰間掛著一把十字狀護手之長劍,全然不似中原人士,論外貌那受委屈的縹緲派女徒的長相都比起他都更似漢族人一些,真虧那洛陽門衛未將之攔下。
那人便是暫居桃源谷的宗師劍客,羅傑‧艾立克。羅傑首次正眼瞧向夏良蔽,給這麼一瞧,夏良蔽竟是混身顫慄,在他印象之中唯有二人能如這般、僅眼神交會便令他如此恐懼,那便是河南大俠河槭,以及丐幫幫主蘇阿七。
夏良蔽武功不濟,亦說不上勇敢,但正因如此對於敵我差距可是瞧得很明白,那色目人肯定是震驚當世之高手,怕是只要對方有意下殺手,他這方所有丐幫弟子加上他和武當二位好手加起來齊上,也都將難逃一死。
只見那色目人高手笑道:「我本以為小孩子吵架罷了,沒想到還有人能道出這般好話來,你姓夏,名良蔽對吧?」見對方指名道姓,夏良蔽亦是故作神態自若道:「我姓夏名良蔽,字乘之,乃太子少傅之後。」可因恐懼卻是不禁呼吸急促,而身後那些丐幫弟子又叫囂,此次羅傑成了他們口中應該滾出中原的色目夷人了,也使夏良蔽多了些底氣,多少平靜了些。
羅傑全然無視那幫乞丐的叫囂,又道:「我很久沒聽過說得這般好聽的廢話了,上次聽到,還是來自我替其工作的某位諸侯之言,你口才可真不差。」夏良蔽聽言,一時之間還不知他是在褒他或是貶他,便直言問道:「你是在褒還是貶我?」
羅傑諷道:「當然是褒你啊,他最後給大王下令吊死了,只因沒了利用價值。就如同你現下這般,可謂是棄子之典範!」說罷,便放下手中筷子鼓掌起來。
替惡徒打下手,幹些傷天害理之事,終有一日亦會作為替罪羊被宰來吃。
夏良蔽知彼此功夫差距,不至於會因挑釁而失了理智,可他身後的丐幫弟子卻不是如此,聽言便破口大罵:「你這番邦蠻夷竟敢對我們丐頭不敬!」語罷,那乞丐便提著棍子一個箭步奔向羅傑,朝著他便打去!
黑光一閃,鏗鏘聲響,一柄劍未出劍鞘就將長棍格住,擋在羅傑與那乞丐之間,那出手之人如此道:「不過是嘴上的不愉快,沒必要為此流血吧?」
然而那乞丐不領情道:「臭娘們別礙事!叫化子們正在替天行道!」
夏良蔽本要出聲便要阻止手下,因為他已見到那色目人已以握劍之姿持筷,蓄勢待發,若是方才那弟子真揮棍打向對方,那異族劍客手中的筷子怕是已經插穿其咽喉。幸好夜雨榴救了那傻子一命,他在心底暗自感謝這姑娘,卻又不便表露,便道:「還請姑娘莫管閒事,丐幫弟子功夫雖未必高,但幾根硬骨頭還是有的。」既是警告那人武功不如人最好退下,也不失了丐幫面子。
他以為手底下人明白自己話中之話,可那弟子出乎意料的傻,又罵道:「沒錯!臭婆娘莫多管閒事!我丐幫鏟奸除惡還輪不到妳這丫頭插手來管!」這話一出,夏良蔽便知自己搞砸了。
隨著那弟子鼓動,竟是又有另外二名弟子提起長棍,氣勢洶洶的便朝夜雨榴逼去,夜雨榴見狀,想道她真是好心給雷劈,出手救人還給你們嫌了,甚至暗自抱怨起來這幫乞丐,欲自殺何不去找棵樹自縊去?
那夏良蔽雖為鄉丐頭,可他不見得管得動所有手底下之乞丐,畢竟他頭上還有更大的叫化子,若他出言阻止他們行俠仗義,一旦此事傳至賈舵主那兒,怕是賈舵主會質疑自己是否對丐幫忠心。他現下可說阻止那些人不是,不阻止也不是。
那帶頭的乞丐道:「臭娘們!妳不讓開我們連妳一起打!」說罷,那三人便當真朝夜雨榴揮棍而去!
接著,那最先揮棍的丐幫弟子便朝後摔得四腳朝天,摔入丐幫幫眾之中,另外二人見那人被刺飛,一時間慌了手腳,應對不及,備給隨後朝他倆襲去的二劍擊中。那二劍隔著劍鞘揮出,一劍一個。三個叫化子轉眼間都給褒禪劍法放倒在地。那三招劍招皆是平平無奇,大巧而若拙,卻又都敲在對的位置,一記尋常直刺正中心窩將叫化子一劍刺倒,隨後便是正中顏面與鼠蹊的削與撩,疼得他們短時間站不起身來。
夜雨榴搔了搔面,苦笑道:「為阻止你三人送死,只好用些粗魯的手法了,對不住了。」瞧見此,夏良蔽沉下面,暗自擔憂。方才那三劍,他一瞧便知這女流之輩功夫竟怕是整整牆出自己一截。令他不禁大駭,究竟是自個兒弱還是褒禪派厲害,一個小徒弟就有如此高明之劍藝?
註一:亦力把里國,即1420年代開始的東察合台汗國,今稱新疆。
因此嚴格說來位於天山的縹緲派不算是中原門派而是西域門派。
因為我是地理白癡,查史料時發覺天山位於現今的新疆境內,明國當時稱作亦力把里國,未被明國直接統治。
我見過武俠故事裡的「天山派」或我見過武俠連續劇裡位於天山的門派卻又是都滿滿的漢族色彩,地理位置和文化整個錯亂的感覺。
我原本是受這些謬誤影響弄出了個充滿漢族文化的縹緲派,後來才發現自己的錯漏,於是以合理性上來看的話,位於天山的縹緲派根本不可能有太多的漢文化影響。
只好大改設定,在服飾上描寫全部改掉,費了我好大的勁。
註二:
鐧,因同劍字,一種專門克制刀劍的短柄鈍器,通常是有握把與護手的一支金屬棒,鐵棒通常以四稜狀為突出,往往都是練雙鐧。
沒有見過的話很難形容它長什麼樣子。
ns18.117.111.63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