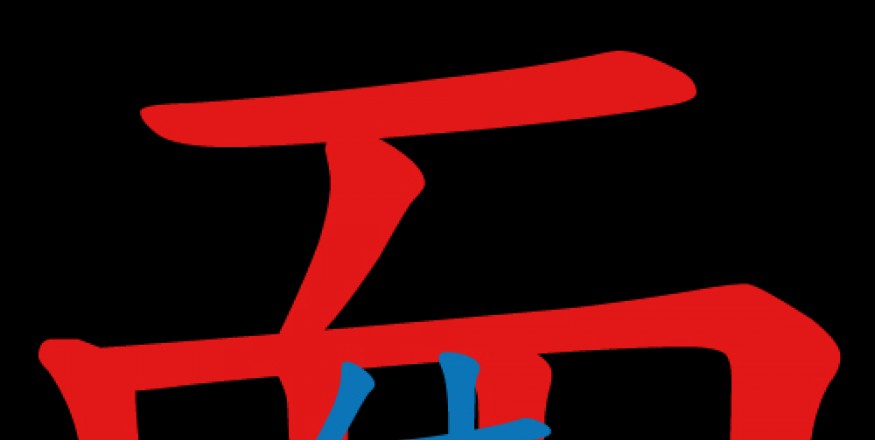序之二:萬中無一的練武奇才
待那飛雲狗走遠後,長孫讓笑道:「夏荷姑娘,您可真奇人也。」他撿起地上的赤玉辟邪,用飛雲狗落下的麻布包起,長孫讓道:「竟是僅憑眼觀就學會了我褒禪派武學,劍法、身法、心法,姑娘您一個不留的都偷師走了。」
姬夏荷身子一震道:「公、公子您看出來了?」她不知道這長孫讓打哪聽來她名字的,她更在意眼前這俠士是否要殺她,怕得不得了,這些武林人士在她眼中一只指頭就能捏死她。她也明白,方才她與那飛賊相鬥時,她之所以能佔到上風,也是因那飛賊不願傷了她,而她手中藤條亦不過只傷其皮肉,那怕是抽他個上百下都無法制服他。
「哈哈哈哈,姑娘真乃萬中無一的練武奇才,方才任某都聽到了。」老成的聲音傳入夏荷耳裡,任劍霄從灶房後門走出,雖說仍有些腳步虛浮,看來他已能行走,褒禪紫霞功於療傷方面亦算優秀。任劍霄為一派掌門,見到鎮派之寶就這麼被人給偷師走,原是一股火氣升了上來,想除之而後快。但他若當真在這裡下手,一劍殺了姬夏荷,怕是金大善人和自己的弟子都要同時惹惱了,這才忍耐下來。
他又一個轉念,想到那褒禪派在改名之前,曾是某個人人稱道的名門正派,卻因為末代掌門與嵩山派的鬥爭當中醜態畢露,儘管嵩山派就此敗亡,卻也成武林笑柄,聲名敗光。之所以改名褒禪派,亦是為求去除過往給人的壞印象,無奈的是,因祖輩累積出的名聲太差,人才凋零的困境直至三代後亦未解決,如今褒禪派弟子人數不足十人,且任劍霄名聲雖大,武功也高,早年卻已被其師父評價為資質平庸之輩,終生難晉身絕頂高手之列。今日見這姬夏荷,雖說她偷師武功乃武林大忌,但這等奇才若收為弟子,加以教導,不出十年必將青出於藍,對褒禪派有利無害。這愛才之心一起,因門戶之見燃起的殺心便全消了。
「任劍霄!瞧你教得好徒弟!竟然放走了那飛賊?」但這掌門現下還有其他問題要解決,罵聲從灶房後門傳來,那金大善人帶著自己兒子,轟的一聲推開房門來問罪,那大善人氣沖沖的,短肥的指頭都要碰到任劍霄鼻頭上了。
長孫讓道:「金先生,至少家寶未被奪去,何不放寬心。晚生見那飛雲狗出手處處留情,不似是大奸大惡之人,於是放了他一命,受了如此重傷,諒他短時間也當不了飛賊了。」
任劍霄此時卻神情大變道:「住口!讓兒。你不該讓那葉雲跑了!難不成他一時手軟就能抹除他過去的姦淫師妹、殺害知縣的罪行嗎?」任劍霄乃是護短之人,此時內心倍感煎熬,不論出於何種原因,他慶幸於弟子未追趕那飛賊,那飛雲狗所練內功相當古怪,若非他手下留情,長孫讓豈有機會活命?而他那時已身受重傷,若讓兒一追,怕是會逼得飛雲狗拚個魚死網破,兩敗俱傷。然而,他再不想給那少爺面子也該給金員外一個面子,金員外交友甚廣,倘若真得罪此一人,那便是得罪千人,他仍有褒禪派的名聲要顧,便是作戲也得在他面前訓斥愛徒。
但長孫讓可瞧不出師父只是在逢場作戲,聽到這般訓斥便面露難色,當真覺得師父怪罪自己,頭低低著,很不是滋味。
見此,那金員外嘆道:「唉!罷了罷了!兩位俠士沒有大礙便好。方才老夫也見到了,那飛雲狗功夫厲害的很。說了莫見怪,老夫怕是長孫少俠也不是對手,發了這般大火也是理虧。」這員外郎被稱作大善人自是有其理由,沒兩下就調整好了情緒,又道:「的確如長孫少俠所言,家寶沒讓人奪去便已是件喜事,據老夫所知,這亦是那飛雲狗首次盜寶失敗,先前談好的銀兩老夫事後會派人運去褒禪山去。」伸手從長孫讓手中接回那赤玉辟邪。
任劍霄抱拳回道:「任某謝過員外郎了,若員外郎不介意的話,任某還有一是相求。」任劍霄見那金員外氣已消,便決定拉下臉皮,開口相求。
金大善人問道:「任大俠又有何事相求?」
任掌門回答道:「員外郎可知道貴府內有一奇材?方才若不是她出手相助,單靠我那徒弟就怕早給那飛雲狗奪去貴府家寶。」金員外聞言,眉頭一挑,他稍前才趕來後院,既沒像長孫讓親眼所見,亦沒有華劍大俠那般耳力聽出姬夏荷有那般厲害,所以他滿腹疑惑問道:「老夫府上有這等高手?怪了,老夫怎會不曉得。」
任劍霄手指姬夏荷,笑道:「這位夏荷姑娘,方才若不是她拿著一支藤條,施展出我褒禪派的劍法與輕功,削開那飛賊腰間布袋,纏住那飛雲狗,任某那給他點了穴的徒弟必然來不及解穴並追上他。員外郎,這夏荷姑娘天資聰穎,竟是僅憑眼觀便無師自通我派武功,真乃萬中無一的練武奇材!」
聞言,金大善人又不善了,勃然大怒對姬夏荷道:「什麼?夏荷!妳膽敢偷師人家門派的武功?真是膽大包天!妳不知對俠士而言,這是何等不敬之事嗎?」姬夏荷一聽恩人對她如此說,面色都嚇白了,想說自己終究因這事敗露要就此殞命,渾身都發抖著。
她試著辯解道:「奴、奴婢並非蓄意──」,但那員外郎比起一介婢女,更不願得罪那掌門,便揚言道:「任大俠,老夫管教不嚴,府上婢女多有得罪,竟是犯下此等大錯!老夫便讓人將她一刀殺了便是!」這話一出,夏荷都雙腿一軟,跪了下來。連那金少爺都慌了,他是好色,可沒和屍體搞起來的怪癖,但這金府內是他爹說得算,他可不敢出聲忤逆。
任劍霄見他誤會,便趕忙道:「員外郎,您誤會了,任某並不想要她命。您便莫怪罪人家了,說來慚愧,員外郎也知我褒禪派三代以來人才寥寥,今日一見這等奇材,任某愛才之心油然而生,恰巧她亦學會了我派武功,與我派有緣,可否讓任某將之收為徒?」
金員外才明白搞錯,但他臉色又一沉,心忖:「你辦事不力,給那飛賊打傷也就罷了,那徒弟還放走那飛賊!至此竟有膽要搶我金府財產?我呸!這對師徒都要騎在我這員外郎頭上來了!」於是這大善人面露喜色的推託道:「既然任大俠不介意,那老夫便不對她追究。但──見任掌門您傷勢未癒,若兩位俠士無其他要事,何不早些回去歇息呢?」言下之意便是:你們快滾。
姬夏荷見老爺不追究,鬆了口氣道:「謝、謝老爺。」她不敢再奢望些什麼,什麼成為人家任掌門的徒弟,她從未想過,自然亦不會考慮加入褒禪派中,只要留了一條命,那便夠了。
浪費人才。這四字乃是任劍霄現下唯一感想,儘管如此,任劍霄亦發覺員外郎不如表現一般,仍對長孫讓放走飛雲狗一事耿耿於懷,就是憋著沒和他倆撕破臉而已,現下實非提議收徒的好時機。任劍霄無奈嘆道:「真是可惜,我倆今日就先告退了。」說今日就先告退,意味著日後仍會到訪,他亦不願見人才在金府被浪費,便放話還會為這婢女再來一次,就等他氣消再說。
金員外亦聽出了這大俠話中弦外之音,微微頷首,既然那任掌門如此堅持,只是因方才吞不那口氣才開口趕人,金員外看重家寶更重於家僕婢女是發自真心,但對家僕婢女好亦是發自真心,否則姬夏荷才不會如此敬重這老爺,若夏荷真如那掌門所說乃是奇才,那日後讓她入了人門內也無不可,婢女命苦這四字,他雖無法體會,亦能理解,他亦不願見到府內婢女總只有相同命運。可他都已經趕人了,若現下又改變主意,面子掛不住。
任劍霄見此,便對長孫讓說道:「讓兒,我們走吧。」隨後帶著長孫讓便往金府外走。
臨走前,任劍霄讓徒弟先去備馬,估計至少半刻鐘後才可歸來,此時,一位金府家僕喊住了任劍霄,貼耳細聲道:「老爺吩咐,將此物交予任大俠。」說罷,便塞了三兩銀子至任劍霄手中,又說:「這點小意思還請任大俠笑納.莫將老爺方才一時情急失言這事給傳了出去。世人只需知曉,老爺對金府家僕婢女有如家人便可。」家僕擺了個笑臉,任劍霄也擺了個臭臉,心忖:「我褒禪山雖不算富裕,卻也不缺你這幾個臭銀子。」三兩銀子可不是什麼小錢,在這世道一個平民百姓過一整年也只需一兩半,買一畝良田亦只需七至八兩銀,因此普通人家狠可能一輩子都沒見過銀兩,然而這三兩銀子對這金大善人來說似乎不算些什麼,輕易便拿得出手。
但那大俠仍是將銀兩收入懷中,收起銀兩,亦收起俠氣,他知道若他拒收,肯定會得罪金員外郎,而員外郎結識江湖豪傑眾多,他可不敢拿褒禪派名聲來賭。
而華劍大俠此時萬萬沒能想到,他這一走,便永遠的錯過那奇材了。
※
任劍霄因事務纏身和療傷抽不開身,距上次拜訪金府,已是兩個月之前的事了。兩個月來,因為金府與飛雲狗那一鬥,任劍霄識破飛雲狗身分,如今飛賊飛雲狗正是那霸天門逆徒葉雲這事已是武林皆知。當然,人們亦知這葉雲武功進步飛速,竟得以重傷一派掌門,更加顧忌此人。
任劍霄此次前來並非是為工作,僅為姬夏荷而來,他沒帶弟子,孤身一人前來,亦是怕那金員外一見長孫讓火氣又上來了。
今次拜訪,他踏入金府庭院時,便見到一名婢女正揮著掃帚,任劍霄雖老,卻沒老到會忘記那人是誰。那婢女便是當初被那飛雲狗給挾持的小桃,小桃也記得這俠客,一見他進門,便提著掃帚過去與他打了聲招呼:「啊!是!任大俠,您好。來金府有要事辦嗎?稍待片刻,小桃這就去沏壺茶給您來!」
任劍霄見這孩子年紀小,想來自己若有女兒或許亦是如此吧?這麼一想,他便不自知地露出慈父般面容,微彎腰,問道:「不用不用,小桃啊。任伯伯問妳個問題啊?夏荷姐姐去了哪兒呢?」
小桃天真地回道:「夏荷姐姐,夏荷姐姐她正為大婚前作準備呢!」
任劍霄心底一驚,想說姬夏荷怎麼就要成婚了?莫非那金員外當真這麼氣他們?這就要把她給嫁了?他便問:「夏荷姐姐是要和誰成婚呢?」小桃回道:「金少爺啊!說要娶他為妾呢!」任劍霄聽言,才想起那不是被他罵過無恥下流的金少爺嗎?想那夏荷姑娘這麼討厭他,這婚事她肯定是不願意的,護短乃人之常情,任劍霄護短,金員外亦護短,所以比起任掌門想收弟子,兒子能開心自是更重要的,金員外會同意他兒子這麼做,任劍霄亦不是不能理解。
但這下他也慌了,畢竟此乃家務事,他也沒立場好介入,但他那懷愛才之心,總希望這事最後仍有轉機。此時小桃又說:「真好吶!嫁了這麼個富貴人家少爺!從此衣食無虞!金少爺也挺體貼,說要讓夏荷姐姐大婚時更標緻些!要把她的那雙大腳弄小點。說是這個年紀才折,勉強只能弄出個鐵蓮,雖不如金銀,但他也不在意,待她傷好便要立即成婚。」
任劍霄聞言,一時矇了,他明白在這世道,許多婦女都會纏足,但任劍霄身為武林人士,又出於人才凋零的褒禪派,這生以來見過許多可造之材都因此斷送可能性,多次深感可惜,卻也無可奈何,畢竟此乃普遍之習俗。
但一經纏足,便難以藉足發力,必將腰馬無力;一經纏足,便練不了劍法;一經纏足,發出的所有勁皆將減半;一經纏足,更甭想練輕功。
可以說,一經纏足,便等同被廢了武功。
更何況,姬夏荷早已過適合纏足的年紀,這稱不上纏足,只是折腳罷了,那金少爺讓人對她這麼做,只怕是挾怨報復。報誰的復?那自是那當初幫著徒兒罵他無恥下流的任大掌門了。
他驚覺他才是那禍首,渾身顫抖,乾笑了兩聲,連道別都沒有,便以那躡影五峰奔出金府。
※
待日落許久後,任劍霄才重回金府,此次他可不是正大光明來訪的,他已準備了布條蒙於面上,這一次他可不走正門,反以輕功躍過屋簷,同飛賊一個樣闖入金府,他全力運起褒禪紫霞功增強五感,將府內所有人聲聽個、嗅個清楚,府內不知何時比先前來的要多出一十八人,還都帶著股鐵味,估計身上是有帶兵刃,且個個呼吸吐納都像是習武之人。
但他暫且不關心這些,他已用耳力聽出那姬夏荷的位置所在。輕踏數步,於屋瓦上近乎沒半點聲響,又一個飛身便落於她所在屋內的屋頂上,悄悄翻開瓦片,露個口出來。一代宗師竟如宵小般夜闖別人家,連他自己都想笑了。
他目視那道口,那房內的佈置已全然不似下人會有的模樣,想來那金少爺心意已決,他又掀開一片瓦,正巧見到那姬夏荷臥於床上,床尾擺著一壺扁狀夜壺,透著股尿味。夏荷雙足方折不足一月,疼痛令其難以入眠,欲翻身卻因雙足疼痛而未果。此景竟讓任劍霄心頭一糾,按捺不住,封上瓦片後便落於地面,推開夏荷她房門。
房門一開,自有聲響,然而夏荷臥於床上,目光沒對著門口,她想,會如此不先招呼便闖入之人除那金少爺外也不會有別人了,於是她根本不願正眼看向門口。金府上上下下每一個人都說她嫁給少爺後將幸福快樂。一介婢女能成金家之妾,立於所有家僕婢女之上,一直便是金府大多婢女之願望,甚至可說嫁為一府之妾,是這世道中大多婢女的願望。姬夏荷如此輕易便達成他人的美夢,近乎是所有人──哪怕是那金大小姐在內,都為她慶幸。
可有一人不為姬夏荷慶幸,那便是姬夏荷。
她原想說自己與金大小姐關係親密,本以為自己將會隨大小姐一同被嫁出金府,遠離那金少爺,固然她不會認識小姐丈夫,金大善人總不會給自家女兒找個太差的對象,至少據她所知,鮮有男子如那金少爺那般令她倒胃,屆時和小姐一塊從了他也未嘗不可。倘若她真不喜歡人家,也無可奈何,她是婢女,又能有多少選擇?
任劍霄解下面上布條,道:「夏荷姑娘。」他只喚其名,只因他心底慚愧,不知從何開口是好。然而,那華劍大俠出現在此,令姬夏荷猛然回首,忘了那雙足之傷,吃痛地叫了聲,即便在此時,她亦沒忘禮貌道:「先、先生?您怎麼會──」
任劍霄道:「任某就是來賠個不是!今日任某本是為求員外郎讓姑娘拜入褒禪門下拜訪金府,卻意外得知姑娘大婚在即,雙足亦被折斷,唉──」說到此處,任劍霄不禁嘆息,萬中無一的學武奇材就因一人的一己之欲而被毀,他搖頭,渾身顫抖、搖搖晃晃步向夏荷的道:「若要怪!便怪任某!若不是任某當日對那金狗子口無遮攬,也不會連累了姑娘您!都是任某的錯!」此時他已不顧與金員外的交情,開口便學著自己徒弟叫那公子狗子,姬夏荷亦聽見那掌門雙齒連連相碰之聲。
對此,姬夏荷回道:「先生請別怪罪自己,小女子亦未曾怪罪兩位俠士。這點傷才不礙事,小女子本命該如此,既身為婢,豈又敢奢求些什麼?」夏荷這話是撒謊,因為她心底的確怪罪過人家,卻又知道不應怪罪人家,或許他倆莽撞了些,卻也是出自好心,便是那日兩人未仗義相言,終有一日亦會有其他俠士喝止金少爺的。她知遭其遷怒乃是遲早之事,不願任劍霄為此事愧疚。
任劍霄聽言,臉色一青,立馬道:「妳不願讓任某愧疚對不?」一言便戳穿夏荷,姬夏荷不過是個年輕女孩,這善意之謊,又如何瞞過這閱人無數的老江湖?任劍霄又道:「任某也算多吃了幾年鹽,姑娘的這點心思,任某還是明白的。」
姬夏荷道:「先生既然明白,那又為何要讓小女子也過意不去呢。」夏荷為了讓任劍霄好受一點,絞盡腦汁的要勸他寬心:「先生所有不知,兩位俠士啟程回褒禪山後的六日,夏荷便──夏荷便已成了少爺他有實無名的妾,小女子一身功夫還不如一帖蒙汗藥,只能說小女子命該如此。夏荷一是曾為婢女,二是以為人收用,事已至此還有哪家郎君瞧得上夏荷?怕是只會笑夏荷殘花敗柳,這是天、嗚嗚──」姬夏荷雖是想勸任劍霄就此寬心,卻再也裝不了平靜,話到一半,便哽咽了起來,她深吸了口,強再開口道:「嗚──是天注定如此!」 是天注定如此,若不如此想,說不準姬夏荷早已承受不住、懸樑自盡。
於是事情徹底不對頭了。
姬夏荷本是要勸那華劍大俠莫再管此事,現下完全成了反效果。
華劍大俠細聲罵道:「那混帳狗子。」聲雖不大,卻任誰都可聽出話中怒火。隨後,任劍霄問道:「夏荷姑娘啊,妳全名為何?」姬夏荷被這突來的問題弄混了,才想起任劍霄未曾知曉她的全名,她便答道:「小──小女子姓姬,名夏荷。」
任劍霄又道:「是任某無能吶!莽撞行事,連累姑娘,任某願為此負全責。妳方才說,哪家郎君瞧得上妳,任某不能雖給妳找個如意郎君,倒可以給你個爹。姬姑娘,妳可願作任某義女?」
姬夏荷聽言,自暴自棄道:「事到如今,這又有何意義?」她想來任劍霄是希望她有個身分,免得給人家欺負了,但她又明白,哪怕是掌門收她為義女,可褒禪山離洛陽金府何其遠,遠水救不了近火,收其為義女毫無意義。但那任劍霄又道:「倘若姑娘答應,今後任某便帶妳來褒禪山一同生活,若是不答應,任某亦會將姬姑娘當我褒禪自家人。」姬夏荷驚道:「夏荷若走,老爺便失了面子,怕是老爺不肯──」
任劍霄此時便插話怒道:「管他放不放人!他若不放任某便讓他不放也得放!」語畢,夏荷才驚覺任劍霄為自己與金家樑子是結定了,世上竟有人願為一介婢女得罪一戶大家。夏荷道:「老爺結識武林豪傑眾多,倘若先生真得罪他,怕是褒禪派亦會──」
任劍霄又道:「還請姬姑娘放心,任某絕不會讓褒禪派受牽連。我任劍霄行走江湖多年,還是有些辦法的。」而夏荷見他心意已決,便不再多言。那華劍大俠走近姬夏荷旁,隔著被氌伸手往她兩腿點了幾下,道:「任某點了姑娘足上穴位,疼痛會緩和些,姬姑娘先歇息吧,或許睡起一覺後,事情便有所轉機。」語畢,任劍霄便掉頭走出門外。
「好的,您慢走,義父。」
※
當姬夏荷醒來時,發覺她已在一密封的空間內,她聽到反覆的喀拉聲響,她伸手拉開牆上一道布條。向外一看,發覺自己在荒郊野外,她才知道她已被人搬到馬車上,她又掀開前面的布幕,那任掌門正駕著馬呢。
任劍霄聽見夏荷已醒,頭也不回便道:「醒了?任某就說事情會有所轉機。」
姬夏荷一陣頭昏腦脹,一時沒搞懂發生了何事,只見任劍霄此時將一袋麻袋帶口朝下,撒出片片碎瑪瑙。赤玉辟邪完整時才會是玉辟邪,被掌力震碎後,便只是一堆碎瑪瑙罷了,分次分處散撒,便再也無人能知那本是尊赤玉辟邪。
姬夏荷低下頭來,細聲問道:「任大俠,小女子不過一介婢女,夏荷不解,為何大俠您寧冒這麼大的風險也要幫夏荷?」
任劍霄卻也只是淡然道:「那金府上上下下如此多人聯合起來欺負個小姑娘,任某已有愧於妳,若此事撒手不管,那我任劍霄便是又有愧於一個俠字!」
夏荷聽言,眼淚便欲奪眶而出,又道:「此事,乃家務事啊,沒人會管的。官府不會管,平民百姓也不會也不會管,為何──」
此次任劍霄直呼其名道:「夏荷啊。妳知道嗎?任某還依稀記得,在三十三年前,任某曾在入褒禪派那日,問過師尊他何謂俠。妳知他如何說法嗎?」認劍霄又道:「他老人家答道:若有不義之事,朝廷不管,官府不管,庶人不管,俠客便管,這便是俠。」
姬夏荷哽咽回道:「是,小女子對任掌門,嗚──感激不盡。」
若有不義之事,朝廷不管,官府不管,庶人不管,俠客便管,這便是俠。
此話自此深深烙在姬夏荷心中。
任劍霄又回首笑道:「再說,爹爹幫女兒出口惡氣,天經地義,不是嗎?昨晚妳可是叫過我義父的,我雖老,耳力卻不差,還如此見外叫我掌門作什?」
「是──嗚嗚,是!義父!爹爹!」
※
那日午夜,洛陽金府面臨血光之災,上上下下二十多口皆在一夜之內被殺盡,老爺小姐、家僕婢女,一個不留。連帶當日被雇來護著他們的洛陽蝴蝶門連帶掌門在內共一十八人全數不敵,蝴蝶門慘遭滅門。
令官府注意之一處,乃是一名年少婢女是被拍斷頸項而死,死得極快,近乎沒有痛苦,其餘死者不是被刀劍斬殺便是被氣勁震裂五臟六腑。也因此官府懷疑這名被叫作小桃的婢女和兇手有什麼關係。官府又見蝴蝶洪掌門手中刀械刃上纏有碎布,卻絲毫沒有半些鮮血,而同時金府家寶赤玉辟邪又不翼而飛,這與江湖傳言上那飛雲狗葉雲的那門邪功特徵與目的均相符,而葉雲出身自霸天門,能以劍法奪人性命一點也不奇怪。也因此官府懷疑那葉雲便是這滅門血案的兇手,加派人手要抓拿此人。
此外,金府正廳桌上被兇手擺著一整疊文書,據查證,那應是由金府地窖庫房中所搜出,上邊正寫滿了金員外郎這數年以來,多次貪贓枉法、謀害良民的證據。讓這金大善人一夕之間便成了金大爛人,這事一傳出去,江湖中人對那葉雲的評價亦有些變化,再加上飛雲狗先前只盜不殺,一些江湖中人私底下稱呼起這飛雲狗為義賊,早已浪子回頭,相約日後見了莫要為難此人。
而那金少爺和他將迎娶的丫環卻不知所蹤,三個月後,人們才在城外荒野發現一具男屍,其死狀悽慘,四肢筋骨均被斬斷,雙腿之間似遭銳器反覆戳刺、血肉模糊,屍身上亦有無數犬類牙印,不少血肉已讓野狗加餐。而那丫環,傳聞似是被逼嫁少爺而飽受折磨,給那飛雲狗放走,或其他看不下去的俠士事先救走了,那位英傑為何人江湖間仍未有定論。
所謂俠,本就是以武犯禁之狂徒。
俠道魔道,一線之隔。
※
褒禪山山腳處,華劍大俠立於在空地,而其弟子長孫讓在旁空揮劍練習那褒禪劍法,而那任劍霄倒也沒要弟子在這時練習,兩人只是在等二弟子的到來。
長孫讓恨恨罵道:「徒兒當初只是對他有些幻滅,想不到那金大善人當真是個欺世盜名的大爛人,我倆還替他辦事,收了他銀兩!現下想來還真渾身不對勁!」
任劍霄聽言,便道:「這世道便是如此,知人知面不知心,縱是見多視廣,亦難保不為奸人所迷惑。總有表面上聲名顯赫,私下惡事可沒少做的欺世盜名之徒。讓兒啊,往後你也要小心些,防人之心不可無,莫要給這種奸人給害了!」
長孫讓笑道:「徒兒謹遵教誨。」任劍霄卻又挖苦道:「唉,為師在勸你少喝點酒時你怎麼不這樣說呢?」那首徒則乾笑道:「這、這是兩回事啊。」
任劍霄話鋒一轉,問道:「仲恆他人呢?去哪了?怎麼遲還不到?為師不是說過今日此時便要驗收他我倆不在時的練習成果嗎?」
長孫讓答道:「似乎在幫忙姬姑娘,她在此處生活還不慣習,且雙足之傷仍需有人攙扶。」任劍霄點了點頭,笑道:「那就好,為師就知恆兒他本性善良,只是不善表達,該關心人時還是會關心的,夏荷就請你倆多關照了。」
看到兩名弟子都對姬夏荷來褒禪山表示歡迎,任劍霄對這麼安排亦感到安心了。
見師父心情大好,長孫讓便如往常一般打趣道:「師父,您說一個人是否欺世盜名不易判別,又說些人表面上聲名顯赫,私下惡事沒少做。可師父您亦是聲名顯赫的華劍大俠。哈哈,莫不成師父亦是欺世盜名之徒?」
任劍霄聽言,臉色一沉,陷入沉默,讓那長孫讓都嚇得噤聲,劍也不揮了,連忙說道:「徒兒這玩笑開過了,對不住。還請您息怒,原諒徒兒。」任劍霄依舊沉默,卻深感汗顏。長孫讓並不知曉他於洛陽金府所做之事,就為救夏荷一人,犧牲三十多條人命,為不波及褒禪派,為了守住褒禪派的臉面,他別無他法,只得將所有人滅口,並盜走赤玉辟邪將這血案嫁禍給葉雲。哪怕動機為何亦是欺世盜名,就算他揭發了金員外所做之惡行,試圖將那葉雲塑造成義賊,亦不過是以欺世盜名之舉舉發欺世盜名之事。想來,自己又和金員外郎有何區別呢?皆不過是為了個面子傷害無辜的邪魔歪道罷了。
任劍霄人稱大俠,但他也不是任何事情都做來問心無愧的,更說不上光明磊落。只是為守住褒禪派,他必須那麼做。
良久,他才開口道:「沒什麼,為師並未生氣。只是讓兒所言或許真是對的。這江湖啊,身不由己,人總會做出無奈之舉,就連為師有時也不知自己究竟真算個大俠,或只是欺世盜名之鼠輩。」
長孫讓低頭道:「師父自然是個頂天立地的大俠!徒兒自小與您學藝,與師父相處了這般長時間,師父的為人徒兒再清楚不過了!」任劍霄看得出來,他是真心如此認為,而不是藉機拍馬屁。
任劍霄搖搖頭,道:「這可難說。讓兒,還記得師父教過你,對付奸人惡棍要如何嗎?」長孫讓答道:「是!您說過,下山時碰上惡棍奸人,拔劍殺了便是!」
華劍大俠聽言,滿意的笑了,他拍拍徒弟的肩道:「那麼讓兒,假若有一天,你發現師父真是個欺世盜名,大奸大惡之人,你知該如何做嗎?」
這話讓長孫讓吱吱唔唔起來,他當然明白師父言下之意,但那可是以下犯上之大罪,長孫讓亦不敢隨意將其說出口。
然而,華劍大俠指著自己的心口道:「聽好了,屆時,不要管什麼大逆不道,你也應拔劍將師父殺了便是。」
此話沒有半點虛假之意,任劍霄真心如此期盼。
《面俠》 序 完。
ns3.144.210.92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