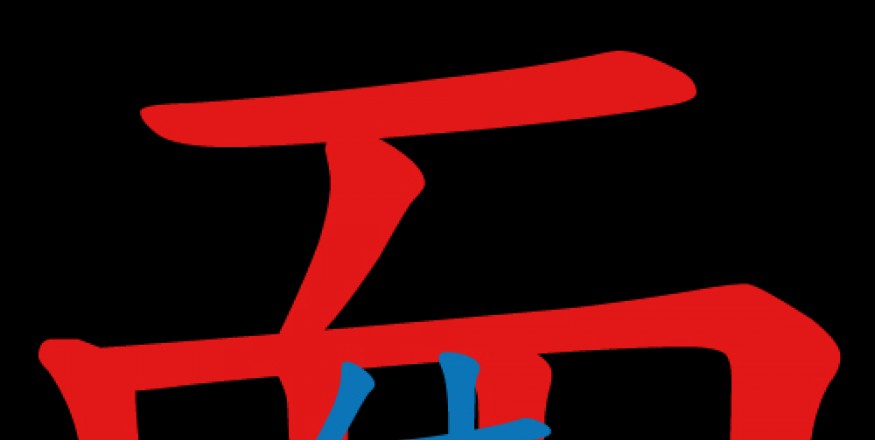第十一回:東行洛陽
只要是河南人幾乎都聽說過洛陽的河南大俠之河槭之名,他是洛陽富商之後,年少時樂於習武,其父便讓他與諸多門派的武師學習,但武林門派皆有不少不傳外人之密,最終河槭只不過學會了一票武林大路貨。
可河槭天資聰穎,竟是從這些大路貨中自行整合,又觀北斗七星之奧祕,便自行悟出一套拳法,將這套拳法命名作:北斗星拳。自此他在江湖上行俠仗義,漸成一位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河南大俠。
那河槭在武林中頗有威望,近日他便要度過五十一歲大壽,廣發請帖邀請各路武林人士來共襄盛舉,各路豪傑亦不敢不賣他這個面子。少林、武當、峨嵋、褒禪、無天、縹緲、丐幫、八卦、全真、霹靂,幾乎叫得出名字、名聲不要太小或太差的門派都收到了請帖,而一些鏢局也是,甚至連一向不為名門正派所待見的唐門與桃源村亦是如此。
夜雨榴聽聞那杜承生對此感到麻煩,便隨意推了個人讓他去代表桃源村,至於那倒楣鬼會是何人,她要等到洛陽才會知道。所幸師父給他們三人的盤纏足以讓他們雇馬車,從西向東遊,馬車可比人走得快多了,預計二日後就會到達洛陽。
此次那任劍霄學乖了,讓三名褒禪弟子都一同進退,那夜雨榴和魯仲恆前一次都差點給奸人害死,他先前僅憑功夫高低來判別會不會為奸人所害當真是個失誤,便讓長孫讓也跟著二人。
雖說魯仲恆頗討厭那種場合,和任劍霄表示他想留於山中,但任劍霄仍是強硬地讓三名弟子一同過去了。而那三名褒禪弟子正由首徒駕著馬車,另外二人坐於車上,沒兩下便鬥嘴起來了。長孫讓未阻止二人,笑著任由二人吵鬧。
忽然間,那首徒長孫讓嗅到了股異味,便將馬車停下,師弟師妹仍搞不清狀況,便給長孫讓趕下車來,並讓他倆拔出兵器備戰。
夜雨榴問道:「怎麼了?大師兄?」
長孫讓道:「有股火燒屍身之惡臭,我們去看看。」說罷,那長孫讓空指了個位置,此時夜雨榴才發覺師兄所指約莫百丈遠處正冒起一陣輕輕黑煙,方才她因為和仲恆吵嘴才會沒瞧見,平時的她決不會看漏。
夜雨榴驚道:「那是鎮子?」魯仲恆則什麼都沒察覺,那輕輕黑煙不足以引起眼力不足的他注意,他嘖了聲,從車上躍下,亮出腰間單刀。三人留下馬兒,朝著黑煙之處奔去。
方踏入河邊小鎮處,三人便見到一棟棟倒塌之平房,當中亦有不少被一火燒掉而焦黑的模樣,三人心底一震,一同走向看似還完好的井口邊,井口旁堆滿了屍體,有一、二十具,夜雨榴掃視了下屍體,發覺不論老幼青壯,井邊之之死者全是男屍,而倒塌防房內亦則都是女屍,下手之人不知是因合緣由才這般將男女分開屠殺。
魯仲恆一個皺眉,捻起一具男屍的手腕,瞧見上面仍有支玉手鐲,便自語問道:「沒有搶走財物,是有什麼深仇大恨才殺成這樣?」長孫讓聽言,亦是覺得莫名其妙,這些村人不似是遭遇流寇,而是有其他原因才落得這般下場。
夜雨榴蹲下來查看屍體的模樣,她並不像她的師兄們瞧慣了屍體,見到這些屍體身上滿是銳器傷痕,飄著腐臭與血腥味的屍身,她胃袋內之物就似要湧了出來,但她忍住了,掩住口鼻,以右手手指翻動屍身的衣物,喃喃道:「得罪了。」她仔細檢視傷口,胸口三處刀傷,咽喉一處刀傷,雙眼亦給銳器刺瞎,左手臂三處刀傷。當她檢視到下半身時,她臉色一青,這名男子竟給人去勢。
她連忙起身,檢視了這些死者,不論老幼,不論死因,胯下之物都給人砍掉或弄得血肉模糊,她自己曾遭遇二次淫賊,亦不是不能懂為何有人會想如此做,可下手之人究竟對男性有什麼深仇大恨?畢竟總不會道五歲幼童當得了淫賊吧?
長孫讓道:「只針對男子下這般狠手,應該是南狄邪教,先前我和師父一同到洛陽時,聽聞過他們,但從未見過他們下手。聽說洛陽丐幫多次想要剿滅他們,卻因不知他們據點位於何處,陷於被動,連連失利。」魯仲恆問道:「南什麼邪教啊?聽都沒聽說過。」長孫讓苦笑道:「如果我們在褒禪山也聽說過他們的話,那南狄邪教怕是已驚動全武林了,可師兄我僅聽說他們在河南一帶行事。」
夜雨榴想道大師兄見多識廣,竟會對這邪教略知一二,可聽其所言,這邪教之危害亦僅限於河南一帶,她不知該道是幸好那邪教猖獗之處僅限河南,又或是該替這些受害者感到難過。
長孫讓道:「南狄邪教為人所知似乎已有三年之久,無人知他們究竟想要什麼,只聽聞他們當中不少彪形大漢,不好對付,每當至一個村落時便殺盡所有男子、擄走所有幼女,怕是要賣給其他邪魔歪道。」魯仲恆左看右瞧,還真沒在屍體之中見到年幼女童,可瞧見眼前慘況,他亦怒道:「那河南大俠和無天派不都居於河南嗎?這等邪魔歪道,竟是無人拿他們有辦法?哼,我還以為河南英傑輩出,卻盡是無能之輩?」
夜雨榴在旁聽言,總覺得有不合理之處,長孫讓所聽聞之傳言似乎與現況有哪兒不對勁。若這邪教真如長孫讓所言當中有不少成員皆是彪形大漢,那瞧上去肯定很醒目,怎又會三年來仍找不著他們的據點?而一群彪形大漢又有何理由只對男性都下這般狠的手?她實在想不透。若是那群邪魔歪道擄走幼女是為賣予他人賺錢,亦是不大合理,身為女子,夜雨榴自是生來便厭惡將女子當作貨品買賣之人,卻亦了解年輕女性的價格會比幼女高得多,畢竟就算是淫賊亦多半對幼女不感興趣,若南狄邪教之目的是錢財,卻又為何要對村中理應價格可提得更高些的那些年輕女子視而不見,反而出手殺之?更別說留著玉鐲這等貴重品不取走,此事頗為蹊蹺。
夜雨榴覺得或許她想多了,或許他們的行為僅是某種邪教儀式,毫無實質意義,無法以世俗的眼光去判斷,若以世俗眼光去看待自然會有所偏差。夜雨榴一直以來都認為那長孫讓功夫高強、正氣凜然、彬彬有禮、毫無缺點可言,在她瞧來大師兄根本是個完人,可如今她亦懷疑了,那大師兄當真是個完人嗎?當真不會有弄錯的可能嗎?竟是不覺得此些傳言滿是疑點?
大師兄所道之言十分奇怪。
這還是夜雨榴首次這般認為。
她不知這世間,不論是完人或是小人,都可能給謠言蒙騙。
忽然間,夜雨榴瞧見了村口處有二十數人前來,那幫人蓬頭垢面,渾身服裝破爛、服上不少破洞補丁,瞧上去五顏六色,領頭之男子瞧上去與長孫讓年齡,乃是二十後半。他手提一支黃桿子,拄著桿子一步一步走至褒禪派三徒跟前,那些人一近,她便聞到一股騷臭味,那乃是泥垢、糞土與汗混成之異味,她雖知無禮,卻也不禁皺起眉頭。
那提著黃杆子的領頭男子,停下腳步便道:「這位小兄弟不知師承何派,
竟道我等洛陽丐幫是無能之輩。」似乎是對魯仲恆之言有些不滿,他表明身分,道明他們乃是丐幫弟子。
魯仲恆知曉丐幫分舵眾多,以洛陽分舵為中心的丐幫在河南一帶十分活躍,若南狄邪教在河南作亂,那洛陽丐幫肯定曾與之交過手,亦或許折損了不少人馬,也因此那黃桿乞丐才會對魯仲恆之言頗有微詞。
夜雨榴知其是天下第一大幫,便是覺得臭也不敢對這些乞丐有怠慢,她想到二師兄總是話說得難聽,難免得罪人,可丐幫卻是二師兄得罪不起的,便試著替魯仲恆解釋道:「原來是諸位是丐幫弟子,見笑了,二師兄他總是口不擇言,還望閣下莫要介懷。小女子乃是褒禪派門徒夜雨榴,這位是二師兄魯仲恆,大師兄長孫讓。」
那年輕乞丐眉頭一挑,吐了口息,想道長幼有序,師妹介紹師兄成何體統?況且一介女流之輩哪來的立場說話?他斜眼瞧了夜雨榴一眼後,便轉向對長孫讓抱拳道:「竟是那位褒禪飲中俠!夏某久仰大名!」他聽聞過褒禪飲中俠之名,只是一人在河南一人在陝西,未曾謀面。今日一見果真如傳聞一般,縱是單單看去便有股英氣逼人之感。
長孫讓笑道:「不敢當,虛名罷了。在下倒久聞丐幫威名,還敢問這位兄臺尊姓大名?」
黃桿乞丐笑道:「我姓夏名良蔽,字乘之。太子少傅之後,父親早年經商失敗,家道中落,我加入丐幫好混口飯吃罷了,沒想到便混成了個鄉丐頭。」隨後瞧了四周慘狀,嘆道:「唉,這又是南狄邪教所為吧?我等又晚來了一步,那南狄邪教畏首畏尾,狡猾至極。慚愧啊!這群邪魔歪道功夫不差,行事又如此躲躲藏藏,我們這幫叫化子三年來與之交手多次,亦只可將之擊退,無法找出這幫惡徒老巢位於何處!」
魯仲恆聽言,便問道:「你們這不就承認自個兒沒用了,方才道我你們沒用你還生氣做什?」那夏良蔽聽言,差點氣得耳裡冒出火焰了,其身後的乞丐亦是舉起桿子來就似要動手。常理道,江湖人士聽他這般道,無不是有禮的道些好話安慰安慰這夏良蔽,更可能順便多添個幾句鼓勵其,可魯仲恆說話直得很,不按牌理出牌之語將他的臉皮撕個粉碎。
夏良蔽他握緊那支黃桿子,沉默不語,那黃桿子象徵其為貴人之後,那丐幫弟子共分兩類,藍桿與黃桿,藍桿弟子乃是一般市井之徒成為的乞丐,黃桿弟子則由家道中落的達官顯赫、皇親貴族子弟組成。為以服眾,幫主多是藍桿弟子出身;而舵主、丐頭一類通常為黃桿弟子擔任。
他自認身為黃桿弟子,即使乞丐亦高庶人一等,如今竟是給這不知尊卑的臭小子當面羞辱,氣得說不出話來。
夜雨榴察覺其面色有異,連忙道:「師、師兄!你怎這般道?得罪人家夏丐頭了!」長孫讓亦道:「阿恆!你怎麼這般失禮!快對夏兄道歉!」
魯仲恆又道:「哼,你倆擺那假得要死笑臉做什麼?若是丐幫與那邪教多次交手,就該比我們更了解他們,但我們都已經瞧完屍體了,他們才到來,這般慢郎中怪不得抓不著人家,還要人家道他們幹得很好?胡說八道亦該有限度,你們能瞧著這些屍體,道出這番話,但我可不能!」
夜雨榴明白他二師兄脾氣不好,又嫉惡如仇,瞧見這滅村慘況自是忿忿不平,如今眼前這丐幫中人惺惺作態的求稱讚,長孫讓或許會不動聲色的附和其言,但魯仲恆可受不了這般彎彎繞繞的,想要他賣丐幫個面子根本沒門,他本就不善與人來往,一直以來便是有話直說,這般直腸子性格是夜雨榴為何喜歡上他的原因、亦或許是那魯仲恆武功雖沒低長孫讓多少,名氣卻不甚的原因,說話太直,得罪的人多了,江湖上朋友便少,自然鮮有人談論其。
那夏良蔽被罵成這樣自然心有不甘,卻又知眼前這位少俠乃是義憤之下才會道出這些失禮之言,骨子裡仍是俠者風範,夏良蔽雖是有些自以為是,卻也不願將事情鬧大,同是名門正派,口頭上吵吵還可以,動手就成大事了。於是便道:「我知這位兄弟是出於義憤才口不擇言,不願與你多計較,但請記著!今日是你無禮,我等不跟你計較,不意味著我等承認你那所謂無能之評價。」
魯仲恆依舊毫無歉意「哼」了一聲,那黃桿乞丐搖頭嘆息,對長孫讓道:「長孫少俠,別過了,我等德將此事告知舵主。」說罷,便他率著眾人走離村內,留下褒禪派三徒,夜雨榴覺得奇怪,那夏良蔽竟是全然不觀察村內死屍,若是這般只是瞧一眼,知道有村莊給滅了,要通報給頂頭上司,卻不多留下來細看狀況,怪不得追了人家三年仍找不著人家老巢在哪。
見那幾人已然離去,夜雨榴不發一語,便開始四處遊蕩,那魯仲恆和長孫讓亦看不懂她是要做些什麼,直到她在一戶倒塌的人家內找到一柄鏟子,伸手使勁從中抽出,提著鏟子便找了個空地,將鏟子刺入土中,默默地替這些無辜死者們掘墓。
長孫讓見此,嘆息道:「師妹,我們還有路要趕,那河南大俠壽宴也不會等我們,晚到了便不好了。」馬車只有一輛,供三人乘坐,他們仍須趕路,若在此處耽擱了怕會讓河南大俠以為褒禪派不給面子。
夜雨榴道:「這般讓他們曝屍荒野,如此撒手不管他們也太可憐了。」說罷,又以鏟翻開土來,反覆幾次,地上已有個小坑,她憶起她入門前衛夫子村發生之事,憶起當年村中夫子所告誡之言,道死者皆必須獲得安葬。儘管前朝火葬風行,這朝卻認為犯大惡需焚其屍,但普通人家焚屍乃傷風敗俗之舉,甚至必須處以極刑,那衛夫子生前並不信鬼神之說,可他亦道過人身屍首須好好葬下,否則怕會引起瘟疫,害人性命,雨榴生性善良,決不願見此事發生。
她早已受夠替人挖墳,況且那些屍身已發出陣陣腐臭,令她面色蒼白胃中之物翻攪,她忍著吐意,咬緊牙關,以前臂拭去額上汗水,只是默默地翻開土,終於才將一具屍體推入坑中。
長孫讓又道:「師妹,官府的人會來處理的,現下我們還是離──」此時魯仲恆從長孫讓身旁走過,左顧右盼,找不著第二支鏟,便從地上隨手抓了根木柱,至夜雨榴身旁,以木柱鑿地,道:「師妹她做得對,我倆得先好好安葬這些人,那河南大蝦要生氣就給他生氣唄,大不了黑蝦子氣成紅蝦子!」
聽言,夜雨榴便不禁莞爾,魯仲恆此時又道:「很好啊!我喜歡看妳笑! 但要是真笑,和剛才的假笑的樣子天差地遠!」若是平時他道出這話來,這話肯定讓夜雨榴滿面通紅,可現下她可在做正經事,顧不得為此歡喜,將羞意全往肚裡吞去,在替人挖墳埋屍之時肯定不是什麼打情罵俏的好時機,她年紀雖輕,亦分得清事情輕重緩急,這股甜滋滋的味道她便藏於心中,久久記著。
長孫讓見二人都跳下去幹這事,道:「唉!罷了,師妹說的對!不該讓他們陳屍於此,此地離大城遠,官府之人若到了怕是已瘟疫橫生。」便也挽起衣袖,在廢墟間挑了支破棍子和師妹與師弟一同挖土。
長孫讓知這事是吃力不討好,諸多武林中人總是吹噓著自己鏟多少奸除多少惡,以示自身乃是俠義之士,掙得個善名,在求善名之時,許多俠客或許皆忘了俠道之本質乃是助人,替無辜之人挖墳葬屍一事,怕是江湖中任何人都辦得到,卻不是所有江湖中人願意幹的,便是讓人知道了亦不會闖出什麼名聲來,還可能給人調侃搶了官差飯碗。夜雨榴初入江湖,不在乎那些無謂聲名面子。
想到這,那長孫讓便是一陣顫抖,他現下以二十七歲,他驚覺自己在某處已和那些為了面子行善的俠客有幾分相似,行俠仗義之本心以忘卻三、四成,對眼前的小姑娘感到自嘆不如。功夫人人可以練,俠義心腸可不見得能。瞧著這小師妹的身影,他露出微笑,心中一陣暖流流過,小師妹縱然小他十歲,他便覺得若有這般好姑娘陪伴終身,肯定會是樁美──
──此時,他一個大駭,甩了自己一耳光,令魯仲恆和夜雨榴都朝他瞧,前者問道:「師兄你做什麼忽然甩自個兒耳光啊?」長孫讓便是慌張苦笑,撒謊道:「沒什麼,想到方才自個兒竟是忘了俠義之心,只為怕失面子那般阻擾師妹,實在慚愧。」但心中卻是暗忖:「尚兄他屍骨未寒,我竟對他情娘有這種想法?況且小師妹意中人乃是阿恆,我竟想行這般不義之舉?長孫讓你真是罪該萬死!」
然而那夜雨榴真信了他的話,笑道:「怎麼會,雨榴亦知大師兄肩上有褒禪派首徒之責,怕一個不小心給褒禪派蒙羞,有此顧慮乃理所當然。反倒是雨榴有些無理取鬧了。」此話讓長孫讓身子又是一震,更是不知所措,他移開視線,故作鎮定嘆息道:「那我今日便陪師妹妳任性一回吧!」
※
所幸褒禪師兄妹三人提早出發,當中談不上快馬加鞭,就算被那村莊之慘事所耽擱,亦是如期到達洛陽,甚至還早了一日到達,四月十二日晚間,天色已暗之時,三人已達洛陽城門口,那夜雨榴未曾到訪洛陽,只知那說到洛陽,便要說說那最知名的天下第一古剎白馬寺,她雖是對佛理一竅不通,亦不會不想參觀古蹟,當初便是抱著來祝壽順便玩樂之心態而來,若不是途中目睹慘事,心情壓根不會受影響。
但比起玩樂,師父交代過更為重要的事情,他三人方入洛陽城門口,便有一身材高宨,年近三十之女子前來上前,與長孫讓打了聲招呼道:「長孫少俠,別來無恙。」
那女子身材高大,竟有五呎四吋之長,背後則揹著一挺長火銃,夜雨榴可說從未見過身長如此長之女子,雨榴又觀其面容,發覺這女子面相不全似漢人,在五官突出,顯得有些西域色目人之血統。雨榴瞧這女子,年近三十,卻仍風韻猶存,瞧得她目不轉睛。
長孫讓介紹道:「雲護法,別來無恙。師弟、師妹、這位是霹靂堂四大護法中的前護法,人稱銳眼神銃的雲翯莉。」
察覺了雨榴死盯著她面容,女子撫了撫下顎笑道:「我有二分之一蒙古人,四分之一的羅剎人血統。」夜雨榴才知雲護法已察覺其視線,連忙低頭抱拳便道:「前、前輩,失禮了!晚輩乃褒禪派三弟子夜雨榴。」魯仲恆見狀,亦是有禮的打了聲招呼道:「我則是褒禪派二徒魯仲恆。」
雲翯莉笑道:「莫需如此介懷,我這副長相在中原很少見,經常給人盯著看。」長孫讓亦解釋道:「我聞霹靂堂與北方韃旦國位置相近,當地人與外族通婚並非少見之事。」雲翯莉又道:「沒錯,可以說霹靂堂弟子混有外族血統常見之事,門人當中亦有不少外族人。」
雲翯莉又道:「幾位少俠是來參加河大俠壽宴的吧?我與門下弟子亦是來早了些,仍有要事去找門下弟子,就在此告辭了。」說罷,那雲翯莉便轉身朝集市之處走去。
當今朝廷與不喜異族人士,在政策上對漢族以外民族之人多有打壓,那自稱忠肝義膽的丐幫亦是因此變得如此,也因此霹靂堂之類位於中洲邊緣處、與外族接觸頻繁的門派才會讓人遊走於中原與中原門派搞好關係,要知這世道教育不甚普及,且資訊傳遞尚不發達,同一件事以訛傳訛下,隔了一處便可能變得與事實天差地遠,而謠言一個不小心便可能引發仇恨,此類的門派絕不樂見此類事情發生。
在雲翯莉離去後,夜雨榴發覺魯仲恆一臉不悅,便問道:「怎麼了?二師兄?」
魯仲恆此時說道:「我最討厭這種場合了,就要和這些一大堆其他們派的人打交道,介紹一堆東一堆西的人。想到明天這種事情還要在重複個數十次就讓人心煩。」夜雨榴覺得她越來越了解這師兄,便苦笑道:「師兄,你忍耐些吧?這也是為了褒禪派。」魯仲恆聽言,忿忿道:「哼,我當然知道。」
※
找到適當的客棧寄宿後,三人先去了河府拜會,河府家僕交代交代他們明日午時再至便可。三人便依夜雨榴的意去洛陽市集處逛逛,夜雨榴順手買了些包子吃吃,本是打算吃些東西後便回客棧。但那魯仲恆煩惱的事情又找上了二人。
「這不是長孫少俠嗎?好久不見。」
忽然之間,一個略帶稚氣的男聲從旁響起,集市之間雖有人群嘈雜之聲,仍能讓三人聽見這聲音,夜雨榴朝聲音來處一瞧,竟是見到了衛蕸站在一名少年身後,微微朝她招手。那矮小的少年身後除了衛蕸,似乎仍帶了另一名四十多歲的男子,他沉默不語,對褒禪派三人的視線毫無反應。
長孫讓見到那少年,笑道:「唐公子,一年不見了,您長得高大些了。」接著介紹道:「師弟、師妹,這位是四川唐門少主,唐少鋒。」
那唐門少主唐少鋒年方十三,不論容貌或是聲調都帶著絲稚氣,長孫讓正要對唐門少主介紹兩位師弟妹時,那少主便笑道:「想必兩位就是魯仲恆少俠和夜雨榴女俠吧?衛遠業司和我道過不少您二人之事。」
遠業司三字真將雨榴給弄矇了,武林門派眾多,構成形式亦是各式各樣,各種職位都不大同,她還真聽不出蕸姊在唐門中擔當什麼樣的職位。
衛蕸笑著走至雨榴身旁,輕拉她的手,笑道:「雨榴,別來無恙了!」夜雨榴見她道:「蕸姊,我很好,這段時間裡過得如何?」
長孫讓聽小師妹對那豐腴女子的稱呼,察覺此名女子正是當初救了魯仲恆一命的衛蕸,便笑道:「原來這位就是蛇影俠女,久仰大名,長安那時多謝對師弟他出手相助了。」那魯仲恆雖然不擅交際,卻仍對衛蕸簡短道:「衛姑娘,您好。」
衛蕸先前在長安見過魯仲恆,那時她便知道魯仲恆乃是口硬心熱,不善交際之人,而先前他總叫她肥婆花癡,今次竟叫了她衛姑娘?她自認尚不夠了解魯仲恆,不知這是該喜還是該悲,但仍是笑道:「真稀奇,魯公子還是頭一次叫我衛姑娘呢!」
魯仲恆聽言,又道:「哼,我怎麼叫妳是我的事情。」
最後,夜雨榴瞧向那年約不惑的男子,問道:「那這位前輩又是?」
男子面無表情,簡短答道:「谷思邈。」似乎與魯仲恆相同,同是不善交際之人,但他話之簡短,讓夜雨榴和長孫讓都愣了一下,不知從何接起話來,一時間氣氛變得尷尬,衛蕸才連忙打圓場,苦笑道:「他是家師谷思邈,平時多待在門內,話雖不多,但人品和武功都遠超於我。」
魯仲恆聽言,誤解了衛蕸言中之意,皺眉道:「做什麼把自己講成壞人似的?妳的人品除了有點花癡外絕對很好啊!別忘了我可欠妳一條命啊!妳便是要求我替妳做什麼都行!」
衛蕸聽魯仲恆這般道,猛然轉過身遮住了臉,只因其脹紅面,不敢給褒禪派三人瞧見,喃喃自語地細聲反覆道:「做什麼都行?做什麼都行?」鬧得他們三人皆摸不著頭腦。谷思邈見弟子這般反應,竟是面露微笑道:「少主,看來您說得沒錯。」而那唐少鋒亦是露出不似他那年齡會有的賊笑,忽然朝衛蕸雙掌一推,衛蕸沒反應過來,給那唐門少主這般推,失了平衡,恰好落至魯仲恆那兒,面部輕輕撞在魯仲恆肩上,兩團軟玉就這麼貼上了魯仲恆,魯仲恆面色一紅,連忙扶起衛蕸,輕輕推開衛蕸,道:「妳沒事吧?」衛蕸僅是微微頷首,未有答話。
魯仲恆怒道:「喂!小鬼頭!你作什麼推人啊!很危險的!」但他未想到那唐少鋒聽言竟是故作訝異,誇張地道:「你當真不知道為什麼?真是個傻子!」魯仲恆聽不明白,只覺得那小毛孩罵他傻,便破口大罵道:「你這小鬼才傻子呢!」唐少鋒又嘻笑道:「就是不明白別人為何罵你傻,你才是個傻蛋啊!」
谷思邈見狀,什麼也沒道,僅是搖首嘆息。
夜雨榴這下什麼都懂了,思緒卻也因此變得一團亂。
註一:
太子少傅,教導太子的老師之一,但地位較低,後來成為虛職。
是從一品官,僅次正一品,官位大得嚇死人。
註二:
明代禁止火葬與水葬,對一般人這麼做是要殺頭的。
估計理由和穆斯林認為火葬也是傷害死者的理由相近。
註三:
羅剎人,古代中國對俄羅斯人的稱呼。
註四:
韃旦國,北元後之蒙古政權,韃旦是明人對其之稱呼,實際上國號仍是蒙古國。
ns 15.158.61.13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