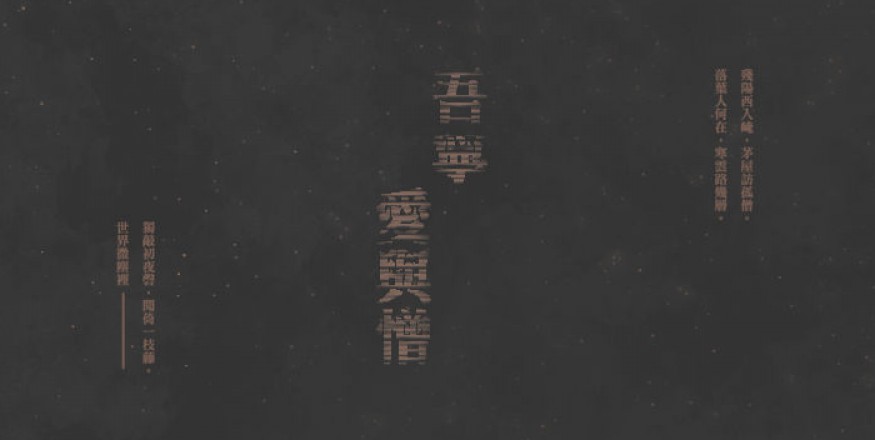入夜,萬籟無聲。
北嫺怡平躺在床,身旁北張罔市的呼吸綿長,與對門主臥的鼾聲相唱和。身下拿來應急的雙人床墊久無人用,瀰漫一股衝鼻且滲入裡層的霉味,更糟的是,硬梆梆的毫無彈性。
不知是床的緣故抑或枕邊換了人,她雖身心疲憊卻一點睏意也無。她向左翻身,只覺頂住床面的手肘像按在水泥地上,側躺的她臉朝北張罔市,北張罔市身後緊鄰一面斑駁的白牆,房裡唯一的窗就開在那,沒有吊掛厚實的窗簾遮光、保護隱私,但可以看見的景觀也僅是鄰居樓房的外牆。
被完美破壞採光的房間晦暗,幾縷月光勉強描繪出物體線條,北嫺怡目光一轉,忽見一雙白濁的眼眸直瞪著她,她抖了一下,差點驚呼出聲,凝神一瞧發覺北張罔市不知何時醒了,睜著雙眼眨也不眨的緊盯自己。
「阿嬤……妳是想上廁所嗎?」
北嫺怡輕聲詢問,壓下忽然侵襲心頭的悚然之感,起身,準備挪向北張罔市。
「哩嘶……哩……麥……哩喜……」
「什麼?」
北嫺怡微微彎腰,想聽清楚北張罔市的言語,卻仍得到一坨模糊的聲調以及意義不明的嘶嘶氣音。
她不得不側耳,貼近北張罔市的唇邊,正當有點拼湊出幾個字時,一道外力撲來,她猛地向後仰倒,碰的巨響,撞到了床頭櫃。左肩隱隱作痛,北嫺怡愣是呆了五秒才反應過來剛剛發生什麼事。
她搓揉肩膀重新坐正,不可思議的望向北張罔市,方才的那一推似乎耗盡她全身力氣,呼喝的急喘。北張罔市專注凝睇的眸子緊鎖著北嫺怡,深處積累多年的憎恨穿透混濁的緩衝,清晰刺進北嫺怡的胸膛,可是她不畏懼亦不訝異,因為她明白北張罔市恨的對象不是她,而是她從那含糊話語中拼湊而出的「不肖媳婦」──
她的母親。
北張罔市的雙唇依然開合不停,仍舊把她當作媳婦教訓著。她垂下雙眸,不發一語的走往門邊的開關,喀答一響,房間大亮。
眼睛刺痛,北嫺怡反射性瞇起眼,視野影影綽綽,她母親提著行李袋的決絕背影彷彿立於身前,耳畔徘徊稚嫩單純的童音,問著:「媽媽妳要去哪裡?」
那晚,她母親沒有留下隻字片語,也沒有回頭看看她,趁著她父親在醫院陪夜之時,永遠消失在她往後的人生。她不曉得這事過後他們是如何辦妥離婚手續的,只曉得自此沒了母親,只曉得獨自照料病重阿公的父親日益消瘦,只曉得幾星期後阿公便過世了……死在她父親手裡。
而後,入獄的父親在受審前一晚自盡。
遺書寫道:「每個人都解脫了。」
北嫺怡眨眼,將那一幕幕眨回記憶底層,眼前景象只剩嘴中唸唸有詞的北張罔市,這還是北張罔市第一次在她面前提起她母親,縱然是以辱罵的方式。北嫺怡走上前,坐至床沿,心底有些複雜。
怨恨嗎?可能吧。
如若她母親當初沒有離開……
北嫺怡嘴角勾起一抹苦澀,她失去父母太久太久,連想像也不知要怎麼描摹,她寄人籬下太久太久,早已不知什麼叫溫馨家庭。
她回身,輕輕牽住北張罔市的左手,溫熱掌心一如既往,她的指尖不禁微微顫抖,「阿嬤,妳睡迷糊了,我是嫺怡啊。」
還來不及給予安撫的笑容,北嫺怡倏地倒吸口氣,下意識放開了手。三條淺粉抓痕橫越整隻手背,不過轉瞬,痕跡高凸,腫痛的傷口旁有些微破皮的碎屑。她摀住手,十分不解的直盯北張罔市,對方眼神充盈戾氣、敵意極深,貌似仍將她認成「不肖媳婦」又或者錯認成陌生人。
她瞄向那攻擊她、皺如雞爪的手,於靜止狀態下劇烈的顫動。耳裡不停接收到北張罔市綿延不絕、誦經般的沉聲亂語,這下,北嫺怡的背脊是真的有些發毛。心跳逐漸加速,快得可以衝出喉嚨,她雙掌緊握交疊,是聊勝於無的慰藉,掌心的冷汗使得傷痕刺痛,她艱難的揚起微笑,「阿嬤……我是嫺怡,北嫺怡。」
無用。
北張罔市渾身傾瀉著暴戾之氣宛如一頭曠野猛獸,北嫺怡與她相望,毫無經驗的她已然無計可施又不敢大半夜吵醒單良延。不知是因為無助、恐懼還是疼愛她的親人變得如此陌生,一陣酸楚猝然襲上鼻頭,燙紅她的眼眶,她語帶哽咽、重複低語,「阿嬤,我是嫺怡啊……」
「阿嬤,我是嫺怡……」
「阿嬤,我是嫺怡──」
為什麼認不出她了呢?
怎麼忽然認成遙遠那年的人呢?
「喂!」
北嫺怡霍地睜眼,房裡的燈被人關了,絲縷晨光代替了朦朧月光,卻仍是未能驅走房內的幽暗。
「喂!還要我叫妳起床啊?都幾點了?」
是單良延的聲音。
北嫺怡迷茫的轉頭,僵硬的脖子炸出強烈痠痛,她按住脖頸緩緩轉回原位,忍著不適,本能的回應著:「我馬上就下去,很快。」
「馬上?妳不要忘了阿嬤的早餐還有藥……算了,隨便妳啦,我算妳遲到扣點薪水好了。」這回答是單良延難得的寬容,他停頓幾秒又說:「妳昨天這個姿勢睡覺?」
北嫺怡胡亂點頭,挺直腰板伸展筋骨,她清楚昨晚一定是在那詭譎的對峙下昏睡過去,而她不敢靠北張罔市過近,縮在床的一角、背倚床頭櫃,半坐半躺,難怪全身肌肉都那麼緊繃。
「喔。」單良延沒打算追問,簡單應了聲便扭頭離去。
北嫺怡並未將注意力放在單良延身上,她靜靜打量北張罔市睡著時平和的容顏,昨夜那無預警冒出的野獸也一同沉睡。原本她只感到詭異,但在剛剛聽見單良延提到「藥」時,她猛然憶起迷糊睡去前,內心莫名昇起的臆測──帕金森的主要症狀並沒有認不清人這一項。
那麼真正的原因該不會是……
她溜下床,不顧散架似的骨頭、發麻的右腿,一跛一跛的走往床尾,拎起北張罔市的行李袋回到床邊,唰的拉開拉鍊,放在所有衣物上方的即是北張罔市的藥物。本該是同種藥品裝在一個藥袋,可二叔非常「貼心」的依據每日每餐的服用量,將它們以透明夾鏈袋分裝好,上頭還有用黑色奇異筆寫著早、中、晚餐、飯後等等的標註。
見識過北張罔市異常的舉止,此番貼心已淪為別有用心。北嫺怡深吸口氣,昨晚的緊張感似乎仍殘留著、從未消退,她拾起一小包,仔細研究,袋裡有著普遍的胃藥、一粒膠囊、一顆直徑約略一公分的藥錠。
膠囊一端深綠一端粉藍,印有一行字母「ROCHE」,她伸長手臂抓起床頭櫃上的手機,解鎖後直接進入搜尋,打上ROCHE,滑了幾個頁面發現只是造藥廠商的名字,於是目標轉為那枚淺黃藥錠,一面刻有數字10,另一面則是一圈字母「I、C、E、P、T、A、R」,她思量片刻,從十二點鐘方向的字母開始依序排列組合、輸入,幸運的,她僅查了三次,便得到解答──Aricept,愛憶欣。
是治療阿茲海默症的藥物。
二叔沒有告訴她實話,北張罔市不只患有帕金森氏症,還合併阿茲海默症。
北嫺怡攥緊拳頭,泛白的關節下一秒已可撐破皮膚。
她受夠了。
真的受夠了。
以前,叔叔那兩家人視她為外來者、不把她當親子女疼愛便罷,她的確是闖入別人家庭的突兀存在。那些年她忍氣吞聲、逆來順受,更甚婚後斷聯,只是想還給他們一個清靜,怎料──
成了他人得寸進尺的籌碼。240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5Xwk2reOx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