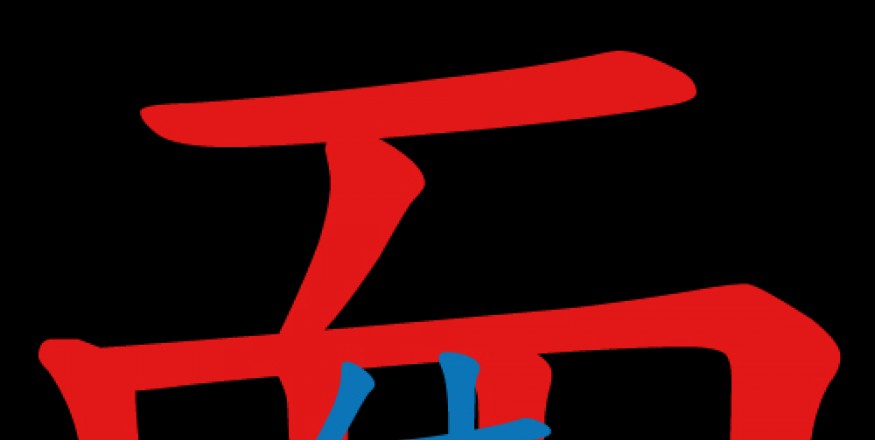第十回:瑪迦拳
隨著第三名對手,使用雙板斧的李大爺李喬上場,那褒禪飲中俠長孫讓僅用三招就將對手擊敗。之後,那些村民也一個個席地而坐,吃起帶來的食物來,一時間褒禪派就好似開了場宴會般。杜承生將小番韭帶下去後,那杜承生提著一酒葫蘆,獨自一人喝著悶酒,夜雨榴便單獨去找在一旁倚著樹歇息的杜承生。她仍有許多事情想要與他問個明白。
於是她好奇問道:「方才那位小姑娘與葉雲有關?」杜承生聽言,苦笑道:「好吧,我瞞不住了。她的確是葉兄託給我照顧的,是他友人的女兒。」
夜雨榴想道,那不就意味著杜承生早就已經認識葉雲了嗎?在葉雲尚被視作淫賊之時,這人竟願意冒著風險幫助他,這也便意味著,那杜承生早知那葉雲乃是清白之人,而且恐怕亦知那淫賊為何人,才會警告魯仲恆與夜雨榴莫接近廖非豪。
夜雨榴道:「你知道淫賊其實是廖非豪對吧?」杜承生道:「我知,我去四處打聽長安城失蹤之年輕女子,最後給人目擊之處,詳加比對後覺得霸天門最為可疑,所以早已懷疑淫賊是他。」
夜雨榴怒道:「那為何不提醒我們!葉雲並不是淫賊廖非豪才是!你知道你這般不說,害得小妹我──」憶起那日之事,雨榴便覺得一陣屈辱與惱火。見狀,杜承生低下頭來,苦笑道:「因為你們當初不相信葉兄,我只好瞞著你們,那時的狀況不由得我選。」夜雨榴聽言,火氣都上來了,差點沒像先前那般耳光招呼過去,因為那不意味著他見死不救嗎?
雨榴怒道:「杜兄口口聲聲說將雨榴當作朋友,卻是把我當餌,就為了誘老賊上鉤?」她知她是在遷怒,那臭嘴邪拳早已勸過他們莫接近那廖非豪,然而他們為顧及褒禪派的面子將其之言當作耳邊風。而杜承生也讓衛蕸替他倆打上了化毒掌,可說是該做的都做了,仁至義盡,杜承生就算再做更多準備,也無法預料到那淫賊竟早已備好毒和藥會如此猛烈。就算知姓廖的是淫賊,在他尚未罪證確鑿前,動手殺他都會為桃源門惹來麻煩,杜承生會他倆去與廖非豪接觸,純粹是無可奈何。
杜承生將腦袋撇到一旁道:「別拿我撒氣,妳明知不是這麼回事。」隨後又將酒葫蘆遞至雨榴面前,問道:「喝嗎?」夜雨榴想道自己沒怎麼喝過酒,又瞄了下在桌邊長孫讓已和李義與方才的李大爺在那兒共飲杜康,夏荷笑咪咪的正替長孫讓斟酒,二師兄和師父則不知跑去哪了。她便想到既然大家都這麼歡快,她也希望與之同樂,便伸手要接過那酒葫蘆。
但她卻未料到,正當她要抓起那葫蘆時,杜承生竟是縮回了手,不讓她拿,他笑道:「不過倒也不用喝了,現在便似是醉了的模樣這般遷怒別人,活像個醉潑婦。」
雨榴困惑道:「杜兄你這是在捉弄小妹?」杜承生笑道:「小爺便是捉弄妳,妳怎麼著?誰讓妳方才拿我撒氣的?」夜雨榴想道這臭嘴邪拳當真這般幼稚,又伸手要搶那葫蘆,但那臭嘴邪拳手上功夫厲害,右腕一拉,夜雨榴又連撲了好幾個空。
杜承生將葫蘆靠上口,仰首飲酒,隨後道:「逗妳呢,我不會讓低於十八歲的小毛孩兒飲酒的,我故鄉的大夫都道未滿十八即便是少量飲酒,亦可能損害髓海,使人思想遲鈍,妳還是三年後再喝吧。」
夜雨榴苦笑道:「怪怪,你怎的和村中夫子說得話這般類似?夫子他亦經常道未滿十八不應飲酒,可村中無人理會他所言。」杜承生聽言,就似聽見了什麼晴天霹靂之事一般,瞪大雙目,伸手便要擒住夜雨榴兩肩,卻又縮了回來,激動問道:「夜、夜姑娘,妳們村中夫子有提過他是從何處來的嗎?」
夜雨榴大惑不解,想道桃源門主怎會對她村中夫子如此感興趣?反問道:「怎麼如此問?嗯……這麼說來,夫子他確實總對他故鄉語焉不詳,總說是從很遠之處到來,卻又未曾提過,或許蕸姊知道的更多吧?」杜承生低首撫面道:「謝謝妳,這下我知我可能並非唯一一人了。」
夜雨榴問道:「唯一一人?此話何解?」杜承生搖搖首:「若是我道了,妳必定當笑話看待,日後等妳更信我一點我再道吧?說起來,妳不去陪魯兄嗎?」說罷,便從樹幹上立起,走入村民之中,與他們共餐,夜雨榴連從後喊住他都來不及。
雨榴這下只能苦笑幾聲,不只是每日都會相見的夏荷,竟是連不大常碰面的杜承生也瞧出來了,當真這般明顯嗎?若是連他也察覺到了,怕是褒禪派除了魯仲恆以外所有人都知道了。
儘管杜承生希望她能更信他一些,但她始終搞不懂這臭嘴邪拳究竟在盤算些什麼,加上師父的勸告,她始終對杜承生懷有戒心。然而,認識他這段時間裡,她發覺他那嘴似乎也沒初識時那般臭了,不過卻越發越孩子脾氣,或許他對視作朋友之人那臭嘴便會收斂不少。夜雨榴覺得杜承生肯定如他所說,已將是將她視作朋友,可夜雨榴卻懷疑自己有未將之視作朋友,若是先前多信他一點,或許亦不會讓自己身處險境。
夜雨榴明白了,杜承生之所以會來信希望來個交流,便也是要讓任掌門更信他一些,莫要再聽江湖傳言道他邪魔歪道,親眼瞧瞧他是什麼人物。她摳摳面頰,夜雨榴打算照杜承生所言去找魯仲恆,此時那魯仲恆會跑去何處?
她先是在宮觀內找,卻只發現了師父,和師父打了個招呼後,師父別具深意的和她道:「若要找恆兒,方 才他說他要到山腳了。」,還調侃了夜雨榴幾句。夜雨榴故作不在意那些調侃,離去宮觀,往山下找尋魯仲恆,夜雨榴想他輕功卓越,亦得加快腳步才能跟上他。
而正當她一個人來到山腳時,見到了她很不想見到的情景。她是見到了魯仲恆,但那小番韭方才才給杜承生帶走,現下卻又跟著魯仲恆來到山腳,而且竟是將臉靠在魯仲恆的胸膛,摟住他的腰,瞧了她醋意大發,便走上前去破口大罵道:「二、二師兄你!你!你怎麼對初識的姑娘家這般輕薄!」
給這麼一說,魯仲恆滿面委屈:「師妹妳別這樣看我,喂!起來啊!」他搖晃懷中的少女,但少女只是嗝了一聲,未有其他反應,夜雨榴走近二人,便聞到一陣酒味。杜承生方才道過他不會給未滿十八之人飲酒,想必是這小姑娘偷喝酒了。
魯仲恆尷尬道:「她醉了,幫我移開她。」夜雨榴聽言,也從後抓住她的雙臂,要將她拉離魯仲恆,小番韭卻在此時冷不防道:「魯大哥好硬啊。」聽言,雨榴理智全無,罵道:「你、你你這淫棍!別對人家小姑娘發情啊!」
魯仲恆一時間百口莫辯,他不知這小丫頭是怎會說出這般醉話來的,他自個兒的身體自個兒最清楚,氣血沒往下陰沖他亦清楚,那小姑娘怕是看狀況有趣便捉弄他。
魯仲恆只好如實道:「她、她醉了,說胡話!不信的話我──」那小番韭此時又道:「雖然村長的更硬,可是魯大哥的大得多呢。」夜雨榴聽言,大駭道:「什、什麼!沒想到杜兄他竟是那種人嗎?」,魯仲恆聽言亦不敢置信,但仍結結巴巴道:「方、方才那臭兔兒爺道過這小姑娘身形雖小,年紀也只比師妹妳小一年,已是可以成婚的年紀。那兔兒爺和這小姑娘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干係亦不奇怪。」
故此,那臭嘴邪拳的評價便莫名其妙的在二人心中掉了不少。
那小番韭又道:「──渾身筋肌壯實,真是硬。可是硬得很適中,曦兒抱得舒服,不像是村長硬得似鐵柱似的,靠上去不舒服。」二人聽言,才終於明白她是道些什麼,均是鬆了口氣,夜雨榴苦笑道:「什麼啊,這小姑娘道出的話真令人容易誤會。」雨榴拉開小番韭,將她緩緩放到地面上。魯仲恆則一臉委屈的盯著夜雨榴。
夜雨榴道:「二師兄,對不住。」,魯仲恆哼了一聲,顯然是對夜雨榴一點都不諒解,夜雨榴知道錯怪魯仲恆,讓對方受委屈了,過意不去。魯仲恆怒問道:「怎麼?特別來山門口這兒找我便是為了罵我淫棍嗎?」
夜雨榴道:「雨榴見二師兄不知去哪了,便下來找二師兄了。」
魯仲恆道:「那種宴會的場合我一點兒都不擅長,以後宴會找不著,妳就知我是偷偷溜出來的,莫需找我。」
夜雨榴又羞道:「我、我便是想──」。話卡在喉頭,夜雨榴之所以找他,便是想多陪陪他,然而夜雨榴卻因羞意無法將話道個完整,只得道個一半,令魯仲恆挑了挑眉,不明所以。
而他也無法懂得所以然了,那小番韭此時估計是酒醉未醒,不知出於何種緣故,從後抱住夜雨榴道:「妳、妳欺負魯大哥!」,雨榴聽言,一臉愕然,她對這小姑娘所道之言全然摸不著頭腦,若是如此,她亦不在意,她想道給這小姑娘抱總好過這小姑娘去抱二師兄,她便笑著任由這小姑娘撒嬌。
可下一瞬間,她便笑不出來了,那小番韭竟是右掌是搭上她的面部,左掌扣住她的左肩,無名指與尾指均掐入其面頰之中,夜雨榴還沒搞懂她為何這般做時,小番韭便已左掌一推右掌一拉,夜雨榴便如陀螺般被迴旋摔翻出去,令她背部著地、痛得叫疼。
這下來得忽然,縱使她習得躡影五峰平衡之法亦不及施展,她從地上轉個半身,左掌伏地,還未全然立起身,張口便道:「小姑娘妳做什麼?」但那小番韭未回答問題,反是右腳瞄著夜雨榴太陽穴側踢而去!夜雨榴一驚,連忙雙足一蹬,後退二步立直身子,避開此一殺著。
可小番韭醉意甚得很,無意停手,右腳方著地,便又踏前一步,左腳朝夜雨榴右膝踢去,夜雨榴以左脛與之腳板互踢,才止住這腿,夜雨榴冷汗直流,想道這小番韭雖無內功基礎,倒是從杜承生那學了些招式,且出手還如此狠辣。莫說太陽穴給踢中可能死於非命,而方才她膝蓋筋肌拉直,給那腳踢到亦可能就此殘廢。
她驚覺不妙,便喊道:「二師兄!」,希望他幫把手替她說服這小姑娘停手,然而那二師兄估計是為報方才給她罵淫棍之仇,竟是在旁看戲樂道:「哈哈!喝醉了便打人啦!這小姑娘酒品真差!」
見那二師兄無意阻止小番韭,夜雨榴迫於無奈,只好以褒禪腿法迎敵,她抬起左腿朝小番韭側腹掃去,可那小番韭後退一步,雙掌於腹前一上一下作勢要抓,夜雨榴便及時收腿再往其脛骨掃去,才掃得她平衡不穩,差點跌倒。
夜雨榴眼力甚好,瞧方才小番韭雙掌所擺動作,便知小番韭並非有意擒住她脛骨,小番韭有意抓住之處乃是其腳板,怕是她那腳真踢下去,就會給那小番韭擒住腳板,接著便雙掌一推廢了她踝上關節。
雨榴見小番韭出招這般狠,便決定趁勝追擊,欲速速結束這場鬧劇,左腳落地之時,便立即換右腳朝小番韭下段踢去,將其掃倒在地!那小番韭面部朝前倒於地面,叫了聲:「咕哇!」,卻又不肯認輸,竟是抓了把地上的雪朝夜雨榴拋去,夜雨榴單腳方收回地面,知若照尋常方式閃避必是不及,竟是給逼著運起內力,雙足一蹬便飄著後退數步,以輕功避過那把雪。
趁此空檔,那小番韭爬起身來,雙臂架於胸前擺出八字形,同時雙足一前一後,輕蹬數步便急速向前,這套身法怪異至極,前進之時兩腿未有交替,可竟是追上了夜雨榴!給一個沒半點內功基礎的人逼得要運內力才得以避過攻擊已令夜雨榴慚愧,而這小番韭竟是可僅靠筋肌之力便追上運上內力的躡影五峰之速!
小番韭不只追上了夜雨榴,還朝她右肋下一拳打去,幸好這拳拳路簡單直接,夜雨榴輕易便伸掌推開那拳,但小番韭另一手五指又朝雨榴右眼插去,夜雨榴歪首避過這指,平衡頓失,卻以左掌伏地,右腿朝小番韭下顎踢出,那小番韭見狀,再使那套怪異身法閃至夜雨榴右側雙臂之外,這下夜雨榴頭頂空隙便暴露在小番韭面前。
在旁的魯仲恆目瞪口呆,看戲的心態變作了觀武。小番韭全無內功基礎,僅以筋力施展身法卻能跟上夜雨榴運足內力的躡影五峰,這便說明了一事,那杜承生所傳授小番韭之輕功身法在平地移動上比躡影五峰更加高明。
雖說夜雨榴頭暴露給對手,那小番韭卻未拳打雨榴頭頂,反倒是拉近距離,以右肘再朝夜雨榴太陽穴打去,夜雨榴伸掌運足氣勁一檔,才不至於給擊翻在地。
魯仲恆在旁瞧那小番韭又出狠招,想道那小番韭喝酒打架便打架了,根本沒必要出這些狠招,除非她只懂得這些狠招。於是乎,他便看出這套盡是狠招的拳法的真面目,那便是杜承生完善承生截脈手前所使之西域拳法:瑪迦兇拳。他想道若這便是那瑪迦拳的招式,那當年杜承生出手即便不願亦是非死即傷,或著給冠以兇字,皆可說是理所當然。
此時夜雨榴右腳以至地面,左掌離地右掌伏地左腿便朝小番韭後頸掃去,這腿夾中了小番韭,她便一個運勁欲將之甩倒,但她忽覺一陣疼,那小番韭竟是以齒咬了她大腿一口,她疼得鬆開腿來,那小番韭卻不肯放過她,又是一拳打中她下陰。
夜雨榴是個姑娘家,可不似男子那般會痛不欲生,被打中這拳僅是疼了些就沒事了,倒是魯仲恆在旁瞧得心驚肉跳。可這一拳真將夜雨榴打出火氣來了,給小番韭這般一打,若是有個萬一,成婚那日讓人懷疑不貞該怎麼辦?
於是乎她左腿方落地面,站直身來,便右拳朝她面部打去,誘她以掌架開其,同時又以右腳朝小番韭左膝一踢,已然不在乎是否會踢殘小番韭。小番韭又咕哇了聲,但夜雨榴未隨之腳下留情,反而左腳再踢其左膝,將小番韭踢得單膝跪地,但小番韭卻又以足發力由低至高反朝夜雨榴頭槌而出,正中夜雨榴肝臟之處,夜雨榴一個吃痛,動作遲緩,她便趁勢伸臂一抱,右掌雖給雨榴拍開,但左掌卻成功伸至其頸項後,伸指便抓雨榴那頭長髮,用力一扯!
這般一抓,痛得夜雨榴哇哇叫,情急之下她竟是伸出兩指欲插瞎小番韭眼睛,但她此乃她首次戳人雙目,給小番韭輕易看穿,小番韭身子朝下一沉,雙臂抱住夜雨榴兩腿,後退一步朝後一拉一推又一次將夜雨榴摔翻在地,夜雨榴本想出腿回擊,但那小番韭已跨坐至其大腿上,以體重壓制她雙腿,隨後小番韭便雙拳交替朝雨榴面部連環打出,那些拳速度奇快、又如雨下,眨眼間便已有三、四拳打出。夜雨榴雖已雙掌盡力抵擋,但仍有不少拳頭落到她鼻頭上。
這一刻,夜雨榴知道她輸了,至少在徒手招式上竟是輸給了這小姑娘。她憤而運足十成力,兩臂一推,以內力將小番韭彈開,小番韭因此被彈了十數步之遠,大喊道:「不公平!不公平!姊姊妳作弊!」但夜雨榴已受夠她的胡言亂語,站起身來,伸手便將腰間之劍拔出!若是腿法比不過她的拳法,她便要以劍法與之一拚!
魯仲恆此時再也看不下去,插入二人之間,道:「師妹!妳瘋了嗎?」
夜雨榴怒道:「師兄,別阻止我,我──」魯仲恆道:「妳是個傻潑婦!」小番韭在旁聽言,大笑道:「哈哈哈哈!活該!」但魯仲恆卻轉過身來對其道:「而妳是個傻醉鬼!」魯仲恆罵道:「褒禪腿法裡可沒插眼的動作,妳當師兄我不知道嗎?竟然還想拔劍?就不怕一不小心殺了人家?」聽言,夜雨榴低下首來,想來她的確給怒氣沖昏了頭,瞧了瞧自己手中的長劍,那長劍已換成平時所用的開鋒劍,若她真拿這劍朝小番韭刺去,小番韭的確可能因此送命。
魯仲恆又對小番韭罵道:「還有妳這小醉鬼!我是不知那村長為何教妳這套惡毒的拳法,但他難道沒告訴妳不能將這套拳法用來隨便打架嗎?」小番韭聽言,亦是滿面愧疚,兩根食指互碰著,嘀咕著什麼。
夜雨榴想道那二師兄也不想想她倆是為了誰才打架,雖是有怨,也不敢多言怕暴露了心意,魯仲恆見倆人都無話可說,便道:「我帶妳倆去沈大夫那瞧瞧,妳倆可要做好不只給我罵的準備。」
※
夜雨榴的鼻頭給小番韭打得瘀青,大腿給咬傷,肝臟挨了下頭頂,所幸檢查後知無大礙,小番韭的頸子也給夜雨榴夾出印子來,而因身形大小差距的緣故,小番韭為了站穩身子也給扭傷了腳。兩人所受都是輕傷,但對二人來說,麻煩可尚未結束,桃源門主與另外的褒禪派師徒二人聽聞此事後都趕來了沈大夫的醫館,任劍霄扳著張面孔,杜承生則是進門就開始道:「原來葉兄託給了小爺一個大麻煩,還不知道妳還會喝醉了便動手要人性命呢!」
小番韭聽言,亦是不好意思地低下首來道:「咕嗚、我,我爹娘都會給我喝的──」
杜承生又怒道:「妳爹娘是妳爹娘,桃源村的規矩是桃源村的規矩,我早在最初我提醒過的妳不可隨意飲酒,而我亦道過,這套拳法凶狠,妳只可用於自衛,不可隨意使來傷人!妳真厲害!將我的話全當作耳邊風了!」
長孫讓在旁聽言,在旁打圓場道:「好了好了,杜兄還請莫發這般大的脾氣,她倆年輕氣盛,吵架了打起來也沒什麼,彼此氣消了就好。」
他沒有在現場瞧見小番韭所使之拳法,以為只是小女孩間的吵架罷了,魯仲恆聽言,亦搖搖首。而杜承生怒氣未消,對長孫讓又道:「你懂什麼?當真沒聽說過我當年使瑪迦拳時失手廢了多少人?她就拿這些狠招使在你的師妹身上!方才若一個意外,夜姑娘便要廢了條腿或瞎了隻眼,這事若發生了,責任由誰來擔?」
長孫讓苦笑道:「南宮姑娘全無內功基礎,此事應該不會發生才對。」
魯仲恆搖首道:「大師兄你當時不在,什麼挖雪拋臉、腳踢膝蓋、手指插眼啊、肘打太陽穴都出來了,我本見那小姑娘出手狠辣,卻以為我們小師妹有辦法阻止,她就未阻止她倆,沒想到我們的小師妹,竟是被逼得拔劍出來。」任劍霄聽言,一陣詫異,卻又不得不信徒弟所道之言,亦即是說那名作南宮曦的小姑娘逼得自己的弟子不得不拔劍?姑且不論她所使之拳法如何凶險,雖說褒禪派向來是以兵刃功夫聞名,但這意味著這般小女孩的手上功夫遠勝過了夜雨榴的腳上功夫?那杜承生先前才誇過他是個好師父,現下此事發生,任劍霄不知那杜承生是有意或是無意,但此事的確削了他面子,令他一陣惱火。
小番韭楚楚可憐道:「可是、曦兒也只會此套拳法。自然而然動手時就使出來了──」杜承生又怒道:「妳便不要無緣無故與人動手便不會有這些問題。」
小番韭道:「可是曦兒醉了,動手乃是不可抗力。」
杜承生又怒道:「所以我就和妳道過別飲酒了!妳每次都這般喝得酩酊大醉的!我早和妳道過妳遲早有一日會惹事的!」
夜雨榴在旁聽著,越聽越覺得不對勁,她想道這拳法不正是杜承生傳小番韭的嗎?那她惹事,把自己打傷了,豈不是這臭嘴邪拳亦得負起些責任?於是便問道:「說到底為什麼杜兄要教這小姑娘這般凶險之拳法?傳她普通些的拳法不就好了?」
杜承生道:「普通些的拳法,少了恫嚇之效。我先前和諸位道過,我之所以教村人們武功,便是要桃源谷的村人能保護自身,若只是瘀傷可嚇不了那些野盜,讓他們知道來犯可能會缺隻眼,少條胳膊,他們才會望之卻步。」
夜雨榴苦笑道:「可未免也太過兇殘了些吧?正因如此桃源村才會給武林中人視作門派而非尋常村莊啊!您不也希望被稱作村長而非門主多一點?」杜承生苦笑道:「夜姑娘既知如此,那為何先前還要稱呼我為門主呢?」
明白杜承生又在挖苦她之前對他撒氣一事,夜雨榴只得苦笑。
杜承生沉下臉道:「我寧可世人誤解我等,也不願見好人沒有力量,好人沒有力量,此乃世上最悲哀之事。」說罷,似乎回憶起了某些不堪回首之過往,那杜承生忽然伸手掩面,似是要流出淚來。
任劍霄雖不贊同杜承生之作法,認為惡毒之招式本就不該廣傳,卻能明白他為何這般作,可他亦知如此作另有隱憂,任劍霄此次不帶任何惡意的道:「門主可知維持弱小亦有其必要性?您助那些村人自衛,可這些自衛之力亦會招惹道些不必要之死敵,一群尋常百姓,學了武功便可能被視作江湖中人,捲入江湖的腥風血雨之中。」
杜承生本就道到情緒上,又給任劍霄這麼一道,便諷道:「掌門說笑呢,您要不要問問夜姑娘的故鄉有沒有維持弱小?結果怎麼了?」夜雨榴聽那臭嘴邪拳竟又是拿自己的故鄉說嘴,差點一耳光搧過去。可臭嘴邪拳又道:「或與世無爭,或做好戰備,厄運總可能降臨至頭上。我寧可讓他們引起些注意,也不願厄運來臨時他們毫無抵抗之力。」
小番韭瞧杜承生似要情緒潰堤,便走至他身旁,拉了拉他的袖口,道:「別說了,村長,走吧。曦兒受得傷不重,可以回村裡再療養。」
註一:
這回關於現實武術的東西我考據了不少,小番韭使用的拳法和步法九成以上都是現實中有的,因為參照的武術流派並沒有很多應對踢技的招式,至少據我我手邊資料只有應對低位踢的反擊招式,而且因為對手是女性,該拳種對陰部的幾種腿技也顯不出效果因此小番韭沒有使用,所以很多地方的對招方式是由我由我自行發揮,雖然招式應對方式不一定對,但希望有打出其精神來。
另外,褒禪腿法的動作設計很多部分都是參考了卡波耶拉,只是我又不想寫得太像卡波耶拉,所以未採用卡波耶拉中的一些比較高識別性的動作。
ns3.144.101.154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