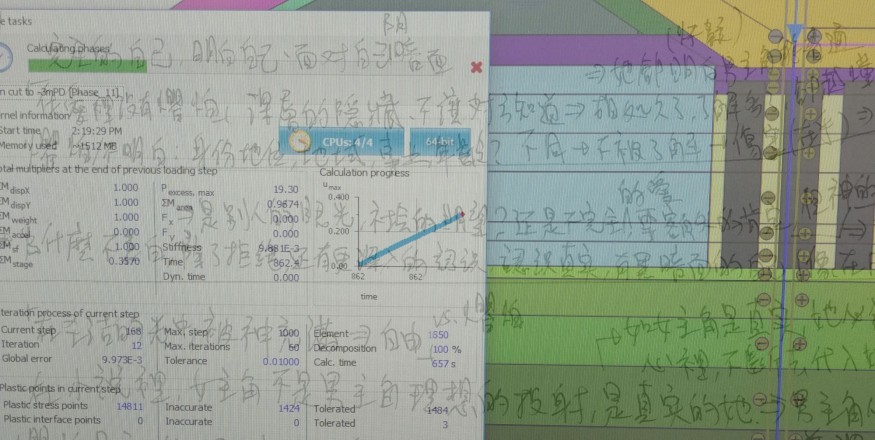靶文,即是文章本身不是重要的,所引起的評論才是它真正價值。有靶文才可以玩飛標。
我寫了幾篇靶文,點擊率非常高,只是一天多,可以有近六百的點擊數。
《孤獨的真相》,594點擊數
《孤獨的真相》,514點擊數
《木馬屠城 – 自由和民主的偽裝》,472點擊數
《木馬屠城 – 公義和真相的偽裝》,222點擊數
連一篇不關連的,《這世代終結的預兆》,也有241個點擊數。
這一下子把我這兩個博客,在短短兩三天就推至網站的第四和第五名。因為是七天點擊總數,排名還會升。
而其他文章,即使放在平台一段時間,點擊數也不多。
而我寫了一年有多的小說,
《光與暗的相遇》,56章,5797點擊數
《光與暗的對決》,88章,7521點擊數
對這個流量不算很多的小說網來說,這兩篇小說的點擊數已經滿不錯了,但和上面的靶文相比,就差天共地了。
我還想寫那布袋彈的科普東西,但我覺得沒有什麼意義。或多寫一些政治的東西抒發一下,但寫出來又挑起矛盾和對立,沒有意思。
對在網絡寫作來說,這些點擊數可以帶來很大的滿足感,因為這代表很多人閱讀自己的文章。
但這些是靶文,即是說,文章往往拿出來引起更多的批評和聲討。
我寫的時候,已經有這個心理準備。以前不寫這些靶文,我知道我站在大多數人的對立面,就不想引起更多的對立和仇恨。
我的性格很敢言,不容易退縮。我試過在一個立場和我相反的數百人講座,公開指責一個十分有聲望的新聞界人物。我也在內地的大會上,問了十分尖銳的問題,令主持人不讓我發言。我也嘗試面對公司眾董事門的高壓而沒有妥協而被裁掉。
我還在大學做學術時,學生要習慣在數百人的會議上和各權威教授去激烈辯論,堅持自己的研究成果是對的。
通常在強調言論自由的社會,遭遇這些會更敢言去對抗,用更激進的言詞和手段去維護自己的自由。好像這一場持續的示威的邏輯,政府越是不回應,更要把運動激進化,不惜以極端手法。
這就是極端主義的苗頭。我們在國際新聞看到的極端主義,我們也摸不著頭腦,為什麼不惜以用自殺的手段,去策劃九一一,去殺害無辜的人,去表達不滿呢?難道他們不知道這不能改變什麼,只會令其他人更不認同他們。
他們抱著同一信念,因為被欺壓得太厲害,卻沒有辦法用其他方法討回公道,不得已極端手段去抗爭,即使成功是如何渺茫,也要一試,可能激起更多人出來反抗。西方對恐怖主義,也是打壓不盡的。
極端主義的源頭,是因為極端的仇恨。他們不是被無知洗腦,是被仇恨洗腦。
面對一件事,去仇恨,或是去關愛,在乎你的選擇。
有人去批評美國警察,批評黑人在美國受到歧視,我是認同的,也有親身經歷。
我在美國從伯克利到史丹佛坐火車途中,有一個黑人婦女,坐輪椅的,無故大叫滿口粗口,之後有警察進到車廂。她不知道為什麼情緒激動起來,我也不知道前因。之後好像變成不斷罵警察,到了一個站,警察把她的輪椅推出車廂,大概不想她騷擾乘客吧,而我剛好在同一站下車。之後警察把她推出站外,黑人婦女不斷罵那些警察,又罵又哭,警察也罵回她。我還要在附近等車,附近只有我一個人。一會兒,警察把婦女從輪椅拉出來,然後走了,之後那個黑人婦女放聲大哭,我也上了巴士。
當中民眾可能不想惹事,這些警察的確很惡,或者這些事太普遍了。
我當時沒有去想為什麼警察這樣做,只想這個黑人婦人很可憐,我又不敢去幫她,很有內疚感。我路程中只想那個婦人發生什麼事會失控,是否沒有人理會她,她這樣被掉在一旁,怎樣爬起來回家。
我去每一個國家,都去看這些低下階層,因為我也窮過,也被人拒絕。
可能我不是生活在美國,香港還沒有發生這些事,對那警察的行徑只是一個認知層面,美國連警察都特別惡的,要小心一點,不要惹事,沒有想什麼公義層面的事。
我還在英國讀書時,在希斯路機場出境回香港。當時歐洲對恐怖主義十分緊張,我看到一個穆斯林家庭,一家六口左右,要出境。爸爸成功過關,但媽媽和她的孩子不能過關。我一直排隊,一直看到媽媽十分緊張,哭起來,完全不知道怎樣辦,英國入境人員十分冷漠,整個大堂排隊的人都很冷漠。我還看見不少牌寫著,對入境人員言語暴力和肢體暴力同樣是零容忍,都是刑事罪行。
可能我們也幫不到什麼,我們心裡可會把注意力放在冷漠的英國入境官員,為什麼竟然把婦女和孩子當成恐怖份子不讓他們出境,可能怕他們去伊斯蘭國嫁給聖戰士。我可以去仇恨那些官僚不近人情的官員,但我當時只看到這個母親哭得很可憐,和她幾個不知所措的孩子。
之後,我對穆斯林十分同情,這種家庭分散,趕不到飛機,經歷過知道一點都不好受。因為很多國家人民對視他們為恐怖份子,口頭上或許說不是,但內心卻會這樣想。
我在英國接觸了不少穆斯林,除了打扮不一樣,其實很會關心人,比一般人還會關心。人在外地,對客旅的有一份特別的感情。
為什麼要放棄爭取公義呢,把公義和憐憫放在一個對立面上?
不近人情的美國警察和英國入境官員,為什麼不去批判他們一頓?正好可以來對抗現在仇恨香港警察的意見,也對示威者勾結英美的外國勢力一個迎頭痛擊的批評。
不少香港人對英美的稱讚,我對她們的批判,在於著眼的東西。香港人大多看到英美的中產生活,而我總看那些地方底層的生活。這些基層被階級化社會遺棄,正如美國公共交通只有基層乘搭,有很多黑人區,英國貧民區,把階段分割成兩個世界,看到不同景象,所以我看到不少讓人忽略的社會不公。
在這些有需要的人面前,最切身需要的是面對面的關懷,不是那遙遠的社會公義。
我接觸的貧窮人,最缼少的不是錢,而是心靈的觸摸。
因為被憐憫,所以去憐憫人。
我們越是高舉公義,越令對方心硬。
我們越是高舉公義,越對他人無情。
我接觸很多內地人,聽了很多社會不公的案例。
他們都很想改變這個社會,但對改變很有無力感。
我最在意是他們的生命故事,經歷了什麼。
在香港的事件,我很多內地的朋友也很關心我有沒有受影響,想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有一個內地姊妹在臉書發了一個帖,看得出她很憂心,去為香港禱告,我很感動。她被很多香港人批判,我覺得很無理,但我很感動。因為她是純粹的關心,不是像其他人一味兒加入批判香港示威者的行列。
還有一個內地同學,他來香港旅行,我陪他和妻子旅遊。我聽他在內地做學術的經歷,也聽他對高校一些批評。而他看到我十分憂心而安慰我,我很感動。
我沒有使命感去為他們做思想教育,但我只想多做一些關顧的工作。我求神給我機會去關心他們,不要被仇恨充斥我的內心。
ns 15.158.61.12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