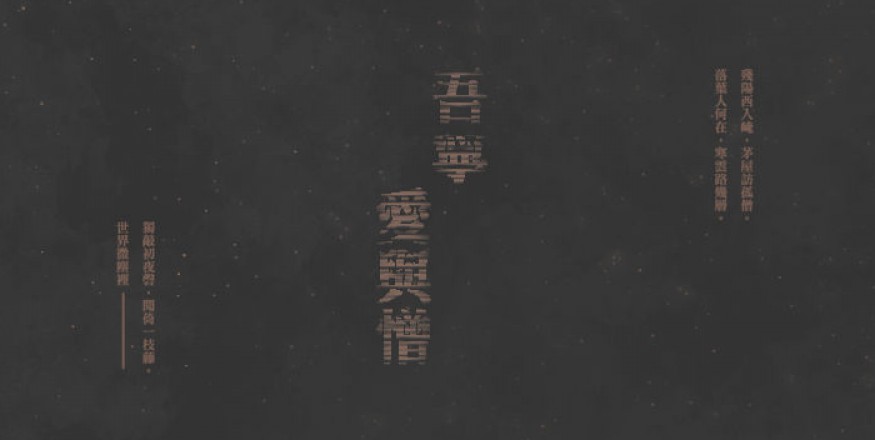北嫺怡再次瞥了眼掌中的手機,現在已是深夜十二點,她卻站在家門前遲遲不敢進入。拉下一半的鐵捲門是單良延等待她回家的暗示,又或者,只是方便他的酒友等會兒離開。手機內沒有半通單良延的來電,以及詢問她狀況的訊息,看來關於鐵捲門的答案是後者。
胸下未被遮蔽的空間可窺見一樓的燈仍未關,也送出單良延與酒友暢聊的豪邁笑聲,聽在耳裡,打在心上,想起等等要跟他商量的事情絕對會使他笑不出來,她不禁覺得自己是撲火的飛蛾。
如此戰戰兢兢,好似夫妻間的溫柔包容,本就該被柴米油鹽逐漸銷蝕,是無須共識的自然定律。
「欸!怎麼沒看見嫂子?」
「嫂子」一詞攫住她的注意力,北嫺怡屏氣凝神。
「喔,她下南部了啦,那邊有事的樣子。」單良延的語調有些懶散,叮的一聲,似乎是倒了杯酒。
「什麼事?你之前不是說沒在和那邊來往?」
「誰知道啦!喝啦!說這個幹嘛?」
咚!
玻璃杯撞擊木桌的聲響隨著尾字落下,力道不小,震得北嫺怡頭皮一麻,左手忍不住捏緊衣角。然而,發出聲音的不是單良延,是那位酒友,「別顧著喝,良仔,現在幾點了?好歹也問一句關心一下吧?那是你老婆欸,是你要娶她的欸。」
一時間,氣氛驟降,但有什麼正破冰而出。
北嫺怡聽著屋內的死寂,醞釀一觸即發的衝突。她太了解單良延,他不回話,是因為怒火在肚裡燃著,更是要對方適可而止的警告。
「良仔,十八年了,離我們大學已經十八年了,那件事也已經十八──」
「喂。」單良延用不輕不重的音節制止對方繼續說下去,「再說下去,就別怪我不留情面。」
語落,又是一陣寂靜。
空氣彷彿因此稀薄,北嫺怡克制著呼吸,深怕兩人發現她偷聽了一個貌似跟自己有關的秘密。同時,她也意識到自己若不快點打斷他們漸漸高昂的情緒,等會兒真鬧起來,除了失去和單良延商量的機會,還會吵到街坊鄰居,在大半夜丟人現眼。
酒醉的人可沒幾分自制力。
北嫺怡悄悄後退幾步,再刻意鞋底蹭地的向前走,唰啦唰啦,小石子緊抵薄薄的底部,劃過她的腳底板。她矮下身,鑽過預留空間的鐵捲門,進了車庫,輕喊:「我回來了。」
車庫的燈未開,但一樓店面的大片玻璃拉門,根本無法阻礙室內燈光。她藉此閃過右方的戶外廚房及結帳櫃台,猶如平時要內用的客人,直往拉門過去。
「來找阿良喝酒啊。」他們倆坐在離門口最近的位置,北嫺怡拉開門後,垂頭將手機放進口袋。不與兩人有眼神接觸的她,扮演合格的若無其事。
「喔嗯。嫂子妳回來啦。」酒友含糊應話,原先的忿忿轉成微妙的尷尬。他起身,撓了撓後頸,突兀的說:「很晚了,我先走了。」
說完,也沒和單良延打聲招呼,便逕自匆匆離去,徒留一室濃郁酒味。拉門喀的闔上,北嫺怡故作鎮定,轉身目送,努力假裝看不出端倪,卻不敢回頭迎上單良延的目光,「他今天是怎麼了?我又沒說不讓你們繼續喝。」
單良延對她這句玩笑話沒有反應。一股電擊般的麻癢倏地從脊椎衝上頭頂,北嫺怡的感知全被單良延的審視佔據,她極力壓制洶湧而至的慌張,趕緊回身收拾起桌上的空啤酒瓶,像是某種自我保護機制,繁忙的手,一點一點掩下了差點露出來的餡。
良久,久到北嫺怡在一樓區域來來回回走動好幾趟,撤走所有空瓶、關好鐵捲門,單良延依然不言不語,而黏在她身上的視線毫無偏移。在角落的北嫺怡擱下手中最後一支空瓶,心知已無事可做,只得緩緩吸了口氣,揚起討好的淺笑,旋身,「那個──」
「妳有事就說。」單良延一手支著右頰,面無表情,「一回來就四處瞎忙,以為我看不出來啊?」
好在,單良延沒懷疑她聽見了什麼。
不過北嫺怡沒時間慶幸,她口乾舌燥,準備出口的話重得她打不開嘴。
跟他好好商量事情的經驗停在新婚的那幾個月,是還未消退的愛給她的膽子。
「喔,看來事情很大條。」單良延亦是足夠了解她,苛刻的冷笑與新婚時期判若兩人,「我給妳一分鐘,要說就快,不要等我耐性沒了才在哭哭啼啼。」
「那個,我……我能不能……能不能接我阿嬤過來照顧?反正二樓還有幾間空房……」
北嫺怡被逼急了,拋掉計畫好的說詞順序,話就這麼溜出。單良延的臉部線條並無一絲牽動,她瞧著,心知事態要糟,卻沒有分毫驚慌,他的一切反應早在她預料之內,只是沒辦法再維持迎合的笑容,「我阿嬤她……三年前得了帕金森氏症,兩位叔叔照顧那麼久,撐不住了……」
「跟我有關係嗎?」單良延坐直身軀,不再看向北嫺怡。倒映在玻璃拉門的側影有些模糊,連方才的銳氣也變得朦朧,「我們當初不是說好了,各自的長輩各自照顧?」
「那是因為──」
「當時我能自己顧,輪到妳,說過的話就不算數了?」
這句話擊潰北嫺怡備好的所有言語,因為單良延說的沒錯。
猶記結婚第一年,單良延家中長輩癌末,但他父母早已雙亡,重擔理所當然的落在他肩上,而她……沒有與他共患難,甚至對他說過──
雖然兩人是夫妻,可是雙方的家人並不會因此成為對方真正的家人,畢竟從未相處過,怎能憑著一紙婚約,便要對方真心相待呢?
那時的她夠大膽,那時的他夠和氣。
一同在心裡簽下無憑據的契約。
「妳告訴過我,妳父母會離婚就是為了照顧妳阿公,所以我明白妳排斥這件事情,我不勉強妳,現在妳自己遇到了,之前那些話就是屁?」
單良延嗓音平靜,頰上有著微醺的紅潤,卻不見他的情緒化以及紊亂的表達。北嫺怡自知理虧,可她沒有退路,「我已經答應我叔叔了……」
「不關我的事。」
「你也知道是他們養大我的,我拒絕不了……」
「關我屁事。」
「那、那我自己顧總可以了吧?」
「可以是可以。」單良延嗤笑,雙眼斜睨她,右拇指比了下自己,「但這間房是老子的。」
北嫺怡神情幾番變化,最終只剩無法言喻的難堪。她雙手攥緊腿側的褲管,顫著聲,「要算得這麼清楚?」
她突然感到迷茫,好似這世界上沒有一方土地供她落地生根。興許,早在母親棄她遠去、父親溘然長逝之時,她便沒有「家」。
她曾經以為單良延能成為她的「家」。
轉瞬間,北嫺怡心灰意冷,眉眼耷拉下來,道不明的疲憊讓她無力再畏首畏尾。她鬆開手,整個人有些許癱軟,可話音平穩,「我在麵店工作的薪水怎麼算?以前的我不跟你計較,從明天起,我要領薪水,你直接扣掉我和我阿嬤的房租、水電費、伙食費,還有……我平常做的那些家事算加班吧?你覺得該怎麼算?」
單良延明顯愣了半晌,兩人對望幾秒,他忽而讚賞似的微微一笑,「還有點骨氣。」
他從座位站起,幾個闊步走至北嫺怡身前,俯瞰著她。她仰起頭,單良延高大的身形恰好擋住天花板的日光燈,狹長的影子覆蓋她全身。
「妳老員工了,薪水一個月三萬二,房租那堆雜七雜八的我給妳減免,算和妳的『加班』相抵。明天,我放妳假,去接妳阿嬤過來。」27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POZA7sM3V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