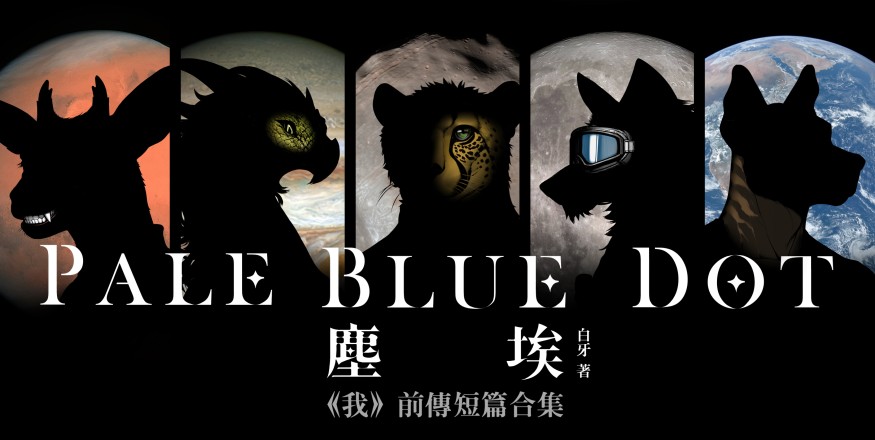對著鏡子,我將紗布拿開,確認傷口止血了。
「我沒太大力吧。」一頭紅鹿將下巴靠上我的兩角之間,緩緩的磨蹭著。
「沒有啦。」我拍拍他的臉頰回應,享受了一下溫存的觸感。「但是太冰了,讓我有點瞬間出戲。」我看著他把假牙擺上洗手台時說道。
「喔,抱歉,下次注意。」他從背後有點慵懶的抱著我,那讓我很有安全感。身為雄性動物,這麼想好像有點沒出息,但這是不到一百六十公分的我僅有的特權。
「喔對了,輪到我準備了吧?」我檢查了一下放在一旁的碳酸氫鈉針劑,保存期限快要過了。
我可不想讓窘迫反應爆發,因為橫紋肌溶解而死在廉價旅館裡面,然後被社會版頭條以聳動標題餵養給飢渴噬血的閱聽大眾。這種羞恥至極的事情光是想像,就快要觸發我的窘迫反應了。
「不用,我想再約後天。」他用濕濕的鼻子碰了碰我的耳朵說。
「欸,也太快了吧?」耳朵上的麻癢感讓我笑了出來,輕輕將他推開。
「要到換角期了,我不想出門。」他嘆了口氣,將我抱得更緊了一點。
「有什麼關係,反正大家也都戴假角,誰也不好意思說破。」我抓了抓頭頂上突然發癢的皮膚說道。看來我的角也差不多要掉下來了。「我後天不行,大後天呢?」
「那天我和女友要吃飯。」他簡單的陳述事實。
「喔。」我清了清喉嚨,自認為完美的化解了尷尬情境。「你有打算跟她說嗎,你的……嗜好?」我知道有些情侶能接受。
「沒有。」他有些抽離的說道,將手放到我的唇邊,用指腹在我犬齒的尖端來回摩擦著。「我是比較硬核派的,一定要是真的牙齒才有感覺。」
其實我是想問對方是否可以接受你自己出來找樂子,不是你有沒有想和她嘗試新玩法。不過我連這頭紅鹿的名字都不知道,好像沒有什麼立場多說什麼。
「或許你可以考慮移民去月球?」我建議道,那裡的居民聽說非常包容。
「哈,犬科帝國的門口,還有那些恐怖的爬蟲類海盜?算了吧,光是想到和肉食動物並肩走在路上,就能讓我全身的毛都豎起來。」他笑道,做了個感到噁心的表情,語氣比我預期的還要不屑。「再約?」他瞬間就穿好了衣服,我微微點了一下頭回應。
聽見房門關上的聲音之後,我又在鏡子前面站了一小段時間,看著自己單薄的倒影,並且輕輕的以食指指腹碰觸,我露出嘴角的犬齒尖端。
290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LYbIvIHfKg
我找到條路,通往旅館的頂層。
是風,有一點點臭氧的味道,可能是直接從輸氣管線吹出來的。感覺很舒服,我短短的毛髮,和衣服下襬以相同的頻率擺動著。
將手搭在金屬欄杆上,我俯瞰著水手谷市區,幻想月球街道的景象──明亮、繁忙,並且充滿活力。基本上就是優化版本的戰神星。
犬科、草食動物和爬蟲類,生活在一起。這是真的嗎?或許有天,我能親自看看。
突然靈光一閃,茅塞頓開,困擾我已久的問題有了答案。我拿出筆記本,寫下新的想法。
完成紀錄以後,我翻到筆記本的最初幾頁,讀著自己有點潦草的筆跡。靠著我手邊能找到的資源,我現在只能勉強翻譯出「強者」和「弱者」兩個詞,這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在湧現的記憶中,我思索著。
「你真是匹,很有意思的山羌呢。」那匹紅鹿一邊說著,一邊咳出更多的血來。
「不要說話!」當時的我怎麼能那麼鎮定的呢?他身上有好多個洞,每一個都汩汩的湧出沒有停下跡象的血液。
附近的紅沙都吸飽了血,變得黏稠。人的身體有多少血可以流出來?就算我趴上紅鹿的身體,也不可能蓋住全部的出血點,因為我太渺小了。我向附近的行人求助,他們都轉開視線,維持著夠遠但不失禮的距離。
「這大概是我的報應吧。」紅鹿居然笑了出來,至今我還是無法理解他是什麼意思。「欸,我們甚至都不認識呢,你怎麼這麼熱情啊?」他還有心情說笑話,但我慌亂到沒有抓到重點。「先說清楚,平常我只和至少吃過兩次晚餐的對象上二壘啊。」因為拐錯了個彎,走上了意料之外的路,讓我發現了這匹渾身是血的瀕死紅鹿倒在街角。
沒有多想,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幫上什麼忙,我就衝了上去。所有曾經聽過的宣導或是偏方,甚至是我中途落跑只有簽到退的環安衛訓練,每一個急救相關知識都在我腦袋裡面炸開了,但沒有半個能派上用場。
「這是誰都會去做的事吧?」雙手都沾滿了濕滑血液的情況下,操作個人終端非常困難,我甚至沒辦法切換成聲控模式。不過那時我還不知道,嘗試通知醫院之類的舉動,是多麼的徒勞。而且仔細想想,看見倒在路上渾身是血的陌生人,直接衝上去的確不是誰都會去做的事情。
紅鹿又笑了,至少我覺得他是想要笑,咳著血泡的喀喀聲不是很好判斷。
「那我……或許也應該去……賭一把……」直到今天,我都無法確定那是不是我的幻覺。
紅鹿用幾根顫抖不已的手指碰觸著我的頭部,讓我半張臉都沾上了血。「Только сила знает конфликт,слабость ниже даже поражения и рождается побежденным。」他唸道,這句我無法理解的話語和文字,就這麼烙印進了我的記憶之中。全然的震驚,但我很確定自己看清楚了他棕色眼睛變成鮮紅色的那個瞬間。
然後,紅鹿就斷氣了。
還沒有從衝擊中恢復過來的我,維持嘗試壓住止血點的姿勢,直到執法單位出現。被當成嫌疑人連續不間斷審訊的四十八小時,是我人生中最接近精神崩潰的經驗,直到我開始準備資格考。
不過說到這個,要不是大學方面出手干涉,我只怕已經爛在某個不會有人注意到的地方了,所以至今我還是很感激我的指導教授。「那你就簽博士班來答謝我吧。」我知道他不是在開玩笑。
從記憶中脫出,我闔上筆記,收回口袋。
因緣巧合之下,為了翻譯我腦海中無法抹去的那段話,閱讀比對了大量古老典籍之後,開啟了許多我對於歷史的疑問。隨著愈深入的探查,我只找到更多的謎題,而沒有解答。關於過去,我們遺忘的比記住的多太多了。我訪問了所有相關的草食動物專家,翻遍了戰神星和其衛星上所有的博物館文物,還是沒有進展。
我怎麼沒有想過呢,答案,當然不會在戰神星上。如果有任何地方能提供解答,一定是太陽系中唯一還有多種族共處的地方,所有故事和祕密還沒有被官方宣傳扭曲的地方──月球。不同種族對於不同事件的不同版本詮釋,肯定還保留在這種高度歧異社會的奇聞軼談之間,只要稍加比對,就能朝釐清歷史的真相更靠進一步。
失傳的語言,沒有留下紀錄的文字,那些,被埋藏那世界另一側的祕密。我,想要了解,一切是怎麼變成今天這樣的。還有,我們之後能夠變成什麼樣子?
改變的契機,究竟是否存在呢?
臭氧的味道愈來愈濃,我站直身子伸展了一下,抬起頭仰天看去。一艘飛艇剛好離港,在身後留下一條明亮的軌跡。內心湧起的某種情緒,讓我奮力向上伸出手,好像這樣就能夠碰觸到,那真正的星空。
ns 15.158.61.5da2